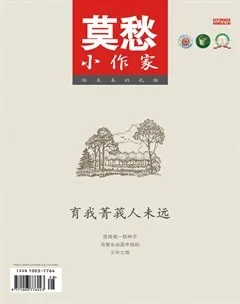大缸
將大白菜、蓮花菜、胡蘿卜、青筍洗凈,撕成葉,切成塊,焯水。往缸里鋪上一層,撒些鹽,淋上花椒、生姜、尖椒熬的湯汁,再鋪一層。直到缸里快滿了,搬來一塊石頭,壓住菜,合上蓋,母親拍了拍手,舒了一口氣。缸滿了,似乎也舒了一口氣,它已經很久沒有滿過了。放在陰涼處,隔幾天,這缸麻菜就腌好了。吃時,撈出幾片,切碎,拿熱油一潑,香。
這樣的冬菜,一定要腌在缸里,一定要用石頭壓住,鼓鼓囊囊,五味雜陳,才不會壞,才出味道。腌菜的這口缸,陶質,缸口直徑20公分,上下一般大,通體暗黃,外壁有許多凸點,有些硌手。缸是泥土的華麗重生,既防鼠蟲,又能隔潮,裝水、腌菜、擱米、盛面,不可或缺。
在家鄉(xiāng),缸不管大小,都稱為大缸。汪曾祺有句話,說家里缸多,光景就好。如此說來,以前我家的光景,堪說慘淡。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母親嫁過來時,家里有口缸。口小肚大,矮胖矮胖,蹲在地上,肚里盛了腌菜。沒幾個月,腌菜吃完,這口缸像長了腿,跑鄰居家去了。這缸原是借來的。
借鄰居的缸還回去了,又從三姑家借來一口,用了好久。后來父親買回幾口缸,腌菜的這口最值錢,花了兩塊多,我們叫它“精品缸”。其他都是五毛錢一口的殘次品,灰頭土臉,有裂紋。裝不了水,就裝米、裝饃、裝洋芋。其中一缸,口大肚大,個矮,缸壁有兩只抓手,像兩只耳朵,裂痕有些大,父親用鐵絲在缸口細細箍了一圈,我們叫它“耳朵缸”。裝饃、裝油餅的缸,口小,肚大,個矮,我們叫它“油餅缸”,聽這名字,好像缸里總藏著油餅,承載了我們太多盼頭。其實,只有臘月二十八以后,這缸才會裝滿油餅,其他日子,里面只蹲著三五塊巴掌大的黑面饃。
我們返城后,母親攢了錢,陸續(xù)購置了四五口缸,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多是瓷質,耐看耐用,放食物,久置不壞,成了家里值錢的家當。
在父親心目中,缸被賦予了另外的寓意。多年來,他不止一次說,做人不可尖酸刻薄,不可落井下石,要像缸,沉穩(wěn)大氣,有肚量,啥事都能裝。據旁人私下講,有人曾給父親使過絆,但父親從未說過那人的壞話。母親無意中透露,有哪些人從父親手里借過錢,一些還了回來,一些沒了音訊。但父親閉口不談。前幾天就有位老友拿來三千元。父親回憶,當初借出兩千,已近二十年了。另外一千,老友非要算作利息。父親拿這錢換了一部新手機,他說,也算是個紀念吧。
如今生活好了,缸顯得笨重,占地方,已經越來越少見。大家更喜歡冰箱,比缸肚量大。還喜歡用塑料袋、塑料箱裝蔬菜,裝米面,看似方便了,但比起缸來,似乎有些潦草,總感覺少了些什么。更有趣的是,不知從哪里,總會傳來一些消息,說某人在鄉(xiāng)間發(fā)現了一口缸,是古物,撿了漏,好運氣。傳來傳去,顯得愈發(fā)神奇。不過,這樣的缸,我聽了無數次,卻一次也沒有真正看到。
張立新: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多家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