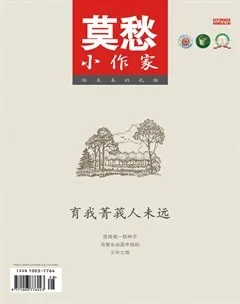沉睡三千年,三星堆一醒驚天下
三星堆又上熱搜了!近日,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新發現陸續公布,6座坑共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其中,7號坑發現一件龜背形網格狀器,外側為網格狀橢圓形,內有一個背部駝起的橢圓形完整玉器;還有一件倒立頂尊人像,高近1.5米,由三部分單獨鑄造后焊接而成。這些都是首次出現。
三星堆的發掘之所以備受關注,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出土的文物在不斷地“創造歷史”、填補空白,給考古界,乃至歷史學、社會學、文明與文化等諸多領域以新知。
文化的確認
三星堆的驚世發現,始于當地農民燕道誠的一次車水淘溝,他偶然挖出了一坑玉石器。這自然引起了古董商的注意,就在古董商們于廣漢爭相搜取玉石器之時,一位對三星堆文化的早期認識與保護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美籍教授葛維漢。1933年秋,葛維漢最早提出了在廣漢玉石器出土地點進行調查和發掘的構想。
進入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后長達三十余年,不曾中斷,三星堆文化也從此得到確認。
在發掘期間,考古人員一并對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測——“在三星堆遺址東、西、南面筆直走向的土埂是由人工疊筑而成,可能是遺址內城墻”。這一推測為后來的正式發掘所證實。這次發掘報告以《廣漢三星堆遺址》為題發表在1987年第2期《考古學報》上,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到了關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問題。發掘者認為,通過這一次發掘,進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遺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征的,有別于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并且它已經具備了夏鼐先生提出的命名一種新考古文化所必需的三個條件。
其一,這種文化的特征不是“孤獨的一種”,而是“一群”,如陶器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鳥頭把勺等特殊器型,往往在各遺址中伴出。其二,這種同類型的古文化遺址,在四川地區的發現已不僅是一兩處,而是在成都青羊宮、羊子山,廣漢月亮灣,閬中城郊,漢源背后山和麻家山等多處都曾發現過。其三,“必須有一處做過比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此以前,盡管材料有限,但不少專家學者已對這類遺址做過不少研究和探索,這一次對三星堆的發掘和整理,正是對這類遺址的進一步研究,并對其時代、分布以及同其他文化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綜上,發掘者認為給這種特殊的古文化賦予一個名稱的條件已經具備。因此,他們建議將這種古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古蜀國的神秘
1986年8月23日,新華社將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重大發現告之于世界。一時間,這個川西平原上原本很不顯眼的小村莊,令整個世界為之傾倒與震撼。奇特夸張的青銅藝術、侈麗雍容的金箔技藝和精美神奇的玉石雕琢,構成了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燦爛結晶。此外,眾多的象牙在三星堆遺址集中出土,也反映了古蜀文明的某種特質,更給后人留下了諸多謎團,耐人尋味。
從原料上看,不同區域的礦山,成礦時間不一樣,鉛同位素會不同。所以,分析銅器的鉛同位素,就可以追溯礦產來源。根據初步建立的巴蜀地區銅器分析數據庫可以比對發現,三星堆時期的銅器和之后成都平原數百年間生產的青銅器,原料并不一樣。成都平原有原料而不使用,恰恰有可能說明:三星堆銅器并非在當地生產。
從技術上看,常識告訴我們,某一區域的鑄銅作坊,使用的鑄造技術是相對固定的。考古學家在三星堆發現,有很多相同的器物卻使用了不同的鑄造技術,例如青銅面具的耳朵與面部的連接方式就至少有分鑄式和一次性鑄造兩種方式。技術來源的復雜或許也能說明:三星堆銅器的來源并不單一。
三星堆不只有巨大的神樹和面具。和大型青銅器相比,七號坑發現的小小銅鈴,同樣是了解歷史的絕佳線索。在距今40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就曾出土過一例銅鈴,那是我國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紅銅鑄就的銅鈴,開啟了中國別開生面的青銅器鑄造之路。二里頭遺址著名的綠松石龍,其中部也有銅鈴。到了殷墟,銅鈴大量出現,并產生了多種用途。銅鈴在三星堆的大量出土,或許也暗示著它與中原文化的聯系,甚至是對中原禮樂文明的認同與接納。
考古學的目的之一是透物見人。透過李白“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詩句,很多人猜想三星堆是一個閉塞的文化。事實上,三星堆所展示出來的與周邊世界的聯系,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青銅礦產資源的有限性與稀缺性,必然引發原材料與產地、使用地之間的遠距離大范圍流動;技術的壟斷性、工匠的專業分工也必然帶來人員的遷徙與移動。借助青銅器的生產,我們看到了不同地區資源、技術與文明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
科技考古時代
在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中,現代化科技的助力貫穿于文物勘探、發掘、提取、保存、修復所有環節,這讓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發掘邁入科技考古時代。
建在玻璃方艙里的挖掘現場,通過高科技影像手段,讓現場信息的收集變得更加豐富、精確和全面。方艙頂部安裝了八臺四百萬星光級的網絡攝像機以及一臺工業全景相機,可以對整個考古過程進行全記錄,專家也可以通過這些設備,遠程實現對文物的“會診”。
在考古發掘現場,首次設置了考古實驗室,可以看到文物細節的視頻顯微鏡、可以現場分析文物材質和含水量等信息的高光譜成像儀等,都被搬到了考古現場。譬如超景深顯微鏡用在現場微痕觀察和微附著物觀察上,保證器物上有紡織品或者血液等附著物時,在現場直接進行觀察。在文物提取與保存的環節,新材料、新方法也運用其中,高分子材料的使用,能將酥軟的象牙很快提取上來。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配備了史上最“豪華”考古隊陣容,整個發掘工作由四十家考古發掘、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數字化服務等單位聯合攻關,考古學、歷史學、物理學、化學、古生物學、古地質學、古環境學等多個相關領域學者近二百人參與。
一件件珍貴器物破土而出,勾勒出三千多年前青銅文明的嶄新輪廓,很多神秘等待開啟,很多答案等待揭曉,三千多年前那個生機勃勃的世界等待復原。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可以說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個奇跡。由一個考古遺址的發掘,發現了一個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寫了一部文化史。
(本文綜合自《一醒驚天下》,周新華 著,浙江攝影出版社,2022年03月,公眾號“人民日報評論”“光明日報”“央視一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