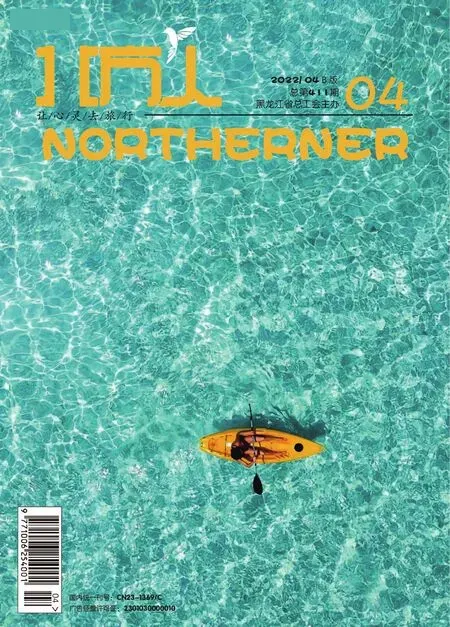“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文/賈樟柯
1998年,我帶著《小武》去參加柏林影展青年論壇。那年我已經二十八歲了,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國際電影節,也是我的第一次歐洲之行。一個人從北京搭乘漢莎航空的航班出發,起飛后不久大多數乘客就都睡著了。機艙里異常安靜,我卻大睜著眼睛不肯入眠,腦子里不時閃過法斯賓德或文德斯鏡頭下的柏林。近十個小時的航程我是在冥想中度過的,一會兒柏林、一會兒北京、一會兒我的故鄉汾陽。
多年之后我想,我之所以到現在還熱愛所有的遠行,一定跟故鄉曾經的封閉有關。而所有遠行,最終都能幫助自己理解故鄉。的確,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那時候兩德統一還未滿八年,人們習慣上還把目的地稱為“西柏林”。可我偏偏對“東柏林”感興趣,放下行李拿上一張酒店的地址卡,我便在暮色中坐一輛公共汽車出發了。每到陌生之地,我都喜歡這樣漫無目的地游蕩,喜歡在偶然中遭遇一座城市。公共汽車從動物園附近出發,穿過城市向東而行。沒有跟當地人說一句話,車窗外的建筑像是能告訴我一切。西邊兒的馬路基本上呈放射狀分布,路邊建筑的設計也表現出開放狀態。可一到東邊,橫平豎直的街道和平板的辦公大樓就似曾相識了,國營體制的感覺毫不掩飾地經由建筑表現了出來。
我下了公共汽車,遙望西柏林方向。遠處大廈上奔馳汽車的廣告在夜幕中旋轉閃爍。那時,不知為何我腦子里突然冒出一個詞:資本主義的柏林。這里的觀眾能理解社會主義的汾陽?我問自己。《小武》拍攝于我的老家汾陽,那里塵土飛揚、城外的軍營每天軍號陣陣。真奇妙,再過兩天,我就要將故鄉的風景人物放映給異鄉人看了。
1998年的柏林電影節還有一個導演,也用電影將他的故鄉帶到了柏林。這部電影的片名就叫《小鎮》,導演是來自土耳其的錫蘭。錫蘭1959年出生在伊斯坦布爾,他是在當兵期間看了波蘭斯基的自傳,開始愛上電影的,他常自編自導自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現在自己的電影中。在看《小鎮》之前,我從來沒機會知道土耳其的小鎮會是什么樣的,也不知道那里的人們怎樣生活著。
坐到電影院里,燈光暗下、銀幕閃亮的時候,才知道《小鎮》是一部黑白電影。電影一開始就是小鎮漫天的大雪,這是我熟悉的。原來土耳其小鎮上的孩子們跟我一樣,只有天氣的變化才能給一成不變的生活帶來新鮮感。這時,銀幕上一個孩子穿過山巒去上學,他進入教室,把雪打濕的鞋子脫下來,烤在火上。火爐溫暖,窗外寒冷,這不就是我小學時冬天的記憶嗎?接著,孩子脫下他的襪子,掛在火爐上,襪子上的水滴掉在火爐之上,“吱吱”蒸發的聲音一點兒一點兒滴在心上。
錫蘭的《小鎮》是那種用電影語言超越了語言的電影。你不用看懂對白字幕,單是通過電影的畫面,我們已經能夠理解導演的世界。錫蘭是一個能把氣候都拍出來的導演。那種雪后的寒冷,雪地上玩耍的孩子們身體里面的熱氣,被雪凍得麻木的雙腳,襪子上掉下來的水和炙熱的火爐相碰撞冒出來的蒸汽,都是這部電影的詩句。我不喜歡跟蹤電影的情節,對我來說看電影最大的樂趣,是看導演描繪的詩意氛圍,沒有詩意的電影對我來說是沉悶的電影。

記得在黑澤明導演生前,侯孝賢去拜訪他。黑澤明問自己的助手:你知道我為什么喜歡侯孝賢的電影嗎?他的助手講了很多哲學的命題,黑澤明搖搖頭說:不是,我在他的電影里能看到塵土。
錫蘭導演呢?我想我在他的電影里能看到天氣。
《小鎮》的聲音世界讓我迷醉。在他的電影里面,夸張了很多聲音,那些聲音被他從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里提取出來,給我們一種熟悉的陌生感。水滴在火爐上被炙烤蒸發的聲音,大自然里面動物的鳴叫聲,遠處隱隱約約人的喊叫聲。鳥叫蟲鳴、風聲雷鳴這些被我們在日常中忽視的聲音,在影片中被提煉出來,強調給我們。這些聲音,幫助我打開了記憶的閥門,甚至能讓我想起我從未回顧過的歲月。
在《小鎮》中錫蘭拍了很多微觀世界的鏡頭,動物,樹木,一草一木的細節、紋路、肌理。樹木、動物這些與我們共存于這個世界的生命,我們從未這樣專注細心地凝視過它們。當錫蘭帶著攝影機去凝視被我們忽略的大自然的時候,其實我們看到的是被我們忽略的自己。我們內心的感受變得如此粗糙,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耐心地聆聽、凝視過這個世界。
通過錫蘭的電影,我突然發現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故鄉遠在他鄉,因為無論在土耳其電影,還是哈薩克斯坦、伊朗電影中,我都找到了我的故鄉。我自己解答了自己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柏林一定有人能看得懂我的《小武》,我相信他們在我的電影里同樣可以找到他們的鄉愁。
(摘自臺海出版社《賈想 II:賈樟柯電影手記 2008—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