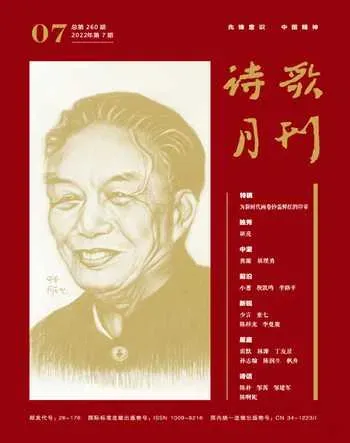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向杜甫致敬”中的探索與掙扎
——谷禾詩歌閱讀札記
陳樸
在日益沉穩有力的詩歌寫作中,谷禾在詩學變奏的試驗場中強身健體,在詩學疆域拓展上精準發力,從個體突圍到整體凸顯,經過反復的精神鍛造、洗禮、淬煉和多重語言探索,詩學定位和寫作方向日益明確,越來越呈現出在根脈堅守中探索復雜多元性詩歌的廣闊空間。
一、拒絕偽抒情與沉穩的變奏
谷禾的詩歌一直堅守著拒絕偽抒情的底線。在網絡自媒體多種載體不停衍變、鋪天蓋地的這些年,詩歌評論界所共同關注的“同質化”詩歌寫作,很大程度上與詩人普遍存在的偽抒情寫作有著巨大的關聯。作為資深從業者,谷禾沒有受潛移默化的流俗影響滑向偽抒情,而是時刻保持著詩歌的自覺、警醒與良知,踐行著詩人的語言使命。
當下和谷禾一樣從山花遍野、牛羊遍地的鄉村,一步步走到城市,在城市立足的詩人很多,但像谷禾一樣一直自稱農村人的卻并不多見,“谷禾”作為筆名,也透射出他對鄉村的懷念之情,這樣本真、樸素、坦誠的詩人,自有他的過人之處。
落在身上的雪
把我變成另一個人,變成雪人
像生命的痛苦把我變成痛苦的人
……
走在雪中的人,變成了一樣的雪人
走哪兒都一身雪,好像這些人
一直是雪的一部分
是“雪”這個詞
——《落在身上的雪》
正如堆雪人時候,人們常常會忘記先有雪然后才有雪人一樣,很多時候,詩人也會像堆雪人一樣出現短暫的“語言的休克”,誤以為只有和孩子玩的時候,才會出現雪人。其實不然,任何事物都有其源頭,“走在雪中的人,變成了一樣的雪人”可謂和“落在身上的雪/把我變成另一個人”有著殊途同歸(“落在身上的雪”)的詩學效應。萬物皆可入詩,在同等深入觀察體驗之外,經驗豐富的詩人能自然中做到游刃有余而毫不費力。
從詩集《鮮花寧靜》到《坐一輛拖拉機去耶路撒冷》,再到《北運河書》《世界的每一個早晨》,谷禾一直以對信仰、愛和詩學標準的不變,回應著不斷豐富的內心之變,在忠實于詩歌的同時探索著“向杜甫致敬”的詩學空間維度。
四十年前,我還沒有出生,只把母親當親人
三十年前,我九歲,把所有的飯當親人
二十年前,我十九歲,只把青春當親人
……
當我八十歲,睡在墳墓里
所有的人都視我為親人,但你們已經找不見我——
—《親人們》
近年來,“杜甫熱”已成為詩壇一個聚光點。“人間要好詩,首先需要一個好詩標準。可是,標準在哪?我的體會是,詩可以沒有標準,但好詩一定要有標準。這個標準不妨暫定成杜甫,權且把杜甫作為詩歌的最大公約數。”谷禾詩集《坐一輛拖拉機去耶路撒冷》 的代序標題即為《向杜甫致敬》,他在其中寫道:“只有從杜甫開始,我們才看到了通達現代人生活的日常之詩,詩人的筆下不只見天地,更見眾生。”過濾掉太多細碎的片段后,足可見谷禾內心深處深埋多年的對杜甫的敬仰和推崇,經歷人世間諸多喜怒哀樂生離死別后,沉穩的變奏自然是一個詩人最好的狀態,“所有的人都視我為親人,但你們已經找不見我”,這般無雜質的語言是深入里層的折射,并非表象的陰影。在超越詩學表達范疇外,哲學語境的探索中處處可見詩人在語言與思想并肩齊飛時的艱難掙扎,這是一個詩人潛心修為、為詩憔悴的艱辛探索,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見證。
二、潛心詩學修為的自覺與警惕精美的庸俗
網絡自媒體時代,很多詩人已進入古人“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狀態,安靜與孤獨成為時代的稀缺品質。“鮮花開在那里。鮮花/寧靜//鮮花開在草原,河谷。鮮花/開在山坡//鮮花開在孩子和羔羊的眼睛里。鮮花//——開在墓地//風吹……風不吹。鮮花,如此寧靜//大地遼遠,天空無限/活著與死去的人,一次次從芳香中走過”(《鮮花寧靜》)。谷禾這首代表作顯而易見就是一首自覺潛心詩學修為之作。在摒棄煩瑣的意象之后,他獨辟蹊徑地以“俗”(鮮花)求“新”(寧靜)。其實寫詩也就是詩人提筆為刀與字詞和意象的戰爭,只要打敗無用之詞、軟弱之詞,自然就是勝利者。“活著與死去的人,一次次從芳香中走過”,如同子彈穿透鋼板一樣直抵人心,讓一些真實存在而又不易察覺的事物明亮起來,如同給近視者戴上眼鏡,入木三分中將模糊的事物更加清晰地給世人呈現在眼前。
“一個成熟的詩人更要警惕精美的平庸之作”,他只有在自覺與警惕之間自如穿梭,才能寫出驚艷之作。
這是我很久以來想說的。
不只愛親人,朋友,同宗,同種,
還要去嘗試愛那不相干的人,
你當然不是神,你是眾生,有什么
關系呢?去愛吧,去愛那石頭,
石頭上荒蕪的雪,被藍色
天空覆蓋的曠野,骯臟的河流,
高低俯仰的樹,枯萎的葉子,
黑暗泥土里流亡的骨頭。去愛吧,
去愛那耕牛和羔羊,它眼睛里的
隱忍和驚惶。也愛那撲上去的屠夫。
不要詛咒他,去憐憫他,望著他
突生悔意,緩緩放下舉過頭頂的刀子
——因為你的愛,善在他心底萌芽了。
——《嘗試愛那不相干的人》
谷禾在詩學締造中并不認同完美主義的論斷,他堅信詩歌的殘缺美,善于將根植于大地和內核中的東西挖掘出來,善于在探索中檢索自己想要的效果,他從不奢求技術的光束能在自己身上多照一會兒,而深信讀者雪亮的眼睛不會被永遠蒙蔽。“嘗試愛那不相干的人”是詩人內心的獨白,也是對自己詩歌格調的最好詮釋。
三、“向杜甫致敬”與“向現實深挖”
漢語新詩在走過百年歷程后,很多詩人在不斷學習西方詩歌的同時,又提出了回歸傳統,從母語中吸取營養的主張。在我看來,這種回歸并非藝術的倒退,而是給予現實的一種重新認識和發現。霍俊明在對谷禾的評論文章《“杜甫詩傳”第三頁——關于谷禾的“現實敘事”》一文中曾寫道:“每次讀谷禾的詩,我總會想到與我們同時代人密切粘連在一起的恍惚而又真切的現實感,詩歌在谷禾這里首先承擔起了精神傳記的功能。”沒有現實描寫的詩歌就是沒有人間煙火、不接地氣的詩歌;“向杜甫致敬”的寫作方式有很多,但是“向現實深挖”無疑是要經過的第一道門檻。
扛攝像機的家伙走來
三三兩兩的,他們的廣角鏡頭
移過河底挖掘的民工,
定格在一根濕漉漉的木頭上
紅色工程車的巨臂繼續向下,向下
抱緊那木頭,再,向上——
溫柔地移向,河岸邊聚集的歡呼人群
圍過來的人們忙著用卷尺測量
用扳手敲擊。偶爾也被招呼過來,
結結巴巴對著話筒憨笑
——《河底清淤現場》
生活現場是詩歌的生命線。“向現實深挖”對詩歌自身的含金量有著核心的作用,可以從切入點、痛點、記憶點中形成三點一線(主線)的力量,給人猝不及防的視覺或聽覺體驗。從“定格在一根濕漉漉的木頭上”“結結巴巴對著話筒憨笑”等詩句可以看出,谷禾在現實書寫的掙扎中有過前后張望的經歷,也有過降速、停止、再超速的思想轉變。詩人在掙扎中慢慢握緊了偏移的方向盤,喘氣的頻率在掙扎中也慢慢恢復正常。谷禾詩歌的現實介入是詩意介入的延伸,是與散文的現實介入有著本質區別的。
在谷禾這里,“向杜甫致敬”從來沒有成為一句空話和噱頭。百年來,漢語新詩學習杜甫的詩人很多,但大多只是照貓畫虎學到皮毛而已,學到精髓者罕見。不敢說谷禾是學到精髓者,但谷禾必定是學到深處的詩人。如何讓漢語新詩煥發生機和活力,重現中國古典詩歌的輝煌?如何古為今用,推動漢語詩歌更好發展?要破解這樣的難題,僅有“向杜甫致敬”的自覺還是遠遠不夠的。谷禾在“向杜甫致敬”的探索與掙扎中,已經寫出了諸多優秀詩作,非常值得更多的研究者關注。在未來的日子里,這也許會成為一種共識——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忠實讀者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