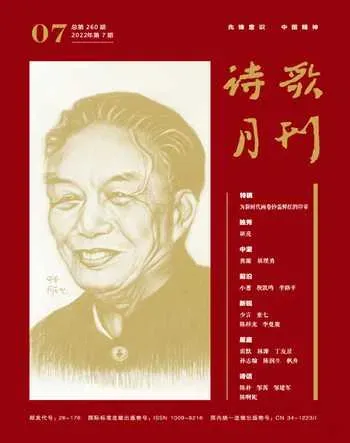語(yǔ)象的智性與古典藝術(shù)的交鋒
——傅榮生詩(shī)歌考察
陳啊妮
傅榮生的詩(shī)寫(xiě)得很輕,短小精悍,行神如空。這種輕是語(yǔ)言的簡(jiǎn)潔干練,精神的通透,以及情感內(nèi)蘊(yùn)的有力填充。返虛入混闊,積健為雄思。從文本開(kāi)篇,傅榮生的詩(shī)歌就有立意和聚力于思想性拔高與凈化的寫(xiě)作動(dòng)機(jī)。在他的 《辯護(hù)》《結(jié)繩記事》《湖心島》《南方來(lái)信》《戒律》等作品中,詩(shī)人已然對(duì)自然質(zhì)樸的生命體驗(yàn)和抽象的精神刻畫(huà)彰顯出其不可多得的語(yǔ)言造詣。
俗常中的事物,意象和隱喻都是傅榮生隨意擷取的天然寫(xiě)作資源,詩(shī)人在創(chuàng)作中善于建立個(gè)體象征的獨(dú)特塑形,對(duì)于細(xì)節(jié)的挖掘是經(jīng)過(guò)深度思考的。這些深度思考的過(guò)程在詩(shī)中甚至是完全透明的過(guò)程,對(duì)于事物表象的審視,詩(shī)人更加側(cè)重它們的象征深意,而在剔除常規(guī)審視和自然抽象的選擇中是智慧的,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出了語(yǔ)言果斷的行動(dòng)力。“一滴雨/在枝條上發(fā)呆/鳥(niǎo)在微漾中走神/百年銀杏/看守著村落/銹跡斑斑的寂寥/和此時(shí)的遲疑/在風(fēng)里/我看到了/紫陽(yáng)花的糾結(jié)”(《殤》)。從某種意義來(lái)說(shuō),傅榮生在整體象征與局部象征的平行運(yùn)思中側(cè)重于反論式象征,就如《殤》中“紫陽(yáng)花的糾結(jié)”,詩(shī)人以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位移詩(shī)緒的高漲,無(wú)疑“殤”的整體象征不斷在分解情感的疏離,才使“糾結(jié)”具有不必遲疑的隱痛。
將自然萬(wàn)物人格化移情呈現(xiàn),對(duì)于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啟迪,詩(shī)人傅榮生的詩(shī)歌給我們帶來(lái)了兩種顯著的美學(xué)效果和精神價(jià)值。其一是傅榮生詩(shī)歌的古典審美自覺(jué),以及直樸詩(shī)意的素描體系呈現(xiàn),全力以赴在短詩(shī)中展現(xiàn)博大壯闊的萬(wàn)物象征和精神內(nèi)蘊(yùn)。傅榮生的詩(shī)歌大多在七行到十行,與古典節(jié)數(shù)貼近,對(duì)一個(gè)意象的語(yǔ)言陳述拓展,詩(shī)人獨(dú)創(chuàng)的詩(shī)歌體制在韻律和諧的追求上,是向古典詩(shī)歌致敬和拓新的雙向奔赴。首節(jié)鋪墊,第二節(jié)主旨揭示,后節(jié)收尾燭照全詩(shī),都是承上啟下的自然過(guò)渡。“窗外/蟲(chóng)吟斷斷續(xù)續(xù)/那節(jié)奏/像在替我們分配時(shí)間/醒著的/或夢(mèng)著的人/都領(lǐng)走了屬于自己的部分/在鳴叫的間隙里/有人懷揣云梯/跟著起伏的群山徹夜奔跑”(《聲聲急》),在短短幾行之內(nèi)運(yùn)思,生發(fā)出更高的主題意蘊(yùn)。“窗外”是語(yǔ)境推衍,“蟲(chóng)吟”“云梯”都是時(shí)間的浮游姿態(tài),“跟著起伏的群山徹夜奔跑”是層層鋪疊的情感躍升,無(wú)疑“聲聲急”在末節(jié)陡然增強(qiáng)的詩(shī)歌回音是劇烈的,最終為詩(shī)歌主旨營(yíng)造了足夠的氛圍。
傅榮生對(duì)命運(yùn)形而上的思考是深度的,一種沉靜、睿智、禪意的古典審美運(yùn)思像烙鐵一樣灼疼我們的神經(jīng)。如在《成子湖的蘆葦》一首:
被詩(shī)詞反復(fù)傷害過(guò)的
這片蘆葦
拒絕成為任何比喻
他們安靜地站在自己的蓮花里
我來(lái),沒(méi)有帶上紙和筆
只帶著泊在傳說(shuō)里的一座橋
和隱隱約約的水岸
把蕩里的落日,引渡
作為一個(gè)被重復(fù)使用的經(jīng)典意象“蘆葦”,詩(shī)人開(kāi)始傾聽(tīng)它們作為喻體的魂之所系,“被詩(shī)詞反復(fù)傷害過(guò)的/這片蘆葦/拒絕成為任何比喻”。對(duì)“成子湖”這片土地致以深切的情誼,“蘆葦”似乎是無(wú)法回避和不可剔除的象征,而詩(shī)人反作用于一種慣性的形象設(shè)象,“我來(lái),沒(méi)有帶上紙和筆”,對(duì)自然抽象的深愛(ài)是博大的,被虛幻統(tǒng)攝成一種滌蕩著風(fēng)之氣息的“蘆葦”,在某種隱喻的思想行走中復(fù)活了。而詩(shī)人“把蕩里的落日,引渡”,則是構(gòu)成了生命情感的持重釋放和消泯。一個(gè)立體的、多維思想元素的“成子湖”的蘆葦是豎立感的,亦是詩(shī)歌藝術(shù)審美下排他的蒼莽呈現(xiàn)。這里不得不說(shuō),傅榮生的語(yǔ)象畫(huà)風(fēng)若“長(zhǎng)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這些司空見(jiàn)慣的意象“蘆葦”“落日”是經(jīng)典的重塑,是古典另類的唯美,具有修辭骨感的精神厚意。
傅榮生有學(xué)者的洞察耐心,在他的詩(shī)歌文本中,情感抒發(fā)和理趣哲思都有較為固定的語(yǔ)言基調(diào),是一種睿智、飄逸、靜默的東方審美,一種富于沉潛和勃發(fā)的語(yǔ)言心態(tài)。其實(shí)詩(shī)人對(duì)短詩(shī)的整體思想見(jiàn)地的營(yíng)造是難度最大的。長(zhǎng)詩(shī)有足夠的思想語(yǔ)言舒展空間,越長(zhǎng)越好,傅榮生的短詩(shī)卻反其道而行之。“河岸柔軟起來(lái)/淺水照出萬(wàn)物的模樣/溪邊/一只白鷺/抖掉身上多余的影子/把脖頸往塵世里伸了伸/振翅/消失在天際/——就像不愿融化的雪/又返回天空”(《白鷺》)。在此詩(shī)中,詩(shī)人詩(shī)緒的回潮起落是精微而空靈的,前兩節(jié)的托舉結(jié)構(gòu)出于修飾的刻意,也追求吟誦的語(yǔ)言實(shí)用性,對(duì)于藝術(shù)化推衍的詩(shī)意架構(gòu),傅榮生摒棄文字的拖沓,內(nèi)容的繁復(fù),無(wú)疑這短短的行數(shù)為“白鷺”貢獻(xiàn)了語(yǔ)言象征的自勵(lì)。“抖掉身上多余的影子”是一種形而上學(xué)的概念寫(xiě)意,著力強(qiáng)調(diào)和闡釋詩(shī)歌的思想空間。而在結(jié)尾的斷裂中,“就像不愿融化的雪/又返回天空”,用“雪”烘托“白鷺”的圣潔寫(xiě)意,寄寓引申一種介乎精神邊界的思索,這是一種未經(jīng)教化的野性的喚醒,也是詩(shī)人一種直覺(jué)和慣性的思想行走實(shí)踐。
可以確定的是,傅榮生對(duì)于生命深度考察的意義在于,在精神意向上對(duì)于生命真切的感受和覺(jué)知,在詩(shī)歌文本中成為思想顯像不可回避的佐證。詩(shī)人不是完成某種人類的精神救贖,就是對(duì)于生命深深地悵惘和贊美。在傅榮生詩(shī)歌中,哲學(xué)不是死板的教條,而是他的語(yǔ)言活水,是潺潺流動(dòng)的價(jià)值認(rèn)同。如《結(jié)繩記事》的文本呈現(xiàn):
當(dāng)我們?cè)噲D用文字
解開(kāi)一根繩子上的死結(jié)
才知道語(yǔ)言已經(jīng)荒廢多時(shí)
我們只能順著平滑的部位
往前,或往后探尋
死結(jié),只是時(shí)間較勁或停頓的地方
多年以后,我們才會(huì)明白
繩子上如果沒(méi)有死結(jié)
許多事情往往無(wú)從談起
“結(jié)繩”首先是詩(shī)人自我思想的一個(gè)“結(jié)點(diǎn)”,這是一個(gè)謎之“死結(jié)”,當(dāng)詩(shī)人將膂力傾注于人類命運(yùn)的深刻意味,那么無(wú)常如雪就不再是一種語(yǔ)言的渲染,而是一種理性客觀的觀照,“死結(jié),只是時(shí)間較勁或停頓的地方”。在“結(jié)繩”用作象征去派生厚重的生命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中,無(wú)疑這是一種疼痛的語(yǔ)言出鞘,閃著命運(yùn)無(wú)常的寒光和晦暗的沉重思想。詩(shī)人貌似不動(dòng)聲色,而情感的走向是價(jià)值的最終固定,“許多事情往往無(wú)從談起”,這一不斷強(qiáng)化的否定之否定不斷增值著個(gè)人生命的自足、豐盈以及釋放,而不僅僅是一種自醒的體悟。“結(jié)繩記事”其實(shí)是完成了一個(gè)思想完全打開(kāi)的運(yùn)思過(guò)程,詩(shī)人以平緩的語(yǔ)氣導(dǎo)出思想的癥結(jié),這是一首有著生命哲學(xué)意味的“繩索”。
古典鋪排,理趣哲思滲透,以傳遞日常自足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為審美基底,在智性的語(yǔ)象氣質(zhì)里,傅榮生的詩(shī)歌藝術(shù)表述是有著深刻思想與情感的。以詩(shī)歌體式傳播自我生活覺(jué)知,傅榮生在突破現(xiàn)代詩(shī)語(yǔ)與格律束縛中做出了成功的嘗試,生命自由的形式與詩(shī)歌自由意志力的強(qiáng)勁結(jié)合成為語(yǔ)言的化合劑。“要多少春風(fēng)/才能吹綠一個(gè)人的空白/長(zhǎng)出蓮花和糧食/順便長(zhǎng)出一片竹林/為此/我曾叩問(wèn)過(guò)一條/解凍的溪流”(《空白》),傅榮生在細(xì)膩的詩(shī)思迂回中肆意揮灑深刻的詩(shī)歌思想內(nèi)涵:空靈、禪意、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