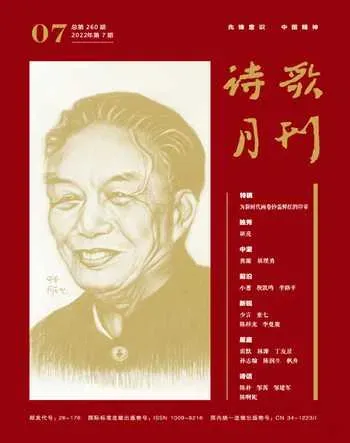昌蒲的夜(組詩)
孫志翰
圓舞場
我常坐在小山頂上遠眺
南湖公園的露天舞場里人影晃動
想必是退休的舞蹈者
快三、慢四、午夜倫巴
鼓點上的進退、轉折多么嫻熟
走到近前更令人暗嘆
一對對黑色蝴蝶
一絲不茍、千錘百煉
腰身的擰動隱忍而多姿
另外,還有人繞著圓舞場沒完沒了地跑圈兒
是中年、青年、中青年
他們偶爾兒朝圈內不解地瞥上一眼
卻氣喘吁吁,肢體僵硬
仿佛找不準目標
像些馱重生物
正馱著重物前行
高壓線所能解決的問題
電線桿之間的眾多瓜葛
成為鳥類的落腳點
麻雀飛累了,在其上停歇
或者是飛得太高,用來呼喚同伴
站在那里,經常看到人類排起長龍
涌向鐵皮車廂的洋流,逐漸凍結
通電后
時光劇烈地膨脹
巫山烤魚
不能仿古人炙魚于江上
或者燒一截梓枝歸于自然
對魚的肉體、肌骨、膠原與蛋白
作出精確的定義
我們終于使這個種群停止思考
上鉤與否不再只為果腹
在食客的汪洋里
打破了四川話的禁忌
可以不指摘炭火的短命
正宗原產地頻現貓膩,就像哲學問題
辣椒的語言迅速聚積
如果這是守恒的能量將如何消解?
一根稻草睡進一大片蛙鳴
小暑之夜,焚香、翻書
洪流在巫山草魚的十指間穿行
我逢人便講那水果糖有多甜
走南闖北,鐵盒磨掉了斑斕
微笑如開出的銅花
我試圖將它復原,逢人便講那從前的水果糖
后來連唇齒都磨薄了
外表油滑世故,不再苦中作樂
想起那塊糖入口即化
全身肌肉都追不上那快感的消融
我把鐵盒里最甜的水果糖吃掉了
理發店外遇雨
活于幻象并愛上了幻象
——雷平陽
要理理發了
坐在門前的木椅上
等沙沙不休的秋雨收嗓,噤聲
或者干脆噼里啪啦的鬧騰起來
助理員在丈量廣告牌
更大瓦特的幌子被給予厚望
人們為何信奉新時尚
一件晃晃蕩蕩的赭黃色風衣
已不能列入實用主義
小辮兒不再是異象
即使周圍統統被削光
好像珠峰上無人認領的線索
他挽起女友水波瀲瀲
足下若有浮萍
我目送火烈鳥一樣的幻象離去
卻驚慌失措于他突然回頭
將我視作雨中的稗草
詩人何為
不做冷漠的鄰居,熱心的敲鐘人
我愿終生守護
幾只找上門的流浪貓
幾個喊出我小名的癡情者
不能少,也不盲目擴張
分享一桌晚餐的人
厭惡詞中糟粕
哄抬悲劇
大路只走一邊
處心積慮死,凜冽地活
與之碰杯
衣衫襤褸的人,都算上
菖蒲的夜
西海的風光直逼江南
古老的亭榭燃起橙色火焰
玻璃落地窗敞開心扉
一步之遙的濕地上
千屈菜,蘆葦未獲得植物學優勝
菖蒲開出豐饒之花
花上的露水始于每一個晨醒
可它已被禁足
一排排黑色陶缸使人心生哽咽
誰不是禁錮于奇異的命運
像上世紀的荒誕展覽
雙頭蛇,同體兄妹,花瓶人
仍震驚著我
仍使我竊喜
看似尚無歹毒之意的現實
允許我的肉身到處走走
看看菖蒲的夜景
落葉
我不得不為一片葉子感到欣慰
古老的使命,對于秋天
這個命題,獲準一次候鳥式的飛行
無人察看同一處的新生之葉
是否因為放棄而洗心——
同烈日較量一場后,每一片落葉
都要完成幡然醒悟的追憶
郊外的深秋
一排排烏黑的禿樹緘默著
緋紅色的剩果心事沉重
它的中年之香如一條細細的絲帶溜過來
剛碰鼻翼就滑遠了
連綿的薄霧連同遠處的油彩青山
統統不屬于我
焦急趕路的目的地是農家宴
后院的魚塘緊挨停車場
43號釣坑上的人陰沉著臉“打窩子”
黃泥漿水面沒有鯉魚高高躍起
魚竿何時擰成拋物線
5號線何以性情剛烈
敏感多疑的魚漂兒何時晃動
釣魚的人多了,一塘渾濁
麻雀居無定所,烏鴉困意全無
輪番搖曳著高壓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