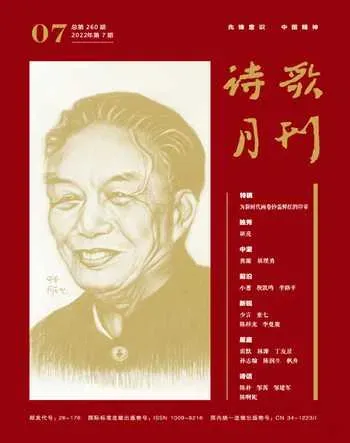片羽(組詩)
胡亮
六月
苜蓿花特別擅長紫色,而微型藍蜻蜓
則精通短暫。幾米外的小河
反復練習著清澈,以便嫻熟地
洗去我雙頰的土塵。
紫色像微瀾那樣悅耳,而短暫像錦雞
那樣將最長的尾翎也縮回了灌木叢。
我特別擅長轉動群山,而你則精通蔚藍。
憑窗
我的近視眼再次受教于落日。一列火車逆行,
駛離了暮年,停靠在中年。
這是中年新家:所有窗戶都朝西。
這是中年涪江:在鋁合金的方格里豁然開朗。
萬神殿
鐵角蕨又多又密,好像是濕地的汗毛。
八角金盤略高于鐵角蕨,風車草
略高于八角金盤。銹毛蘇鐵,
海桐,龍爪柳,芭蕉,槐樹,還有
金葉水杉,搭建著青黃相接的天梯。
我的驚愕步步高,
翻越金葉水杉,仍未企及那最高的真實。
巨人傳
如果麻雀的羽毛有點丑,如何才能獲得
錦雞的羽毛?……聆聽!
如何才能獲得鷹眼或馬蹄,
還有翠鳥、野花或青藏高原的肺腑?
……聆聽!
我像蕨類植物那樣聆聽著大地,
又像大地那樣聆聽著掉落的繡花針!
無盡
解開一叢叢巴茅的發辮,從這個野湖的耳垂
走到額頭。我們環行小半圈,
止步于眉間。湖變得越來越大,
剩下了越來越多的發辮和幸福。
得閑
我已經找了一個多小時,額頭冒出了
一層細汗。楠竹做的筆筒,
柏木做的抽屜,橡膠木做的書架,
復仇般地消化了房間里的一切
鐵器。一盆綠蘿從書架的第五層
垂落到木地板,
就像司空圖的二十四個妙諦
或飛瀑。是的,我要找到那把小剪刀,
我要剪掉從綠蘿上濺出來的一片黃葉。
小樹林
“植物才是遺物!”——很少有人能領會
這句話的綠意。兩棵藍花楹,
一棵黃葛蘭,幾棵香樟,
以及若干叢斑竹,哪里還具有什么
“當代性”?綠意勾兌了秋意,
秋意勾兌了古意。就在這條蔥蘢之路,
我們會碰上張船山,過一會兒,
還會碰上蘇子瞻。小樹林圈住了小茶亭,
小茶亭圈住了十二平方米的南宋,或
三個小時的東晉。詩人們,
青年們,明天就是白露,
快讓我們臨摹每棵樹,臨摹它們的綠意!
不要羞愧于笨手笨腳,
而要羞愧于“當代性”結出的老繭……
分寸
我抓住一只花腳蚊,它又從指間飛走了。
可見——
它的前生:一條赤鏈蛇,一只短尾鱷,
或一只黑盾胡蜂,當初對我絕無惡意。
魔術師
我要把剛摘下來的一顆葡萄,拆分成
一百顆。要把葡萄上的一克新雨,
拆分成一千毫克。我要在更慢里求得
最慢,要在兩匹磚的細縫里發掘出
一噸享樂主義。我要把五畝葡萄園
拆分成無邊無際,要把
嘗到甜頭的一個下午拆分成今生今世。
豐收
秋天像一個可以伸縮的榫頭:對少年來說,
是夏天的長尾巴,對中年來說,
是冬天的短脖子。夏天我沒有訓練
潛水,冬天也沒有計劃滑雪。
西風如車,嫻熟地搬運著從銀杏葉
尖端滴落的一克理想——從這個身輕
如燕的金色密封艙,我該不該嘗試
向外跳傘?秋天已經派來一株
雙莢決明,在我上班或下班的中途,
一邊開花,一邊掛果,一邊無言
答疑,像一個雙手合十的鵝冠花和尚。
無言,就是五千言。再乘上
幾次過山車,我或能習得上乘的孤獨。
小團圓
第一輪明月不斷撤退,有時撞上了隧道口,
有時游過了桉樹林,有時跳上了
獸脊般的小山丘——被我和一輛綠皮
火車無望追趕。就在這些時候,
第二輪明月高懸于涪江左岸,一動
也不動——被她無理糾纏。
兩處清輝好無賴,擰緊了兩個身體的發條。
我的急性子與綠皮火車的慢性子
強行簽訂了協議:
時速要提高到一百六十公里,
兩輪明月要遇合成一輪明月。
沈府君
漢代的無名工匠雕成了一對墓闕,守護著
沈府君。春風吹過渠縣,
沈府君早已四散為一片兩三畝的野草花。
朱雀已無實用性,白虎亦無
實用性。無名工匠早就以偉大的遲疑
預言了藝術的獨立日——
兩只石獸把春風送出了沈府君的領地。
捷報
我看過高倉健主演的兩部電影:今天,
看了《兆治的酒館》;兒時,
看過《追捕》。高倉健還是那么年輕,
仿佛六年前離世的只是
他的替身。那么,迄今逍遙的反而
是本尊?這樣的錯覺令人著迷。
詩從來就不會輸給電影——
我將比高倉健更老,也將比他更年輕。
無休
四天算不算是闊別呢?今天我徒步上班,
發現銀杏加速變黃,而水杉
開始變紅。是誰調配著紅黃兩種顏料,
就是誰讓小詩冒出了白發。
我駐足于涪江之畔,在永恒中小憩了
兩分鐘,然后就匆匆趕赴一個會議室。
圍城
兩只刺猬,從一開始就沒有吮到棒棒糖,
而試圖用舌頭,
懷柔那遍體竹簽。
而在郊外古戰場,無數刺猬備好了云梯。
恍惚
十六頭亞洲象離開了西雙版納,向正北,
走過了普洱,
折而向東北,走過了墨江、元江和石屏,
繼而向正北,走過了峨山、玉溪
和晉寧。巨腿移動,
玉米倒伏。如果它們繼續向前,
就將橫穿昆明靠近成都,折而向正東,
就將途經我的五畝孤獨,
還將用鼻子大大咧咧地碰碰重慶。
求諸野
鷓鴣的叫聲被一個山頭分了岔,就像被甩到
山腰的魚尾巴。麻雀的叫聲很圓,
似乎要用滑輪放下一座天堂來。
看看吧,這座天堂的建材如此普通——
一條小河正在轉彎,一片草地齊茬茬,
一塊地毯小得剛好夠寬,
幾杯紅茶,幾個皮蛋,一碟葵花籽,
幾句真心話的下午。蟬的叫聲織補了
構樹與楓樹因交叉而形成的各種
不規則夾縫。哪里有什么虧本生意?
我賺到的嫩黃和新綠
足以把天堂鉚接于任何一片水波。
交通
接下來,朋友,你開始吹奏印第安木笛。
我很快聽到了樹狀的南美洲和北美洲,
聽到了十只奧奈羅鳥,
——它們動身飛越太平洋,其中九只
就要停上你的肩膀。此刻,
燈籠花紅得羞澀,斑竹綠得謙遜,
紫葳正在搭建一個音樂的凱旋門。
一只本地畫眉鳥作為臨時替補,
與木笛互相問答。朋友——
請記得用音孔的專列,運走這紫葳,
這斑竹,這燈籠花和畫眉鳥;
請記得用尺八
把它們吹奏給與我暌違的鼓浪嶼。
若爾蓋
你彈了幾首名曲,半即興。又彈了一首
心曲,即興。在半即興與即興之間,
隔著一座昨天下午的鷓鴣山,
而在羊角花叢里面,又藏著一條直通
即興的隧道。當你收起琵琶,
露珠就從皮制琴囊上滑落。露珠,
白河,黑河,收到了同一封密件
——加入黃河的喋喋!這個時候,
所有星星突然低于并略大于
核桃,北斗用銀勺子從黃河舀起了
一大把沒有聽過癮的耳朵。
最尖的一只耳朵乃是月亮的倒影,
這倒影加蓋了波浪的暗花。岸邊,
幾棵沙棘在與寒氣的談判中
不斷收縮,它們羞愧于既不能留下
黃河,又不能割贈草原。
也無妨,我們已經確信——
如果沙棘辦不到,就寄望于音樂。
即物
一個小伙子騎著摩托車,帶著一個女孩。
她的小腿上紋著一個什么圖案:動物,
植物,或抽象符號?六七十公里,
恰是夏天的時速。他們駛離了這個
秘密補給站——
小路兩旁長滿了枇杷,
樹下長滿了斑茅,
地面長滿了鴨跖草;不遠處的一小塊
廢地,長滿了黑心金光菊、陳艾
和鬼針草。一對中年散步者交換了
眼神,兩只手自然相牽,
就像火棘由青轉紅。所有蔥蘢
都見證了他們內心的摩托車,所有
蔥蘢都把他們的系列眼神譯成了
秋天的短序,譯成了野蜂蜜的續集。
悟空
一匹流水,兩匹流水,漫過了剪刀——
那個剪刀手顴骨
高聳,并沒有得到一匹絲綢。
流水和剪刀在一棵法國梧桐下舉行了
一輪和平談判——
流水比剪刀更硬,剪刀比流水更軟。
左岸
我把雙眼租給了一只鷺鷥,在十七樓,
可以看得更清楚——涪江向右拐了
一個彎,就像一小截圓周。
如果難眠,我就不能賒來一尺波浪,
就不能把波浪折成一只鷺鷥,
就不能讓它飛往右岸,歇在某家
醫院窗口,并向某個圓心致以
比護士服更白的表白。如果入眠,
以上種種豈是問題?《瓦爾登湖》
從我的手里滑落,即將勝任
孤枕,“可以測出天性的深淺”。
九月
雨絲那么新,那么細,那么尖,身手
那么曼妙,穿過了針鼻子,
拉出了線狀的涼意。芭蕉一邊
減肥,一邊撰寫夏天回憶錄。
某人一早辦結了出院手續,下午
就急著換上了草綠色
長裙。小病的山頂就是哲學,
哲學的山腳就是秋天。當銀杏逐漸
變黃,剪指甲就會成為一門藝術。
當涪江逐漸變瘦,水落石出,
我們就會挑出一只很小的勺子
而不是一只巨杯
來品飲身體之間的任何一束靜電。
鉆石胃
箭鏃的成分檢測報告,已經從實驗室
送到一張梨木書桌——其含量,
百分之一為稀有元素,或未知元素;
百分之四為小誤會;百分之十五
為有眼無珠;百分之二十三為嫉妒,
秒勝了青檸檬對酸的積極性;
百分之五十七為仇恨,硬度和亮度
略低于欖尖鉆;其與韭菜的相似性,
為零。我餓了,狼吞十萬箭鏃
——為了把它們消化成一小堆廢鐵。
無遮
書房外面就是一個狹窄陽臺,也是理想
花園的一個次品或殘品——
兩盆藍色繡球花,一盆梔子花,
兩盆銅錢草,一盆茉莉花,
茉莉花的一根長枝條挑逗著兩盆多肉。
都沒有開過花。我挨個兒澆水,
摘掉黃葉,剪去枯枝。在平靜
與平靜之間的一個尖刺狀空隙,忽而
念及一個人。很快,我生出了
羞愧。而在花園的一個角落,一盆
天竺葵在預期以外,在幾棵鳳尾蕨
的干擾之下,冒出了羞愧般的紅苞。
驚艷——致Virginia Woolf
伍爾芙!伍爾芙!你的兩只大眼睛組建了
美之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你的白銀憂郁
接通了良知。不管是用鵝毛筆,
還是用蘸水式鋼筆,你定然會寫出
這個句子——
在斑斕花朵的中心,總有一只蝎子,
在問:
“為什么要活著?”
雞尾酒
索道的語速比盲人更快,還沒說完
草甸、冷杉和油松,已然跳到
落葉松。過了三千八百米海拔,
史詩快要進入緊要關頭——
寒冷開除了大部分植物,被反復
敘及的唯有黑黢黢的亂石堆,
無序,
而有序,像一群群團坐的怪獸,
就讀于一個湖的深藍。噓——
索道咬斷了舌頭——大哥已就緒,
達古冰川進入了變聲期。體力
急需想象力來接力,我——我們
——從來沒有見過大哥——
我——我們——頓時信服——
必定有一張齊天的大嘴巴,
能一口飲盡群山環抱的雞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