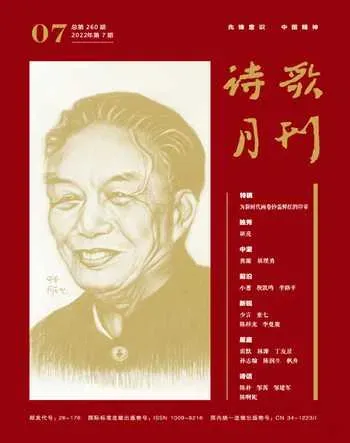童七的詩
童七
無題一則
我們是一朵花的很多花瓣
曾經集中地愛著同一片花蕊
秋天后,愛意萎縮
我們只能蜷縮起自己,把不屬于自己的
都還回去。溫暖回到太陽那里
霜降從月亮上來臨
雪山腳下的露水重新習慣新的溫度
多少婚禮在冬日舉行
多少人就讓過去的自己持續枯萎
那些為了慶祝而聚攏的人兒,跑進山中
尋找早開的山茶
多么好的兆頭。他們不是為了慶祝
而是將在那里,醞釀并期待
很多個春天
一棵孤獨的水杉
以水面為分界,水杉往兩個不同的介質中
呈反方向生長
水面以上,與天空相接的地方有許多云彩
那些云如沉重的道德附著在藍天上
水面以下,泛著波光的紅葉總想把自己
往橫向延伸。印象派的日出里
煙波浩渺,水杉可以壯闊成出生的胎記
而水面自己呢?
一些水為了望見青山,不斷地借風扒開浮萍
一些水為了望見藍天,自己成了無法言說的秘密
一些水為了保存溫度,努力地接納來自世界的惡意
而一些人呢,他們赴遠方趕一場婚禮
只為了一種空無的祝愿
燕子啊燕子,你是一種南來北往的事物
季節也無法讓你停留
寒暑無法在你身上交替
命運的美好的一面卻總在捉迷藏
水杉擁有更好的命運
在陰霾的冬天,它的縱向的紅
和它橫向的朦朧都讓飛鳥羞怯
也讓我們成了冬天的很多面之一
壬寅年初二凌晨,盧家營觀雪
石頭不曾嫌棄日落覆蓋給它的光輝
躺在水中,任寒暑交替帶給它斑紋
牧民趕著牛羊歸家,一些事物重復著童年
我們和一些冒失者一起,把雪花
藏在夜晚的盧家營
在盧家營,真正熱愛雪花的人極少
他們熱愛的是雪花給萬物的潔白
給林木塑造的整飭,以及
覆蓋在荒草上最后的尊嚴
在它的安慰下,美豐富而多義
山頂處,潔白已經混淆了天空和大地
沒有哪一個農民能準確地認出自己的土地
白色侵占人間的夜晚
我與飄雪良久對視
這場對視,讓迎雪而上的我
落成了陸地間
最潔白的那個我
沉默
無話可說的時候我們可以沉默
于是五個人或者六個人 有的沉默里
裝著對人間的不滿 有的沉默里
四月的水蕨菜正在發芽 有的沉默里
有人用鞭子抽打自己 有人則把自己讓給了
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 有人看著一杯茶
眼睛里有一面湖
池中魚
它們沒有料到自己,將死于
一個高原的冬天。這個冬天沒有落雪
冰凌卻布滿眼見之處
池中魚困于池水和泥地中間,已成琥珀
日光照在它們翻起的白肚皮上
一側,留下小小的影子。
綠汁江
江水
不羈從哪里來,無非是樹底,草根
碼成巍峨的山脈那里
不羈到哪里去,無非是江河,湖泊
去找到更多的水,加入他們,成為他們
石頭們裸著肚腹,江水們從容地打滾
平原和曠野到了這里,被迫卷出高度
擋住下午四點十分的日照
鷹隼盤旋在飛機尾翼里
在這里,天空是奢侈的
它形狀狹長,它神色幽怨
只能以長度延伸自己的威信
而江水們,正沒日沒夜地
追著天空跑
時光
江水兀自流。
天空藍得有些無聊,它把藍
投到水中。海鷗于是在藍天游泳
水中不僅有藍天啊,還有樹木和樓房
一群皮肉正在松弛的中年男人
在房屋中游泳。他們把自己脫得赤條條
好像年輕時錯過了什么似的
一個勁往幻影中的房屋里扎,樹木
在流水中浮動
滇樸的落葉從中間穿過
它們那么容易地就“經過別人,成為自己”
鷺鷥氣定神閑
站立在河中央被銹凍住的管道上
沒有踱步,也沒有鳧水
它把頭抬得高高的
撐著四宇內的一方天空
我坐在河邊,開放著鼻子
水草的腥同時鉆進來
眼睛和皮膚上微小的器官
漫無目的地游蕩
像很多人
年輕時候做的那樣
小院日常
不能開窗
讓鳥兒們盡情地在庭院中
啄食
掉落的玉米粒;鳴叫
也不能說話
看,它們還會跑到房梁上
偷吃剛掛起來的咸豬肉
再到水缸里喝水
那是我們的水缸,不過不礙事
讓它們喝吧,喝飽了它們才能
饒有興趣地警覺
在瓦片上跳躍
在樹葉間親昵
仿佛在這個院子里
我們才是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