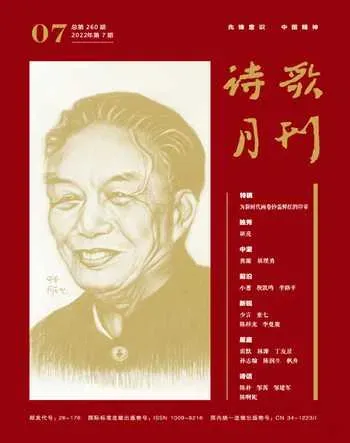陳梓龍的詩
陳梓龍
春天的修辭學
太陽慵懶地趴在樹上
望著從南國飛回的新燕
是如何叫醒,沉睡了一冬的花朵
煙雨不請自來
它們說,要為這些嬌貴的春花沐浴
梅花、桃花,甚至是不善言辭的苦杏子
都曾邂逅一場迷人的春風
這是三月最大的饋贈
滿城喜鵲執迷于一面鏡子
還未找到,河面上就漾起了句點
水的肋骨開始逐漸柔軟
那些被雪隱藏的腳印,全部重新顯現
春天變成精妙的修辭
所有詞語,都隱喻美好的人間
穿行人間的雪
天空一直注視人間
知曉寒風是把刻刀,割裂的樹皮
形似祖父額頭深硬的紋路
這些曲折,就像身體里遍布的腫塊
永遠無法消散
以隱秘的方式傳承,在人間
留下通往冬天的路
還未學會行走,雪里就有行走的足跡
宛若天空用持續的省略
敘述空曠的心事,讓真相成為謎底
讓單薄的雪花流浪人間
并告知:曉色將至,春天的馬蹄奔涌而來
良宵引
沿著長滿薰衣草的河岸,一直走
河島中偶爾驚起幾只水鳥
我們迎山而坐,垂釣空曠的黃昏
燈火闌珊處,水墨色的瓦屋點綴幾棵梅樹
遲暮的愛人住在那里
修補逝去的光陰。花苞落入碗中
剔透如月,你喚我歸家,夜色如此妖嬈
仿佛我已完成一生的證詞
認領手中的命數。夜寒逼人
我們默默無語,任憑唇在黑暗中相觸
柔情似蜜,“大洋彼岸驟起了風暴”
一個人去海邊
平靜的生活在蜀中,除了山
就只有山,這些心中的高墻直入云霄
即使身處浩瀚的夜空
總有一處柔軟,不屬于自己
那就往南方走,一個人去海邊
摘蔚藍色的浪花獻給愛人
捉魚、拾貝殼,用貝殼建一幢房子
就住在這里,遠離未來,更遠離過去
成為一座島嶼,海洋的符號
用這種偽裝的命運,一瓣一瓣剝開自己
蟬語
漆黑的村莊,只有一盞燈在心中
如果沒有蟬語
我只能與黑暗獨白,月光之間
有一條無法窺視的河流
向我傳遞溫度,而深秋的寒刃太急
割傷了一只蟬的半生
像歲月劃過,母親的臉頰
當燈火消逝,月色沉溺
人群散盡的村莊微縮成一個句點
只有蟬聲不曾停止,繼續講述,這失語的人間
歸去來
心中有一個不斷重復的聲音:
“歸去吧,歸去吧”
但歸往何處,舊友,年華,慈祥的眼神
已風干成雜草叢生的瓦房
除了比酒還深沉的暮色,我什么
也不曾擁有,陰雨落在南昌
我行走在洪湖東路
這一刻,夜晚疼痛而神秘
無人知曉,一枚雨滴蘊藏了多少鹽分
喻
桂花香鋪散開來
清晨的太陽,慵懶趴著
在我昨夜留下的,不忍拭去的淚痕之上
長椅上坐著的姑娘,用木梳
捋弄懷里的那只,濕漉漉的麻雀
溫柔的模樣,像極了,撫摸愛人的頭發
這時蟬聲戛然而止,風不再奔跑
落花墜在湖面,漾起層層波紋
而我,也不再想飛。即使這心兒像天空般遼闊
一碗茶
在斑鳩的歌聲里,泡一碗濃茶
躺在搖椅上,品味生活中細微的苦
茶色微黃,小小的碗里似乎藏有秋天
隱隱倒映著后山枯瘦的樹木
當燃燒的葉子零落成泥
一棵樹就完成了安靜的一生
而我體內,還有尚未數清的年輪
在鵝毛大雪中虛構消解的生命
冬日,是一場離別送行另一場離別
有太多事物,我們不忍揭示隱秘的疼痛
其中包括漂泊他鄉,只有寒風
張開雙臂擁抱我,和這碗沒有飲盡的苦茶
草木集
萬物有靈,一株植物也有疼痛的內心
風拂過原野,我看見
烏桕和黃昏交換金色的火焰
燒盡最后一片葉,體內的年輪
敘述著被雨珠驚動的湖面
直至灌木枯萎,留下多褶的面容
時間被喻以更深刻的含義
那些活在人間的草木
被迫在四季的刻度中端舉墓碑
生長,結籽和枯黃,重復本無意義的輪回
從消逝走向永恒,終于趕在雪落前
埋藏裝有天空的弦月
所有承受風雨之物,都像替我而活
大雪終將把自己還給土地
這種洶涌的平靜,是十一月最疼痛的部分
現象學
霓虹陷入沉睡,黑夜的稱謂不曾改變
只是人間因此閉上一扇窗
剩下的火種,能否引燃星辰的眼睛
指引流浪者回到故鄉
它還有隱喻的含義,即便是光明本身
也摻有陰暗,如同天空
不能容忍一枚孤月,懸掛在雨露濕潤的內心
生命具有不能承受之痛
無法用零碎表象,掩蓋命運的卜卦
即使殘缺這個形容,已變成動詞
讓歲月遺漏最為重要的部分
卻無論如何,也沒能抹去
風來過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