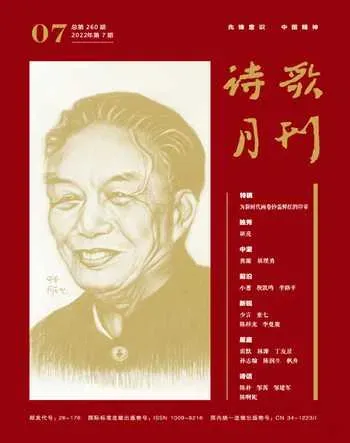李曼旎的詩
李曼旎
離別之夜
請不要讓我們的夜晚
變得神圣,對于這個城市
我們約等于沒有發生
夏日的皺紋曾貼在
我們的臉上,像擁擠的島嶼
一灘小小的貝殼
沒有海邊的房子,沒有
帆船上晶亮的故事。只是
想象著你的眼睛向我投來
我們的相遇如此狀態
如一片眼瞼遇到了另一片
睫毛在曙色的地平線中垂下
我認不出一首舊日的旋律
它是否輕飄飄地拂過了
度假海灘的街道。那里有著
珍珠般明媚而永恒的空氣
僅僅用肉眼就可以看見
……但我記住了一個
健康而模糊的人
他來自哪里誰也無法回答
命運將他安排得如此熟稔
他試圖在今夜粉碎離別的決心
他融化的臉在半透明的窗戶上生長
他親切地貼合我并不鋒利的骨骼
一月的雨
冷濕的夢境于冬日傳來,一月份
的雨僵硬,形如罹患
關節炎的機器人,散發出短暫
而無意義的哀鳴。臆想中的琥珀
以夢的形式,短暫寄居在我的身體
在夜晚,夢境常常如一種
消耗品,令一月的雨持續至夏天
窒悶而無從喘息
為自己的潮濕懷抱殺意。
流動態的記憶被扎穿,逃離
現實的通道切斷,整整一晝
幻想與夢,構成絕妙的雙重虛幻:
當我的眼睛吞食一月的雨,它亦緩慢
侵蝕我,如同在太空中
懸浮舞蹈那般
春天,一個陌生人
我們知道你,春天里
出現的陌生人
上一個冬日你來過,獨自
睜著清脆的單眼皮,面對什么
都沒有答話,如一個幻象
無法解釋它自己
那時我們嘲笑你,“她的目光已經
浸透一整個白晝
白晝卻對她如此陌生,活像
失去影子的人”
而再來時你
松弛進一本鵝黃色封面的書里
不被歡迎的春日
使你淪為虛假,你不擅長騙術
卻在單一的色彩里
綴滿無邊無際的謊言:“不再去”
不去心理咨詢室,不去任何
詩社,不觀看三月的足球場涌動
熟識的白色,我們共同陷入過
那些憑空出現的沼澤
異常的事物在這里都有名字,而她只是
一個不期待被命名的陌生人
寫給她的信全都署著
半流動的稱呼,她等待自己
被一個口吻打動,而愛人只是重復著
逃避的種種別名。“到此為止吧”
春天的太陽細雪般落下,篩入手指
朦朧的縫隙。她無法像遠處的
舊居民一樣熟知自己的病態
春日已抓住她的腳
琥珀湖
我們已經丟失了
那么多東西,就如同一開始
便浪費了得到它們的機會
在無數次路過琥珀湖時
看見無所事事的人兒們,沾滿
濕淋淋的橙黃,在雪地里
痛快地燃燒
那時的琥珀湖還孱弱,類似
寂靜的少女。而她現在依然
身處原先的地方,永遠狡黠地
等待另一對男孩與女孩的路過
“熱戀時我們對視,誘使彼此
剝出對方的眼睛,投入象征著
永恒的湖泊里。如那句諺語:
愛使人目盲”
可我們已白白葬送了
那么多眼睛,若把它們都收集起來
在高空中重重相撞,一定足夠形成一個
橫亙一春的雪季。如今我們只能
站在別人的雪里,回憶一應
苦澀的預言:琥珀湖并沒有長大
她只是再也
再也無法認出我們
心臟
那些與你有著同樣
心跳的人,胸腔里有大量
鮮艷的空缺。在那里
空缺填滿了我的身體
為什么看見你時,笨拙到像是
重新擁有了一顆心臟
鮮亮,寂寞,如雛獸
幼嫩的皮膚
撫摸它的我,是一只
跌入松油里的昆蟲
曾經遺失過什么就從身上
長出些什么。現在你該知道那些
錯異的心跳聲
是從什么地方來的了吧
你是永遠的陌生人,下個世紀
寂寂無名的死者。等到你被所有人
遺忘時,我愿用所有的眼睛
為你哭泣(你的眼睛正密不透風地注視我)
即使我不再記得你的模樣
貓的孩子
貓的孩子你離開了那么久,久到讓我懷疑
連我的存在都是你
私自設在世上的暗語
曾經我們看著
鼠尾草色的天空,純白和艷麗的海
分別在你的雙目間浸泡
你在我的懷里發呆。我是你
注視這個世界的方式
那以后,夜的飽和度
使我們不再人為地醒來
朋友們的瞳孔搖動著,下一個秘密
就算無法親眼看到
也會有人來處置我們的盲
像祈求憐愛的人兒將傷口揭開
那曾經是最幸福的時候,可貓的孩子你
離開了那么久,久到僅剩下
在乎的事情,都好像沒有那么重要了
貓的孩子是不曾存在的我的影子
它對沉默的渴求,讓我等待的東西
永遠只在最后一刻出現
“只因為,我畏懼一切事物的降臨……”
它在顆粒狀的歌聲中不斷重復著
同我一樣不知所措的言辭
我請求許愿池取消了
我曾想要過那些不必要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