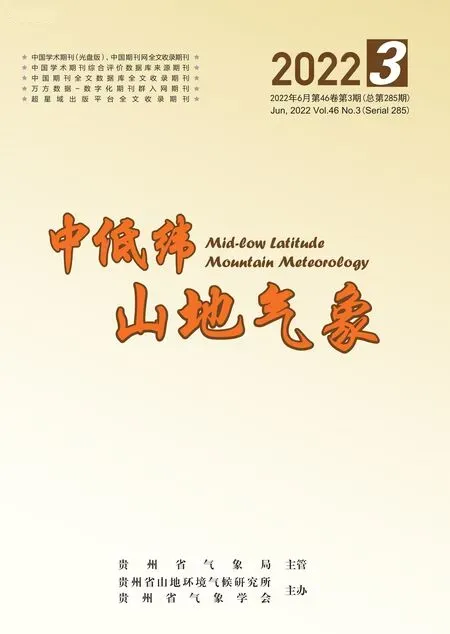貴州省2019年8月極端高溫成因分析
劉紅雙,幸筱炯,楊 熠,武正敏,田 端
(貴州省遵義市氣象局,貴州 遵義 563000)
0 引言
國家氣候中心2020年2月發(fā)布的氣候公報指出,2019年我國極端高溫事件站次比為0.38,較常年明顯偏高0.26,有64站日最高氣溫突破歷史極值,多數(shù)分布在四川、貴州及云南等地,8月大部分城市平均氣溫較常年偏高造成降溫耗能增加[1]。王國復(fù)等[2]認為在全球變暖的大環(huán)境下,我國夏季破紀錄的高溫事件在大范圍的區(qū)域接連發(fā)生,任福民等[3]認為討論極端高溫區(qū)域及季節(jié)變化特征,有助于認識區(qū)域的氣候變化規(guī)律。方啟云等[4]研究表明貴州印江降水量與最高溫度在8月有顯著的負相關(guān),蔡軍等[5]研究表明貴州威寧夏季最高溫度空間分布與地形基本一致。羅四維和錢永甫等[6-7]研究指出青藏高壓東部型和帶狀型過程中,貴州少雨干旱。丁華君等[8]在研究2003年江南異常高溫時指出青藏高壓加強和向東擴張,可作為預(yù)測長江流域以南高溫干旱短期氣候變化的強信號。楊輝等[9]研究表明2003年夏季由于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異常偏強,且持續(xù)西伸控制我國江南地區(qū),使得江南地區(qū)氣溫持續(xù)異常偏高。池再香等[10]在研究貴州干旱特征時指出冷空氣強度偏弱,活動路徑偏北、偏東,南支槽偏弱且較平直,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強度偏強、位置偏西,是造成貴州氣溫偏高的重要原因。彭京備等[11]研究表明南亞高壓偏強與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西伸,使2006年川渝出現(xiàn)形成了少見的高溫天氣。
上述研究主要針對大區(qū)域,針對貴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高溫度和干旱等,貴州極端高溫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因而缺乏對貴州極端高溫的整體分析及認識。貴州地處我國西南地區(qū)東部,自東向西海拔逐漸增高,夏季主要受東亞季風(fēng)和青藏高原環(huán)流系統(tǒng)影響。因此,研究貴州省極端高溫事件與東亞大氣環(huán)流和南壓高壓的關(guān)系,對貴州極端高溫事件分析、預(yù)測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同時極端高溫事件給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勞動生產(chǎn)均造成嚴重影響,也給城市的供電和供水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因而,本文利用NCEP/NCAR再分析資料和貴州省82個地面觀測站逐日最高溫度資料,分析2019年貴州省極端高溫事件發(fā)生的地域特征及成因。
1 資料選取和極端高溫閾值計算
本文所用數(shù)據(jù):①貴州省氣象信息中心1960—2019年貴州省82個地面觀測站逐日最高溫度資料;②NCEP/NCAR 1981—2019年逐月的100 hPa、500 hPa高度場及海平面氣壓場再分析資料,分辨率為2.5°×2.5° ;③國家氣候中心1960—2019年逐月和2019年8月1—31日逐日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指數(shù);④中國臺風(fēng)網(wǎng)2019年7月末—8月西太平洋臺風(fēng)路徑信息。
貴州省極端高溫閾值計算:依據(jù)中國氣象局2015年發(fā)布的《極端高溫的監(jiān)測指標(biāo)》[12](QX/T280-2015),極端高溫主要存在2個閾值,一是極端日高溫閾值,二是極端連續(xù)高溫日數(shù)閾值。本文主要研究極端日高溫的變化,某站極端日高溫閾值由第95位百分位數(shù)確定,即某站1981—2010年逐日高溫的每年極值和次值,構(gòu)建成共由60個按照從小到大進行排序的高溫樣本序列,取排位第58的數(shù)值作為該站極端高溫的閾值。利用上述方法計算出貴州省82個地面觀測站的極端高溫閾值。
貴州省某年(某月)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貴州省82個站點某年(某月)共出現(xiàn)極端高溫的總次數(shù)。
貴州省某年(某月)極端高溫站次比:貴州省某年(某月)共出現(xiàn)極端高溫的站數(shù)/貴州省82個地面觀測站。
2 貴州省2019年極端高溫時空分布特征及原因分析
2.1 貴州省極端高溫閾值及2019年極端高溫空間分布情況
由圖1可知,貴州省極端高溫閾值(圖1a)空間分布由東向西遞減,與貴州地形高度由東向西遞增一致,閾值36 ℃以上主要集中在遵義中北部、銅仁大部、黔東南東部,其中赤水、沿河高于40.0 ℃,赤水極端高溫閾值為41.8 ℃(赤水站海拔高度:354.6 m)、沿河為41 ℃(沿河站海拔高度:334.6 m),最低為威寧站30.0 ℃(威寧站海拔高度:2238.6 m)。貴州省2019年極端高溫(圖1b)主要出現(xiàn)在貴陽、黔東南、黔南等地,其中有4站出現(xiàn)3次,20站出現(xiàn)2次,19站出現(xiàn)1次,全省共計43站出現(xiàn)極端高溫,站次比為0.52,極端高溫主要出現(xiàn)在閾值小值區(qū)32.0~35.9 ℃之間。

圖1 貴州省1981—2010年極端高溫閾值空間分布(a)、2019年極端高溫出現(xiàn)次數(shù)空間分布(b)
2.2 貴州省極端高溫時間分布及2019年8月貴州省極端高溫特征
由圖2a可知,極端高溫在1966年、2011年、2013年、2019年發(fā)生站次數(shù)最多,均在70站次以上,其中以2011年83站次最多,全省82個站平均出現(xiàn)1.01站次極端高溫,次多為1966年的81站次,每年平均有17.3站次極端高溫。20世紀60—7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21世紀00—10年代貴州省極端高溫發(fā)生的站次較多,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后期貴州省極端高溫很少發(fā)生,甚至有些年都沒有極端高溫發(fā)生。極端高溫出現(xiàn)在3—9月(圖2b),5月、7月、8月發(fā)生的站次較多,其中以8月最多達到503站次占全年的48.5%,次多為7月達到280站次占全年的27.0%。3月、4月、6月、9月發(fā)生站次較少,其中以3月最少僅有4站次,占全年的0.4%。因而貴州省極端高溫主要發(fā)生在5月、7月、8月,占全年的87.1%。

圖2 貴州省1960—2019年極端高溫年站次數(shù)(a)、總站次數(shù)逐月變化(b)、1960—2019年8月極端高溫年站次數(shù)(c)、2019年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逐月變化(d)
8月的極端高溫(圖2c)在1966年、2013年、2019年發(fā)生站次數(shù)最多,均在60站次以上,其中以1966年75站次最多,次多為2019年63站次,8月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的變化趨勢與全年趨勢一致。而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最多的2011年僅有一半發(fā)生在8月。2019年全省出現(xiàn)極端高溫(圖2d)共計71站次,比60 a平均高4.1倍,2019年全省極端高溫僅在5月、6月、8月出現(xiàn),其中8月最多63站次,占總數(shù)的88.7%,比8月的60 a平均高7.5倍。
由圖3可知,貴州省極端高溫站次比(圖3a)在1988年、2013年、2019年均在0.52以上,意味著全省82個測站有43個及以上測站出現(xiàn)極端高溫,其中1988年最大達到0.6,即該年60次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分布于49個測站。20世紀60—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21世紀00—10年代是極端高溫站次比的大值區(qū)。1960—2019年的8月極端高溫站次比大值區(qū)主要集中在2005—2019年,其中,1966年、2013年、2019年均在0.45以上,2013年最大為0.52,2019年為第3。

圖3 貴州省1960—2019年貴州省極端高溫站次比(a)、8月極端高溫站次比(b),貴州省2019年8月最高氣溫分布及距平分布(c)、極端高溫出現(xiàn)1次以上站點逐日平均最高氣溫隨時間的演變(d)
綜上,極端高溫主要出現(xiàn)在8月,其中2019年8月的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和站次比分別是60 a同期的第3和第2。從2019年8月的全省最高溫度的分布來看(圖3c),8月最高溫度較常年偏高,特別在省的東部、貴陽—黔南北部、畢節(jié)南部—黔西南的北部偏高1~2 ℃,局地偏高達到3 ℃,最高溫度的大值中心36 ℃在省的東部及東南部,33 ℃主要在省的東部及赤水,其余地區(qū)在33 ℃,個別地區(qū)低于27 ℃。為進一步了解極端高溫的變化情況,將2019年8月出現(xiàn)極端高溫站點的逐日最高溫度進行平均(圖3d),可知最高溫度的變化前期以升溫為主,從8月2日29.0 ℃到8月12日的35.4 ℃,平均每天升溫0.6 ℃,8月21日溫度降至平均值以下。
2.3 2019年與2013年極端高溫8月環(huán)流對比分析
21世紀10年代是極端高溫的頻發(fā)時段,其中2013年8月的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和站次比分別是60 a同期的第1和第3,2019年8月的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和站次比分別是60 a同期的第3和第2。大氣環(huán)流異常是高溫?zé)崂诵纬傻闹苯釉騕13]。下面將從100 hPa和500 hPa高度場及海平面氣壓場對貴州省這2 a 8月極端高溫環(huán)流形勢進行分析。
從2019年8月的100 hPa高度及距平場(圖4a)看出,在32°N附近有2個高壓中心,強高壓中心在青藏高原—伊朗高原,中心值>1685 dagpm,1685線西至50°E以西,東至100°E,東西跨度在40個經(jīng)度以上,1680線控制了我國東部以西地區(qū),其東伸脊點在115°E附近,貴州上空處于1680線控制,整個歐亞大陸及西太平洋較常年都是正距平,且我國中部以西地區(qū)較常年偏高3 dagpm及以上,貴州地區(qū)上空較常年偏高2~3 dagpm。而2013年8月的100 hPa環(huán)流場在青藏高原至伊朗高原也有1個高壓中心(圖4b),中心值在1680 dagpm以上,1680線東伸至100°E附近,貴州上空處于1675線控制,我國30°N以北地區(qū)較常年偏高,西南地區(qū)較常年接近,貴州接近常年同期。2019年8月的青藏高壓強度較常年明顯偏強,相比2013年8月也是明顯偏強,東伸脊點也是明顯的偏東,特別在西南地區(qū)上空青藏高壓明顯控制且強度較常年明顯偏強,而2013年8月較常年偏弱。

圖4 2019年8月(a、c、e)2013年8月(b、d、f)高度場及距平(單位:dagpm)和氣壓場及距平(單位:hPa)(a、b)100 hPa,(c、d)500 hPa,(e、f)海平面氣壓,1960—2019年8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指數(shù)距平歷年變化(g)
從2019年8月500 hPa高度及距平場(圖4c)看出,我國東部以西地區(qū)為正距平,且受高壓脊控制,說明我國東部以西地區(qū)較常年受較強高壓控制,有較強的下沉氣流,利于地面白天輻射增溫。在西北太平洋上有副熱帶高壓的強中心,中心強度>592 dagpm,與100 hPa日本海南部大值中心相對應(yīng),青藏高原存在大陸高壓,中心強度>588 dagpm,較常年偏高2 dagpm左右。從東北地區(qū)到長江流域有低壓槽,且低壓槽較常年偏強,貴州處于586線控制,且位于槽后脊前,同時孟加拉灣至我國西南地區(qū)的高度場偏高1 dagpm左右,不利于孟加拉灣的水汽向我國西南地區(qū)輸送。而2013年8月副熱帶高壓明顯西伸北抬(圖4d),西南地區(qū)受586線控制,與常年強度相當(dāng)。由圖4(h)可知,2013年和2019年8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強度較常年同期明顯偏強,且2019年8月最強,2013年和2019年8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面積同樣較常年同期明顯偏大,但2013年8月最大;2019年8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位置偏西明顯,而2013年8月西伸脊點位置偏西不明顯,且2013—2019年的8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較常年同期都呈現(xiàn)面積明顯偏大,強度明顯偏強,西伸脊點位置偏西的特點。
從2019年8月海平面氣壓及距平場(圖4e)看出,我國華南地區(qū)、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華北地區(qū)東部、東北地區(qū)南部為負距平,四川盆地東部氣壓場較常年偏低或相當(dāng),特別在貴州東部較常年偏低1個 hPa,說明在四川盆地東部冷空氣影響較弱或與常年相當(dāng),且在貴州東部有熱低壓活動。而2013年8月我國除新疆西北外均為負距平(圖4f),且在四川盆地東部氣壓場較常年也是偏低,貴州東部受熱低壓1004 hPa外圍控制,我國整個東部均受低壓控制,且較常年偏強。與2013年相比2019年8月負距平控制區(qū)域偏東偏少,四川盆地東部負距平的值較小,因而2019年8月的熱低壓沒有2013年活躍。
綜上,2019年8月貴州地區(qū)受100 hPa強盛的青藏高壓東伸控制,500 hPa大陸副高外圍受槽后偏北氣流控制,地面上貴州東部受熱低壓活動影響,導(dǎo)致貴州極端高溫,其中全省82個地面觀測站有11個測站最高氣溫突破歷史極值,8個測站與歷史極值相當(dāng)。
校園尺度上,地方滿意度和地方依戀維度均值(3.93)大于量表總均值;地方認同維度均值(3.83)較低,此維度所有測量項的得分均值均小于量表總均值。說明留學(xué)生對云南大學(xué)的自然與物質(zhì)文化環(huán)境和社交環(huán)境有較高的感知,而對學(xué)校功能環(huán)境的評價相對較低。
由2019年8月西太副高逐日變化可知(圖5a),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脊線8月1—9日位于30°N以北地區(qū),較常年同期偏北,最高溫度升高不明顯,8月10 日迅速南落,持續(xù)到8月15日,9—15日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脊線南落16.8個緯度。西太平洋副高逐漸南落的過程,最高溫度逐漸升高,8月12日升至最高35.4 ℃,8月15—20日西太平洋副高逐漸北跳,19日脊線位于31°N附近,8月14日之后最高溫度緩慢降低。可見,西太平洋副高的南落伴隨著貴州省最高溫度的先升高后緩慢降低,北跳后最高溫度繼續(xù)緩慢降低。2019年7月31日—8月30日西太平洋共產(chǎn)生6個臺風(fēng),有4個在我國登陸,其中超強臺風(fēng)“利奇馬”北上,8月7日進入我國臺風(fēng)監(jiān)測24 h警戒線,8月9—10日在浙江登錄。超強臺風(fēng)“利奇馬”登陸與西太副高南落時間基本一致,其西進使副高向內(nèi)陸收縮增強,有利于極端高溫事件的出現(xiàn)。

圖5 2019年8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脊線位置日變化(a)(實線表示實際值、直方圖表示與8月氣候值的距平、虛線表示貴州省2019年8月極端高溫出現(xiàn)1次以上站點最高氣溫隨時間的演變)2019年7月末—8月西太平洋臺風(fēng)路徑(b)
3 總結(jié)與討論
本文依據(jù)《極端高溫的監(jiān)測指標(biāo)》計算出貴州省1981—2010年極端高溫閾值,分析1960—2019年貴州省極端高溫發(fā)生情況,并從100 hPa和500 hPa高度場及海平面氣壓場對貴州省2013、2019年8月極端高溫環(huán)流形勢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jié)論:
①貴州省極端高溫閾值空間分布由東向西遞減,與貴州省地形分布一致,36 ℃以上大值區(qū)集中在省的東部和南部邊緣,其中最高為赤水41.8 ℃,最低為威寧30.0 ℃,2019年極端高溫主要發(fā)生在32.0~35.9 ℃閾值區(qū)間。
②貴州省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的年際變化:在20世紀60—7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21世紀00—10年代貴州省極端高溫發(fā)生的站次較多,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后期貴州省極端高溫很少發(fā)生,有些年甚至沒有極端高溫出現(xiàn)。
④ 21世紀10年代是極端高溫的頻發(fā)時段,其中2013年8月的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和站次比分別是60 a 同期的第1和第3,2019年8月的極端高溫站次數(shù)和站次比分別是60 a 同期的第3和第2。
⑤ 2019年8月貴州受100 hPa青藏高壓異常北抬東伸控制,500 hPa受大陸副高外圍及槽后偏北氣流控制,地面有熱低壓的活動及北上超強臺風(fēng)“利奇馬”影響,導(dǎo)致了貴州極端高溫,全省82個地面觀測站有11個測站最高氣溫突破歷史極值。雖然2013年100 hPa青藏高壓和500 hPa沒有2019年強,但在海平面氣壓場熱低壓的活躍程度比2019年強。
⑥貴州極端高溫的升溫與臺風(fēng)“利奇馬”的西進導(dǎo)致副高向內(nèi)陸收縮增強有關(guān),同時高溫沒有進一步發(fā)展與北上超強臺風(fēng)“利奇馬”對大氣環(huán)流的影響有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