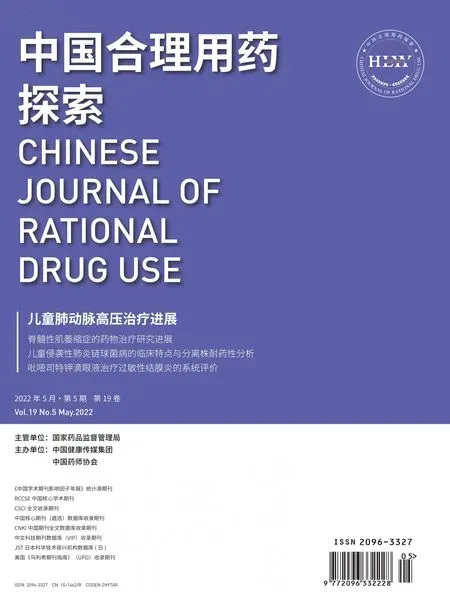阿爾茨海默病的發病機制和藥物研發進展
欒劍,楊心悅
1 吉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四平 136000;2 浙江省錦繡江山外國語學校,江山 324100
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種起病隱匿、進行性發展的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現已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有數據顯示,2018 年全世界約有5000 萬AD 患者[1],至2050 年全球患者數可能達到1.52 億人[2]。2020年,Jia 等[3]報道了我國60 歲及以上老年AD 患者已達983 萬人,是世界上患病人數最多的國家。AD是一種神經退行性疾病,對患者的語言、邏輯、記憶和認知能力都有極大的損害。隨著病情加重,患者會逐漸喪失記憶能力,神志不清甚至完全喪失自理能力。同時,疾病和治療費用帶給AD 患者和家庭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經濟壓力。綜上,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無論從人類健康角度考慮還是從社會資源角度考慮,AD 治療藥物的研發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基于此,本文針對AD 的發病機制和藥物研發進行文獻分析,以期為AD 的臨床治療提供參考。
1 概述
AD 的發病率隨著年齡的加大遞增,表現為認知和行為障礙。AD 主要發病于老年人,病情發展到終末期,患者會喪失自主意識。2015 年,Prince等[4]的研究中,AD 的全球治療及相關費用達到了8180 億美元,且預計在2030 年將逾2 萬億美元。2020 年有研究報道[3],與AD 關聯的高危因素共有9 種,包括居住環境、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吸煙、高血壓、高脂血癥、糖尿病、心臟疾病和腦血管疾病,可以作為早期自查和醫生診斷的參考指標。
2 發病機制
AD 患者的組織病理性學檢查可見明顯的以β淀粉樣蛋白(Aβ)為主要成份的斑塊和以tau 蛋白為主要成份的細胞內神經原纖維纏結,AD 發病機制的主流學說是Aβ和tau 蛋白異常假說。在這2種學說不斷更新的同時,也有新的學說興起。
2.1 Aβ假說
Aβ是AD 診斷的關鍵性指標,其異常沉積可導致患者腦功能失調。當淀粉樣前體蛋白(APP)的代謝發生異常時,會在γ分泌酶的催化作用下剪切生成Aβ。2000 年,Li 等[5]首次鑒定出γ分泌酶。2020 年,Hur 等[6]揭示了神經炎癥調節γ 分泌酶活性及其影響Aβ產生的機制,提示減少Aβ是延緩或減輕AD 病癥的關鍵,因此,γ分泌酶抑制劑的研究一直是AD 藥物研發者最寄予厚望的突破點,只是目前尚無相關藥物面世。根據目前的研究數據和結果,大多數研究結果支持Aβ假說,但是也不斷有新研究成果涌現,沖擊著Aβ假說。2020年12 月,Yang 等[7]研究了γ 分泌酶的3.0 ? 分辨率的冷凍電鏡結構,闡明了γ分泌酶識別3 種不同種類抑制劑的分子機制,包括Semagacestat 的3.0 ? 分辨率結構,以及Avagacestat 的3.1 ? 的結構和γ分泌酶結合過渡狀態類似物(TSA)抑制劑L685,458 的結構,解釋了過去藥物研發失敗的原因,也為未來優化和設計具有底物特異性的抑制劑奠定了基礎。
2.2 tau 蛋白假說
tau 蛋白假說是指患者腦組織中 tau 蛋白過度磷酸化,聚集形成細胞內的神經原纖維纏結,最終導致神經元的變性與死亡[8-9]。過度磷酸化的tau蛋白會造成神經纖維纏結。tau 蛋白是目前國際評估AD 病程進展的金標準[10]。tau 蛋白廣泛存在于神經元中,起到穩定微管蛋白的作用。過度磷酸化的tau 蛋白可能有類似朊病毒的“傳染性”,可在神經元細胞之間傳播[11-12]。tau 蛋白的擴散會使患者病情惡化,使正常的神經元細胞被傳染而變性,造成嚴重的認知障礙。
2.3 膽堿能假說
人的正常學習和記憶與大腦的膽堿能系統有著密切的聯系,而最早發現的AD 的體征之一就是膽堿能神經缺失。AD 患者膽堿酯酶和膽堿乙酰轉移酶活性增強,使乙酰膽堿的合成減少、分解增加,影響正常神經功能,導致嚴重的認知障礙[13]。已獲批的幾種AD 治療藥物中,有4 種(他克林、多奈哌齊、卡巴拉汀和加蘭他敏)是基于膽堿能假說而開發的藥物。其中,多奈哌齊是我國使用最廣泛、銷量最高的AD 治療藥物。
2.4 APOE4 風險基因假說
2020 年,Montagne 等[14]提出AD 的高風險基因APOE4會使大腦的毛細血管周細胞發生退行性病變,加速破壞血腦屏障,損害腦部神經細胞,從而影響患者認知功能。該基因純合型患者AD 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15 倍。由于親環蛋白AMMP9 通路會破壞血腦屏障,加重AD 患者的癥狀,Montagne 等[15]使用了一種親環蛋白A 抑制劑(Debio-025)進行實驗,結果顯示攜帶APOE4基因的小鼠的血腦屏障可以得到一定改善 。
2.5 其他假說
隨著人們對AD 發病機制研究的深入,不斷有新的假說涌現。2021 年,Nakamura 等[16]的研究發現了一系列新的、異常的“蛋白轉亞硝基化反應”都可能導致AD 患者的神經細胞突觸丟失。突觸丟失是AD 患者記憶喪失和認知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該假說的發表,提示AD 的發病機制增加了1 種新的可能。
3 AD 藥物研發進展
3.1 AD 藥品研發進展
1998~2017 年,FDA 僅批準過6 種AD 治療藥物,共有146 個 AD 藥物研發宣告失敗。其中,他克林由于有嚴重不良反應,風險大于獲益而黯然退市。1993 年~2004 年上市的AD 藥物只能緩解癥狀,無法有效地減緩AD 病程的惡化,隨著2019年和2021 年甘露特鈉和阿杜那單抗(aducanumab)相繼問世,全球范圍內獲批上市的AD 治療藥物總數達到8 種(見表1)。Cummings 等[17]的研究提示,截至2021 年1 月,全球總計有152 項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期待未來有更多AD 治療藥物研發上市。

表1 獲批上市的AD 藥物匯總
3.1.1 他克林
AD 患者大腦膽堿能系統功能受損,神經突觸部位的遞質(乙酰膽堿)含量下降,對患者的認知能力造成巨大傷害。靶向提升腦內乙酰膽堿含量的藥物,聚焦于膽堿酯酶抑制劑和毒蕈堿M1 受體激動劑。膽堿酯酶是體內降解乙酰膽堿的酶,膽堿酯酶抑制劑可以阻止乙酰膽堿降解,提升患者認知水平。
1993 年,FDA 批準上市的他克林是第1 種用于治療輕/中度AD 的中樞可逆性膽堿酯酶抑制劑[18]。遺憾的是,他克林會損傷線粒體,抑制DNA 合成蛋白質,誘導細胞凋亡[19],因此導致嚴重的不良反應,臨床表現主要是肝毒性和胃腸道反應。最后,他克林無奈退市。
3.1.2 多奈哌齊
1996 年,FDA 批準上市的多奈哌齊是第2 代乙酰膽堿酯酶抑制劑,主要用于治療輕和中度AD所致的認知障礙,能較好地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腦組織中的多奈哌齊濃度遠高于血漿,呈現出對腦組織的高度選擇性和高親和力。另外,多奈哌齊口服給藥的生物利用度將近100%[20],不受飲食影響,半衰期長且穩定性高[21],是目前治療AD 的常用藥物,也是在我國自1999 年批準上市以來使用最多的藥物。其嚴重不良反應表現為神經紊亂(如躁狂癥、攻擊性行為和暴力行為等)[22],需要臨床加以觀察。
3.1.3 卡巴拉汀
2000 年,FDA 批準應用于輕中度AD 患者的卡巴拉汀也是膽堿酯酶抑制劑,具有雙重抑制作用,即同時抑制乙酰膽堿酯酶和丁酰膽堿酯酶活性[23]。卡巴拉汀能增強患者大腦的神經興奮傳導,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有助于恢復相關的認知能力[24]。其對肝功能無影響,不良反應少且輕微,長期服用存在惡心、嘔吐、腹瀉等[25]。在我國批準上市較晚,主要為進口藥品。
3.1.4 加蘭他敏
2001 年,FDA 批準加蘭他敏上市,其獲批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可同時作用于活化N 型乙酰膽堿受體和抑制乙酰膽堿酯酶活性[26-27],即雙重作用于膽堿能系統。該藥既可以增加乙酰膽堿的效能,又可以抑制乙酰膽堿的水解,使患者體內乙酰膽堿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加蘭他敏口服后易于吸收,不受食物影響,半衰期為5~6h。患者耐受度高,不良反應少,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惡心和嘔吐[28]。我國2003 年予以批準上市,有多家藥企投入生產。
3.1.5 美金剛
美金剛與前面4 種膽堿酯酶抑制劑不同,是一種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體拮抗劑,可非競爭性阻滯NMDA 受體,預防其因過度興奮導致細胞凋亡,進而改善AD 患者的認知狀態。Almeida 等[29]的研究提示美金剛沒有明顯的肝臟不良反應,單獨用藥或聯合膽堿酯酶抑制劑用藥均無明顯不良反應。用藥峰值出現在用藥后6h,半衰期長達65h[30]。
2003 年,FDA 批準鹽酸美金剛用于治療中度和重度AD。美金剛與之前獲批的4 種藥物的靶點不同,且不良反應輕微,可以聯合用藥、多靶點治療。2014 年,FDA 再次批準美金剛和多奈哌齊的復方制劑用于AD 的治療[31]。美金剛作為治療中重癥AD藥物,暢銷世界,我國于2012 年批準該藥進口上市。
3.1.6 甘露特鈉
2019 年12 月29 日,甘露特鈉膠囊在我國獲批上市,是我國科研團隊獨立研發、擁有完整的知識產權鏈授權的AD 新藥[32]。在全球十余年未批準AD 新藥的情況下,甘露特鈉膠囊[33-34]的上市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當然也伴隨著爭議。甘露特鈉膠囊是首個靶向腦腸軸的AD 藥物,其主要成份 GV-971 可以對腸道內的細菌進行重塑,保持腸道內菌群平衡[35-36],從而可以降低Aβ和tau 蛋白過度磷酸化。據Ⅱ期臨床試驗結果報告GV-971能改善輕度或中輕度AD 患者的病程終點[37]。截至2022 年3 月,甘露特鈉膠囊的全球多中心Ⅲ 期臨床試驗仍然在進行當中,此次臨床研究結果將關系到甘露特鈉膠囊能否成功打入國際市場。
3.2 AD 疫苗研發進展
通過免疫療法來治療AD 是備受期待的研究熱點[38],目前進入臨床試驗的疫苗主要有主動疫苗和被動疫苗兩大類,主動疫苗包括AN-1792、ACC-001、V950 等,被動疫苗包括bapineuzumab、solaneuzumab 和poneuzumab 等[39]。遺憾的是,目前大多數疫苗的臨床試驗均以失敗告終,問題主要集中在安全性和體內抗體維持時間等方面。目前尚無有效療法可以根治AD,面對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的現狀,亟待有效疫苗的出現。
3.2.1 抗Aβ 疫苗
Aβ的沉積是AD 發病的關鍵病因,很多疫苗設計的核心就是靶向清除Aβ。最初的基于Aβ級聯假說研發的疫苗AN-1792,通過在動物體內誘導產生Aβ的特異性抗體,取得了很好的療效。遺憾的是,由于Ⅱ期臨床試驗中部分患者因非細菌性腦膜炎而死亡,AN-1792 最終折戟[40]。其后研發的Aβ多肽疫苗雖然采取種種策略預防患者腦膜炎,但仍因抗體維持水平低而失敗[41]。Aβ多肽疫苗在動物實驗模型上顯示出清除Aβ的作用,我們仍可對該領域的前景保有樂觀和信心。
3.2.2 靶向tau 蛋白疫苗
tau 蛋白是AD 的一個重要的病理指標,由于Aβ級聯假說在臨床試驗上屢屢受挫,因而很多團隊轉而研發tau 蛋白相關療法。目前,基于tau 蛋白假說研發的疫苗對于認知恢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沒有很好地解決Aβ沉積的問題[42]。應該說,靶向tau 蛋白疫苗領域雖然在動物模型水平上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推進[43]。
3.2.3 aducanumab
2003~2021 年,歷時18 年FDA 終于批準了AD 治療新藥aducanumab 上市,業內人士的評價褒貶不一,眾說紛紜。一方面是其曲折的Ⅲ期臨床試驗,從備受期待[44],到失敗叫停[45-46],再到復活[47],直至獲批上市,全程都伴隨著爭議[48]。另一方面,此前批準的為數不多的幾種藥物大部分僅能減緩癥狀的惡化,而aducanumab 是一種親和力高,可以選擇性識別Aβ構象表位的免疫球蛋白G1(IgG1)單克隆抗體,可以與患者腦組織中的Aβ沉積結合,激活免疫系統,清除大腦中的沉積蛋白,aducanumab 是FDA 認證的能夠影響AD 發病進程的治療方法。在AD 轉基因小鼠的基礎研究中,aducanumab 通過血腦屏障進入腦內,與腦實質內的Aβ結合,降低腦內Aβ水平,并且呈現量效關系[49]。作為新型疫苗制劑,單克隆抗體aducanumab 價格不菲,每月1 劑靜脈推注,可有效清除腦內Aβ沉積。因此,飽受爭議誕生的aducanumab 只是有條件批準上市,未來還需給FDA 提供上市后研究數據以證療效。但aducanumab 也給業界和目前尚無根治藥物的AD患者帶來了希望。
4 總結與展望
AD 病因復雜,其發病機制至今還沒有統一的論斷,新藥研發也屢屢受阻。目前上市的藥物主要通過調節神經遞質來緩解AD 患者的腦部癥狀,但是往往不良反應大且無法根治。2019 年,NMPA有條件批準我國自主研發的甘露特納膠囊上市,之后本品被納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2021 年,FDA 有條件批準aducanumab 單抗上市,給十余年沒有新藥誕生的AD 藥物市場注入了希望。需要指出的是,面對日趨老齡化的社會現狀,AD 治療領域仍然急切期待療效好、不良反應輕的藥物出現。當前,應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深挖AD 的發病機制,以期找到治療靶點,加快新藥研發進程,根治AD,提高老齡人的預期壽命和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