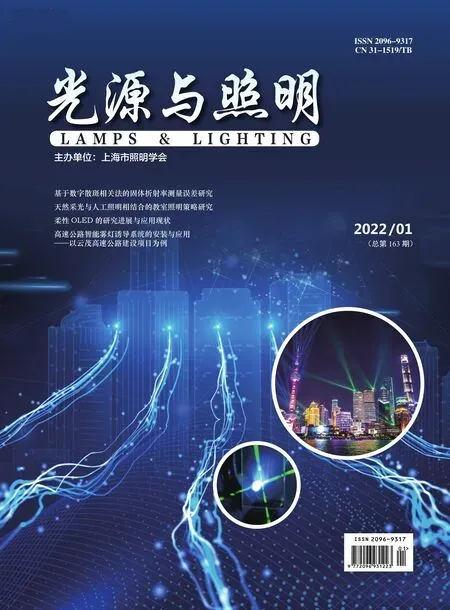基于DMSP/OLS夜間燈光數據的中原城市群建成區時空擴張與驅動因子分析(1992—2012年)
張詞謙,洪 亮※
1.云南師范大學 地理學部,云南 昆明 650500
2.西部資源環境地理信息技術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0 引言
城市化是鄉村聚落轉化為城鎮聚落的過程,是涉及經濟、社會、人口和地域空間等多方面的復雜過程[1]。“中部崛起”戰略構建了位于中國中東部的中原城市群,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2]。遙感作為一種時效性高的大范圍對地觀測技術,在土地利用的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中觀和宏觀尺度上的城市化研究中的應用相對較少[3]。DMSP/OLS夜間燈光數據為獲取城市建成區信息提供了可能,被廣泛地用于城市空間的擴張研究。1978年,Croft等[4]首次提出DMSP/OLS影像具有城市建成區提取的潛力;Henderson等[5]選取舊金山、北京、拉薩3個城市案例,根據高分辨率遙感影像數據提取的城市空間邊界,發現城鎮閾值高低與城市經濟發達程度呈明顯正相關關系;Small等[6]研究了城市的擴張空間格局。但目前國內對城市化空間擴展的研究較少。文章的研究以提取的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建成區范圍為基礎,分析了中原城市群的擴張模式與動力因子,以及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并提出相應的合理建議。
1 研究區與數據源
中原城市群位于中國中東部,以河南省為主體、河南省省會鄭州為中心,包括山西省、山東省、安徽省、河北省的部分城市,涵蓋5省和30座地級市,總面積達28.7×104km2,總人口為1.58億人,生產總值為5.56×1012元,其生產總值僅次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位居全國第四位。
此次研究的數據主要包含遙感數據、統計數據和矢量數據,其數據來源如下。
(1)遙感數據。來源于美國國家地球物理數據中心(NGDC)的美國軍事氣象衛星搭載的傳感器獲取的DMSP-OLS夜間燈光數據,包括1992—2012年的11期數據。數據的預處理包括云及火光等偶然噪聲影響的消除,對全年VNIR通道的灰度值的平均化處理(灰度值范圍為0~63°)、重投影與重采樣等。
(2)統計數據。來源于中原城市群內的5個省份的統計年鑒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主要使用中原城市群中市轄區范圍和城市建成區中與研究相關的經濟統計數據。
(3)矢量數據。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網站的中國縣級以上行政區的矢量數據。
2 研究方法
2.1 建成區范圍提取方法
建成區范圍提取的關鍵是確定燈光閾值。目前,在相關研究領域有4種主流的確定燈光閾值的方法。
(1)經驗閾值法。結合實際經驗人為給定一個閾值,此方法操作簡單,但科學依據不足。
(2)突變檢測法。當燈光閾值達某一值時,城市建成區的多邊形周長會突然增加,這個值就是要提取的研究區域的燈光閾值。此方法忽略了區域間的差異性,不能作為閾值設定的通用標準。
(3)影像空間比較法。用分辨率較高的影像作為輔助,提取城市建成區的夜間燈光數據。此方法受影像質量影響較大,具有不穩定性。
(4)參考比較法。比較燈光值對應的面積數據總和與政府發布的城市建成區面積,誤差最小的數值對應的燈光值即為燈光閾值。此方法從定量角度通過數學計算得到燈光閾值,具有可靠性。
此次研究采用參考比較法提取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建成區。
2.2 擴張模式分析方法
城市空間擴張模式是基于城市空間擴張演變過程的類型總結[7]。當前,城市擴張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重心的變遷上。文章研究涉及重心位置與重心偏移距離兩個指標,可以分別從城市建設中心與發展方向兩個方面分析城市擴張模式。重心的經緯度坐標的計算式如下:

式中:X、Y為區域重心的經、緯度坐標;為第i個像元的灰度值;Xi、Yi為第i個像元的經、緯度坐標;n為區域內像元總量。
重心偏移距離的計算式如下:

2.3 城市格局演變分析方法
在城市格局演變可以中引入景觀指數,其是反映城市的結構組成和空間配置的某些方面特征的定量指標。文章研究主要借助斑塊規模變化方法進行分析,涉及斑塊規模、最大和最小斑塊面積、斑塊面積標準差三個指標,可以分別從斑塊的平均水平、極端情況與變異程度來反映城市格局的演變,具體的計算公式如下:


2.4 擴張動力因子分析方法
城市的空間擴張是城鎮化、工業化、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文章研究以中原城市群建成區面積(Y)為因變量,選取固定資產投資總額(A)、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B)、實際利用外資(C)、工業總產值(D)為自變量,分別代表行政因素、市場因素、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構建城市擴張動力模型。

式中:c為常數項;ai為回歸系數;e為誤差項。
可以將1992—2012年劃分為兩個階段:1992—2002年為第一階段,2002—2012年為第二階段。自變量數據均來源于1993—2013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3 結果與分析
文章運用DMSP/OLS夜間燈光數據,提取中原城市群建成區,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城市群擴張演變過程,分析其動力機制。根據研究結果,1992—2012年,建成區燈光閾值從38逐漸增大到56(見表1)。進入21世紀后,中原城市群快速發展,城市發展進入了高水平階段,建成區范圍分布較集中,擴張主要圍繞中原城市群內承擔經濟中心功能的地級市[8],如鄭州市、邯鄲市、蚌埠市等。建成區主要分布在以鄭州為核心的,在鄭州東北方向的中原城市群核心發展區;南部的高效生態經濟示范區的城市,如駐馬店市、信陽市、南陽市的建成區區域很小。重心偏移距離均值為24 km,偏移距離相對于整個城市群的空間格局非常小,位置變化不明顯;城市空間格局變化不大,但在空間結構上呈緊湊趨勢。

表1 1992—2012年中原城市群城市建成區夜間燈光閾值
因城市建成區面積可綜合表征人類活動的廣度與強度,又與各類城市規模評估指標(生產總值、擴張面積、人口規模、能源消費、城市化水平等)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9],因此,在中原城市群內,中、北部發展勢頭良好,而南部發展較弱,需要引起重視,加快經濟建設步伐。
經分析,行政因素(A)、市場因素(B)、外部因素(C)和內部因素(D)與中原城市群建成區面積之間的擬合優度R2分別為0.92、0.91、0.79、0.91;行政因素、市場因素和內部因素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間顯著相關,對城市群的擴張起了推動作用。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R2分別為0.84、0.99(見表2)。

表2 中原城市群多維驅動力回歸方程
在第一階段中,行政因素對建成區的空間擴張起主要動力作用,這個階段我國城市化進程主要由政府政策引導,因中原地區是重要糧食產區,因此工業并不發達。到了第二階段,市場因素、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對城市擴張的動力逐漸增強,中原地區開始推進工業化進程,而且我國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各個動力因子數據都同步增長,與城市發展的擬合達到最佳狀態。
4 結論
自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城市發展空前,1992—2012年的20年間,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的初期主導力量是國家政策與地方政府,由于政策與地域的差異,中原城市群擴張的“集中”趨勢與國內其他成熟的城市群發展的“擴散”模式不同。中原城市群在建設工業園產業聚集區時,城市群建城區的空間擴張十分集中。
鄭州市作為中原城市群的中心、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其環境污染十分嚴重。應促進鄭州的經濟發展轉向循環經濟模式,吸引更多的高新企業入駐,加快城市群發展重點區域“先富帶動后富”,作為增長極帶動中原城市群內的其他城市的進步。除此之外,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應由以地級市中心城市為發展核心轉向在一個地區內建設多個核心的發展模式,強化城市內部協作發展,因地制宜發展優勢產業,激發市場活力,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城市群內所有地區的競爭力,促進整個區域的快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