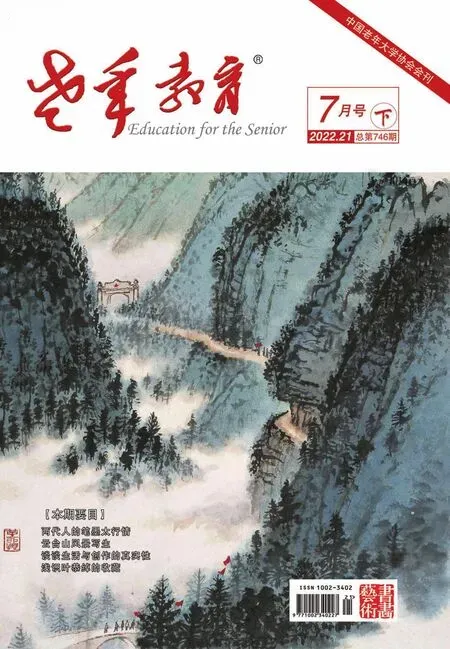淺識葉恭綽的收藏
□劉華贊

《韶山》魏紫熙
葉恭綽(1881—1968),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廣東番禺,擅書畫,喜收藏。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北京中國畫院院長。他曾花費大量財力收藏稀世珍寶,晚年專事著述。2021年11月,北京畫院為紀念葉恭綽誕辰140周年舉辦的“衣被天下誰識恩——葉恭綽的書畫·交游·鑒藏”展,以書畫、交游、鑒藏三項來詮釋葉恭綽先生,應該說是全面而準確的。其中,交游只起到穿針引線的功用,“書畫”和“鑒藏”是主要部分,其中又數“鑒藏”為重。
坊間有“盛世收藏”之說,但這僅為收藏環境的一種。實際上,在收藏史上,朝代的更迭、時局的動蕩也常常會帶來藏品流轉的“繁盛”。晚清、民國便是突出的例子——在這個稱得上亂世的時期,收藏活動卻異常活躍。清宮舊藏的流出、文物市場的繁榮,促生了一大批近現代有影響力的收藏新貴。也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葉恭綽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收藏規模和特色。在那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一方面政壇失語的前清官宦顯貴——從皇家到地方古舊大家,開始成規模地散出舊藏;另一方面西方列強忙于一戰無暇東顧,民族資本得以發展,官員普遍參與各種實業和金融投資,新興官僚資本家發跡、崛起,聚集起可觀的財富。葉恭綽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個人的鑒藏活動或隱或顯,有很多不便記錄之處,所以即便是對藏品有過編目的藏家,也大多不會記錄收藏的全貌。關于葉恭綽的收藏,我們一般可從其成書于晚年的《矩園余墨》《遐庵清秘錄》《遐庵談藝錄》等著作中窺見一斑。在這些著作中,他以書畫序跋等形式對部分自藏或過眼的文物做了記錄,涉及藝術見解、考證、軼聞、掌故等,較為充分地展現了自己的藝術觀、文化觀。即便如此,我們依然無法想象其全部收藏到底是何規模。據記載,僅在1943年,他就曾將所藏山水、書院、寺廟等方面圖籍約447種,以及地理類圖籍2245冊,分兩次捐贈上海合眾圖書館;并曾將所藏碑刻及龍門石刻拓片2000余種寄存于蘇州洞庭山包山寺。還是這一年,他因藏有宣德爐400余件而取齋名為“宣室”,并擬編《宣德鼎彝錄》加以考釋。

隨著對葉恭綽研究的展開,我們發現,與他頗為可觀的收藏相比,其所參與的文化事業之意義和價值恐怕要“重”得多。諸如:編撰《全清詞鈔》、刻印校對《廣篋中詞》、與龍榆生創辦《詞學季刊》、推動影印《四庫全書》《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搶救保護海源閣藏書、編印《五代十國文》、編撰付印《清代學者像傳》,等等。此外,他還參與193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物點收和籌備“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等重要工作,創立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發起建立旨在重振畫學精神的中國文藝學院,參與贊助考古學社及《考古》社刊,發起中國考古會、中國建筑展覽會、上海文獻展覽會,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并出版《廣東文物》,負責抗戰期間文獻保存同志會香港聯絡點工作,推動西南文化研究,等等,能量之大、涉獵之廣、付出心力之巨大、對待傳統文化之赤誠,少有人可比肩。
20多歲的葉恭綽曾有“一歲五遷”之輝煌,不到30歲即為交通次長,繼而為交通總長,掌握重要財權,尤其在經濟領域有著突出才能。1928年,葉恭綽轉而投身文化事業,依舊以積極的工作態度、廣泛的人脈、靈活的處事方式,切實推動著文化事業的發展。可以說,“鑒藏”是他轉向的橋梁,也是他在近代歷史中安身立命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以他曾經站在高位的眼界,他眼中的“鑒藏”并非“玩”,亦無關財富聚集,而是站在民族和國家立場上盡己所能的一份事業。所謂“古物存毀關乎國家興亡”。以這樣的認識從事文化事業,自然不會有失意之感,因為民族大于國家,文化大于一官半職。
總之,對于收藏豐富的葉恭綽,我們不可僅以藏家目之。那些鈐有葉氏“印記”的藏品,因他而聚,因他而散,“呼應”著其起起落落的人生——一切皆是身外物,何況文物!但他留下的那些文化印記卻無法磨滅。當然,如此文化含量的人遠非一次展覽能夠講述完整的,但這些留有葉恭綽痕跡的字畫、題跋、信札、照片……盡管僅是吉光片羽,卻依然能讓我們清晰感受到文化傳遞出的溫暖。
摘編自《美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