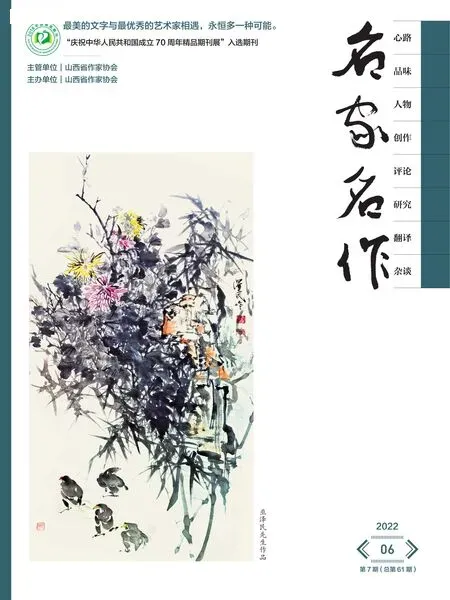新時(shí)代下對(duì)《牡丹亭》浪漫主義精神的分析
彭 倍
《牡丹亭》出自明朝劇作家湯顯祖之手,全書(shū)共有五十五出。《牡丹亭》與《金瓶梅》被譽(yù)為明朝時(shí)期最偉大的文學(xué)作品,無(wú)論是其中所蘊(yùn)含的思想還是藝術(shù)特色都別具一格,吸引了古今中外無(wú)數(shù)的讀者,經(jīng)久不衰。《牡丹亭》講述了女主人公杜麗娘追求愛(ài)情的悲慘遭遇,表達(dá)了作者反對(duì)封建禮教的浪漫主義。
一、《牡丹亭》的創(chuàng)作主題
由于明朝末年內(nèi)外交困的紛擾,加上傳統(tǒng)的道德體系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所以明朝對(duì)重建道德體系尤為關(guān)注。對(duì)明朝而言,重建道德體系就是要對(duì)人欲進(jìn)行適當(dāng)認(rèn)可,從而發(fā)揮出道德體系的制約作用。在封建社會(huì)的倫理中推崇的是一種道德內(nèi)化。在明朝末年,大多數(shù)文人也積極通過(guò)創(chuàng)作來(lái)批判陳舊的道德價(jià)值體系,希望可以據(jù)此讓人們從封建禮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lái)。《牡丹亭》處處都彰顯著作者對(duì)封建意識(shí)的反對(duì)之情,該作品具有強(qiáng)烈的批判和諷刺意義。《牡丹亭》通過(guò)刻畫(huà)人物和故事情節(jié)來(lái)彰顯情和理的個(gè)性解放精神,因此也受到了廣泛關(guān)注。
《牡丹亭》中故事主角杜麗娘從生至死,再死而復(fù)生,其整個(gè)經(jīng)歷都深刻地詮釋了人性如何從壓抑到蘇醒,愛(ài)情如何從禁錮到解放的過(guò)程。在《牡丹亭》中我們能夠看到當(dāng)時(shí)的人們備受封建禮教的摧殘,他們需要與整個(gè)社會(huì)和命運(yùn)作斗爭(zhēng)。杜麗娘一生都在追求個(gè)性解放,不斷對(duì)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要求進(jìn)行挑戰(zhàn)和否定。當(dāng)希望渺茫但又炙熱的愛(ài)情將其煎熬得憔悴不已時(shí),杜麗娘醒悟了,她不再甘心做守在深閨中的大小姐,而是選擇勇敢地向愛(ài)人表達(dá)自己的心意,將自己對(duì)性愛(ài)的追求在夢(mèng)中主動(dòng)表露,而這樣的女子形象在當(dāng)時(shí)封建的明朝中是前所未有的。
二、《牡丹亭》所展現(xiàn)的熱情與沉郁
《牡丹亭》采用了浪漫主義結(jié)合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寫(xiě)作手法,全文突出了反對(duì)封建、反對(duì)個(gè)性追求的寫(xiě)作主題,不斷控訴封建社會(huì)吃人的禮教。《牡丹亭》所表達(dá)的主題思想與同時(shí)期的愛(ài)情作品相比更具有深意,因?yàn)樗粌H展現(xiàn)了情還展現(xiàn)了理,這種“情”與“理”的沖突也代表了明朝中后期的思想家對(duì)朱理學(xué)的反對(duì)。湯顯祖并不是第一個(gè)站出來(lái)提出唯心主義的人。從湯顯祖出生的年代來(lái)看,其應(yīng)該是受明朝思想家王陽(yáng)明的影響較深。也正是因?yàn)橹鲝埻蹶?yáng)明的唯心主義思想,明朝末期才會(huì)涌現(xiàn)出一批又一批反對(duì)封建禮儀的文人墨客。王陽(yáng)明主張心即理、培根說(shuō),其認(rèn)為心外無(wú)理、心外無(wú)物、心即是理,人之根本在心。從《牡丹亭》所表達(dá)的思想來(lái)看也確實(shí)與王陽(yáng)明所提倡的唯心主義相符合。《牡丹亭》所反對(duì)的是古代世俗禮法和陳舊的門(mén)第觀念,故事主角杜麗娘和柳夢(mèng)梅最后也都死于門(mén)第懸殊,這是當(dāng)時(shí)的客觀環(huán)境所造成的結(jié)局。在這場(chǎng)封建禮儀的對(duì)抗過(guò)程中,杜麗娘慕色而亡至死不休,從杜麗娘的遭遇中展現(xiàn)出當(dāng)時(shí)封建禮教對(duì)人性的模式、對(duì)真情的虐殺。
湯顯祖通過(guò)描述杜麗娘對(duì)“情”的追求來(lái)對(duì)抗當(dāng)時(shí)的封建“禮”儀,又通過(guò)刻畫(huà)杜麗娘為了情而死又為了情而復(fù)生的情節(jié)來(lái)佐證人對(duì)自身欲望的追求。在這場(chǎng)情欲與禮儀的沖突過(guò)程中,其運(yùn)用了形象化的表達(dá)手法肯定了人們追求愛(ài)和欲的合理性以及客觀性,并針對(duì)不文明的禮教提出了強(qiáng)烈的抗議和批評(píng),反映了一種新的人性?xún)r(jià)值觀念。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中女性所處的地位是極其被動(dòng)的,被看作是男人的附屬。因此,很少有女性敢于追求個(gè)人愛(ài)情。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肆弘揚(yáng)朱熹學(xué),并指定四書(shū)五經(jīng)為老百姓考取功名必須學(xué)習(xí)的書(shū)籍,在當(dāng)時(shí)人們想要混個(gè)一官半職就必須參加鄉(xiāng)試、會(huì)試,只有通過(guò)這兩項(xiàng)考試后才能參加殿試。這兩項(xiàng)考試的內(nèi)容就是八股文,所謂八股文就是以四書(shū)五經(jīng)里的問(wèn)句做題目,考生只能根據(jù)考官出的題目來(lái)闡述其中的道理,且措施必須符合要求,結(jié)構(gòu)也必須有一定的程序,即便是這樣,字?jǐn)?shù)篇幅還有一定限制,因此要想在鄉(xiāng)試和會(huì)試中出頭,不僅要熟讀四書(shū)五經(jīng),還需要精通對(duì)偶句法的使用。而這樣的考試制度嚴(yán)重束縛了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分子的思想。加上考試內(nèi)容逐漸僵化,變成考生只要可以寫(xiě)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就能金榜題目,對(duì)于考生的實(shí)際學(xué)識(shí)并不重視。而在這樣的科舉制度下,讀書(shū)人的思想也慢慢被狹隘的四書(shū)五經(jīng)以及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在這樣的社會(huì)壓迫下女性遭受著嚴(yán)厲禮教束縛,也是在這樣的社會(huì)背景下出現(xiàn)了大量關(guān)于“女教”的書(shū)籍。
朱厚照登基后太監(jiān)劉瑾權(quán)傾朝野,王陽(yáng)明因?yàn)榈米锪藙㈣毁H到現(xiàn)云貴地區(qū)看管馬匹,也是在此期間王陽(yáng)明悟出了心學(xué)。在此期間社會(huì)也涌動(dòng)出一股追求個(gè)性解放的新風(fēng)氣,這也是對(duì)傳統(tǒng)禮教的一種反抗。一些具有進(jìn)步思想的文人漸漸意識(shí)到封建禮教對(duì)女性的不公平,并為此發(fā)出反抗和不平的呼聲。與此同時(shí)整個(gè)社會(huì)的意識(shí)也開(kāi)始覺(jué)醒,《牡丹亭》和《金瓶梅》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作品,兩部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均通過(guò)情欲去探討人物情欲觀。
作者湯顯祖十分重視女性在父權(quán)社會(huì)中的集體存在感,認(rèn)為女性與男性同樣需要關(guān)懷。從作者湯顯祖的言論來(lái)看,其大有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女性正言的意思。在《牡丹亭》中湯顯祖一直強(qiáng)調(diào)女性對(duì)情色和欲望的追求應(yīng)該是正當(dāng)?shù)模信那閻?ài)也如同日升日落一般天經(jīng)地義,因此不應(yīng)該受到任何人的禁殺和阻撓。與同期的西方戲曲作品不同,在表達(dá)愛(ài)情的方式上,《牡丹亭》更具有東方的委婉和含蓄。例如,杜麗娘雖然十分渴望如意郎君,但其也只能在夢(mèng)中和柳夢(mèng)梅共享魚(yú)水之歡,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卻因?yàn)槿狈τ職猓蠖坏枚粲艄褮g。
三、《牡丹亭》中的浪漫主義表現(xiàn)
所謂浪漫主義文學(xué)就是將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沒(méi)有普遍存在的情境呈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這些生活情境往往都是根據(jù)作者自身的想象和推測(cè)而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這些文字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生活本身的規(guī)律。因此,我們通常認(rèn)為那些帶有非常夸張的描述手法是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特征。
湯顯祖在創(chuàng)作《牡丹亭》時(shí)也充分發(fā)揮出了天才般的想象力,他所刻畫(huà)的人物是奇異的,所有發(fā)生的故事情節(jié)和事件也是奇異的。其創(chuàng)造這些奇異的人物、故事都是為了表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想,將自己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女性所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憤怒之情、不平之情寄托于作品之中。湯顯祖在創(chuàng)作《牡丹亭》時(shí)為了突出作品的風(fēng)格和創(chuàng)作理念,其作出了很多突破。例如,舍棄了我國(guó)傳統(tǒng)浪漫主義戲曲的理想從而表達(dá)出對(duì)真實(shí)生活的依賴(lài),相反在描述女主人公杜麗娘時(shí),讓其自由地受到愛(ài)情的驅(qū)使在生死和天地之間自由往來(lái)。在書(shū)中也有明確描述,如“冥判”“冥誓”這兩章節(jié)都將女主人公杜麗娘對(duì)愛(ài)情的渴望、追求以及敢于和古代人都敬畏的神明所對(duì)抗的那種堅(jiān)貞不渝的情感表露無(wú)遺。這是一種非常大膽的寫(xiě)作手法,作者將自身的理想以無(wú)拘無(wú)束的形式描寫(xiě)出來(lái),以非常積極的幻想形式在《牡丹亭》中表現(xiàn)了自己對(duì)愛(ài)情的熱烈歌頌。為了進(jìn)一步向讀者表達(dá)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想,他還不惜掙脫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束縛,為故事中的人物構(gòu)建了一個(gè)超越現(xiàn)實(shí)的虛構(gòu)場(chǎng)景——夢(mèng)。通過(guò)構(gòu)建女主人公在夢(mèng)境中追求愛(ài)情的情節(jié)來(lái)展現(xiàn)人物性格,為了制造故事情節(jié)矛盾在書(shū)中構(gòu)建了一個(gè)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紐帶。不僅如此,他還突破當(dāng)時(shí)的常規(guī)讓女主人公杜麗娘在夢(mèng)中游園之后與夢(mèng)中情人柳夢(mèng)梅幽會(huì)。隨后又刻畫(huà)了女主人公尋夢(mèng)的情節(jié),更令人感到驚奇的是,杜麗娘死后還可以還魂、婚走。死而復(fù)生在當(dāng)時(shí)的封建社會(huì)是多么精妙,且這些故事情節(jié)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是絕對(duì)不可能發(fā)生的,這是浪漫主義手法。后人將湯顯祖的這種浪漫主義手法與《易經(jīng)》進(jìn)行對(duì)比,推崇他的這種創(chuàng)作手法,認(rèn)為他充分發(fā)揮了人的想象力,通過(guò)虛構(gòu)和幻想來(lái)創(chuàng)作出震撼人心的藝術(shù)作品。
湯顯祖的浪漫主義精神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jié)上,整部作品充斥著詩(shī)情畫(huà)意,不禁讓人贊嘆、回味。湯顯祖在創(chuàng)作詩(shī)詞時(shí)雖然采用了各種艷麗的辭藻,但并不會(huì)讓人覺(jué)得繁縟,相反讀者可以在這些詩(shī)詞中感受到作者淺深、雅俗的感情,值得人無(wú)限回味。例如,在“驚夢(mèng)”這一章節(jié)中就能夠看出湯顯祖的驚人藝術(shù)才能,除了這一章節(jié)之外,《牡丹亭》中的很多唱詞和賓白也都措辭優(yōu)美,作者一改傳統(tǒng)戲曲對(duì)唱詞的嚴(yán)格要求,在創(chuàng)作唱詞時(shí)不僅婉約清麗還頗具潑辣之風(fēng)。從《牡丹亭》的詞曲創(chuàng)作不難看出作者湯顯祖對(duì)自由、對(duì)人性解放的追求,《牡丹亭》也為我國(guó)后現(xiàn)代浪漫主義戲劇創(chuàng)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四、《牡丹亭》中的悲憫與哀怨
一個(gè)人是否成熟,與其年齡并沒(méi)有絕對(duì)的關(guān)系,主要還是取決于其人生閱歷的豐富程度,因此我們經(jīng)常會(huì)發(fā)現(xiàn)一些僅僅十幾歲的人就飽經(jīng)人世滄桑,而且他們往往表現(xiàn)得比那些一輩子順風(fēng)順?biāo)睦先烁映墒臁K^成熟,對(duì)于普通人而言就是不再以自我為中心,能夠充分感知到別人的痛苦,而哲人的成熟在于他們可以對(duì)天下蒼生的痛苦和難處而產(chǎn)生悲憫之心。悲憫與哀怨之情離不開(kāi)悲劇的表現(xiàn),大多作者表現(xiàn)悲劇時(shí)都是以一種理想化的生活形式展開(kāi)的,所以讀者在看待悲劇中人物的災(zāi)難時(shí)有別于現(xiàn)實(shí)生活,對(duì)悲劇的欣賞也只是一種特殊的審美活動(dòng)。不同讀者對(duì)悲劇的感受和理解也有差異。
古今中外,所有聞名于世的偉大文學(xué)作品,無(wú)不有著這樣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與《牡丹亭》同期問(wèn)世的《金瓶梅》也是如此,與《牡丹亭》一樣,兩本書(shū)都無(wú)情地揭露出了時(shí)代對(duì)世人的殘酷,與此同時(shí)兩本書(shū)也滿(mǎn)懷了對(duì)世人的同情,使讀者不禁生出這樣的感受“在一個(gè)不幸的時(shí)代中,每個(gè)人其實(shí)都是不幸的”。中國(guó)文學(xué)的悲劇精神和審美主要表現(xiàn)為悲傷和哀怨,這也源于中國(guó)人骨子里對(duì)自然、社會(huì)、人之間矛盾關(guān)系的肉體磨難,因此其容易懷抱著勸誡人心的道德理想。這種理想也造就了東方悲劇的獨(dú)特性,在悲中可以見(jiàn)喜樂(lè),悲喜兼容之間能夠讓人滋生出善必勝惡的樂(lè)觀主義人生態(tài)度。
湯顯祖對(duì)愛(ài)情的描述是細(xì)致而幽怨的,在他的筆下女主人公杜麗娘曾感嘆道“一生兒愛(ài)好是天然”,只是“恰三春好處無(wú)人見(jiàn)”,男主人公柳夢(mèng)梅道“二十過(guò)頭、智慧聰明,三場(chǎng)得手。只恨未遭時(shí)勢(shì)”。整部作品從二人對(duì)自我身世的哀怨之中展開(kāi),經(jīng)過(guò)游夢(mèng)、驚夢(mèng)、尋夢(mèng)等情節(jié)將中國(guó)式哀怨刻畫(huà)得入木三分。后世很多人都非常喜愛(ài)“驚夢(mèng)”這場(chǎng)戲,這也是全書(shū)中最浪漫、最悲涼的一場(chǎng)戲,因?yàn)閼蛑辛鴫?mèng)梅走后,杜麗娘就凋謝了,在現(xiàn)實(shí)中柳夢(mèng)梅也再?zèng)]出現(xiàn)。湯顯祖曾這樣評(píng)價(jià)臨川四夢(mèng)——人知其樂(lè),不知其悲,這句話將其對(duì)當(dāng)時(shí)女性處境的悲憫之情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五、結(jié)語(yǔ)
真正優(yōu)秀的作品絕不局限在某一個(gè)特定時(shí)代中,《牡丹亭》亦是如此。作者湯顯祖以情欲為出發(fā)點(diǎn),用一首首悲歌喜唱贊頌了女性能夠積極對(duì)抗封建禮教的精神。《牡丹亭》中對(duì)生命、對(duì)自由的向往都是超越時(shí)代的,具有永恒的意義,其之所以能夠被封為經(jīng)典,在于其不僅能夠?qū)懡o所在的時(shí)代,也能夠?qū)懡o未來(lái)。《牡丹亭》不僅展示了人的情與理的矛盾,更是對(duì)人的自然性和社會(huì)性的認(rèn)可,將一部歷史女性生命中的全部需求展示在了我國(guó)戲曲舞臺(tái)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