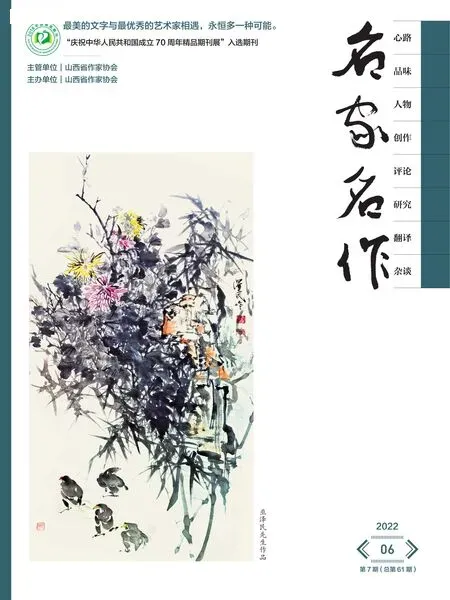試析維拉·凱瑟《啊,拓荒者!》的崇高性
朱思彧
《啊,拓荒者!》不僅表達了作者維拉·凱瑟對內布拉斯加的熱愛之情,并且向讀者展現了她的崇高思想。該小說自出版以來備受學界關注。不少研究聚焦于小說的主題、人物和創作手法,并從生態批評、女性主義、性屬研究、神化與原型批評、多元文化主義、世界主義、地區主義和文學印象主義等角度進行探究。然而學界鮮有研究運用朗基努斯的崇高理論分析這部小說。朗基努斯認為“崇高是偉大靈魂的回聲”,而一部文學作品的崇高性脫胎于“高尚的思想”和“偉大的靈魂。”在他看來,只有當作家具備“莊嚴偉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的感情”時, 他(她)的作品才具備崇高性,并且文學作品崇高性的其他構成要素還包括“辭格的藻飾”“高雅的措辭”以及“尊嚴的結構”。因此,本文將嘗試運用朗基努斯的崇高性美學理論對作者的思想以及《啊,拓荒者!》的人物刻畫、語言和結構進行簡析,從而得出結論:凱瑟的《啊,拓荒者!》具備朗基努斯所定義的崇高性。
一、 維拉·凱瑟
凱瑟的生活經歷,她對內布拉斯加的熱愛以及《啊,拓荒者!》的主題都體現了這位女作家“偉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的感情”。 她曾和家人在內布拉斯加生活了二十四年,并在《啊,拓荒者!》中抒發對內布拉斯加的思念之情和由此產生的創作激情。在這部小說中,凱瑟在贊頌開拓進取精神的同時探討人性:她通過頌揚人定勝天和戰勝自我的精神,宣告她對內布拉斯加的熱愛,表達她對開拓進取精神的肯定。
凱瑟對內布拉斯加草原上移民的艱苦生活懷有濃厚興趣,而這正是她創作小說的主要靈感之源。幼年時她經常拜訪當地不同的居民,這使她自那時起便對家鄉產生了興趣。通過創作《啊,拓荒者!》,凱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像托馬斯·哈代那樣的開拓者,因為“她在自己的家鄉找到了創作主題,直面并描繪它的頑強和悲劇性的福祉”。劉易斯(Edith Lewis)也表達了對凱瑟這方面貢獻的肯定:“除了那里的居民,我想在凱瑟描寫內布拉斯加之前,沒有人會覺得那是個美麗的地方。”在《啊,拓荒者!》中,凱瑟欣賞家鄉的美并珍視這片土地。正如懷特(George L. White Jr.)對凱瑟的評價:“維拉·凱瑟既不描寫絕望,也不描寫戰爭、征服、痛苦,或任何可能打敗人類最高尚品質的幼稚樂趣。”
《啊,拓荒者!》中描繪的人定勝天和戰勝自我的精神不僅表達了作者對內布拉斯加生活和當地居民的愛,并且反映了她作為作家所具備的“偉大的靈魂”。而這種高尚精神和偉大品格在該小說主人公亞歷山德拉·柏格森的刻畫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二、亞歷山德拉·柏格森
亞歷山德拉·柏格森在《啊,拓荒者!》中的品格反映了凱瑟的崇高思想和對生活的熱愛。亞歷山德拉是這部小說中開拓進取精神的化身,她具備幾乎所有高尚的品格——聰慧、善良、有擔當、可靠、堅毅、熱情。從亞歷山德拉的外形、品格和待人接物可以看出,她是凱瑟筆下浩然正氣、奮進精神和高尚人格的代表。
這首先體現在凱瑟對亞歷山德拉外形的描寫之中。亞歷山德拉的出場令讀者感到強大的吸引力:
他的姐姐個頭高而健壯,走起路來快而堅定,好像她非常清楚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她穿著一件男式的阿爾斯特寬大衣(看上去并不令她感到別扭,反而令她感到舒適自在,頗具年輕士兵的架勢),戴一頂圓長絨帽,并用一幅厚面紗扎緊。她的臉看上去嚴肅而充滿思慮。清澈而湛藍的眼睛凝視著遠方,若有所思,像是陷入了困境。
亞歷山德拉在這一幕中看上去堅強、果斷且謹慎,甚至有些許男性氣概,但她湛藍的眼睛和濃密的紅褐色頭發又凸顯出她溫柔且充滿活力的女性氣質。她那光澤靚麗的紅褐色長發象征著活力與希望。作者兩度描寫亞歷山德拉頭發的顏色和光澤:小說第一部分的第一章,當柏格森一家因家父即將離世而面臨困境時,以及第一部分的第四章,當這一家人因土地干旱再遇挫折時。在這兩次困境中,亞歷山德拉都成功挽救家庭于分崩離析,甚至先后為家人和當地居民帶來希望與富裕。在小說的第二部分,當亞歷山德拉成功將荒地改造為良田,使家庭實現增收之后,凱瑟再次對亞歷山德拉的外形進行了一番描述:“亞歷山德拉自己則變化不大。她的身形更加豐滿,氣色更紅潤。她似乎比年輕時更陽光、更富活力。然而她依舊沉著、堅定,目光依然清澈,頭上仍盤著兩條麻花辮兒。”成功和財富并未使她改變。她一如既往地理智、冷靜,只是變得更加強壯。這個時期她的頭發好似一朵向陽花,而膚色也因田間勞作顯得更加健康。正是由于她智慧而勤勞的耕作,她和她的土地都在這一時期呈現出完美的狀態。
亞歷山德拉的精神和品格在她與其他關鍵人物之間的關系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現。這首先體現在她與奧斯卡和盧的關系中。與亞歷山德拉不同,奧斯卡和盧目光短淺、好管閑事、妒忌心強且不知感恩。起初他倆雖然對亞歷山德拉的方法持懷疑態度,但仍聽從亞歷山德拉的安排。當一家人走出困境,這兩兄弟卻開始公開質疑亞歷山德拉的每一個決定:讓伊瓦爾留在家里做事,支持埃米爾上大學,收留返鄉的卡爾住在家里。而亞歷山德拉面對兩位弟弟的質疑,總是與之講理,表現出理解、耐心、果斷和理智。甚至當他倆妄圖使用那并不真正存在的男性霸權,否認亞歷山德拉在家里的權威地位,介入亞歷山德拉與卡爾的關系,并干涉亞歷山德拉的婚姻自主權時,亞歷山德拉仍然堅持耐心地與他們講理。最后,亞歷山德拉不得不警告他們她可以訴諸法律。即使如此,她并不記恨奧斯卡和盧,更沒有與他們決裂。她最終選擇對他倆敬而遠之,并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與合適的事。
亞歷山德拉與伊瓦爾和卡爾的關系則表現了她的善良、聰慧和慷慨。起初,她向伊瓦爾請教問題并依賴于他的判斷和建議。正是在伊瓦爾的幫助下,亞歷山德拉才獲得如此成就。伊瓦爾年邁后,無法務農,亞歷山德拉收留了他,并讓他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盡管其他人都懷疑伊瓦爾精神失常,她卻拒絕將他送入精神病院。相反,她尊重他獨特的生活方式,并因此獲得了對方的尊重。卡爾對亞歷山德拉來說則更像一位伴侶。盡管與亞歷山德拉相比,卡爾性格內向、優柔寡斷、悲觀且未獲得何種成就,但是他溫柔、善良的本性正是亞歷山德拉所需要和依靠的品質。他倆青梅竹馬,自幼便互相依靠和支持。亞歷山德拉對伊瓦爾和卡爾的依賴和支持使她的形象更加豐滿,也更具人性關懷。
亞歷山德拉與埃米爾和瑪麗的關系則表現了她的樂觀、期望、同情和堅強。對亞歷山德拉而言,土地和弟弟埃米爾意味著全部。她將全部的希望與努力都傾注在耕耘土地和培養埃米爾上。盡管她熱愛耕耘,但她仍然希望埃米爾能上大學,能自由地闖蕩世界,過自己理想的生活:
這里生活艱難,負擔重。我們沒法像你一樣來去自由,而且我們的思想已經僵化。倘若這世間僅有我這片玉米地大小,倘若這世上除此再無其他,我不會覺得它值得我為之奮斗。不,我寧愿埃米爾像你這樣,而不是像他們倆那樣。自你歸來那一刻起我便這么認為。
而埃米爾的死對亞歷山德拉造成沉痛的打擊。盡管她的世界被摧毀了一半,但她仍堅強面對現實——埃米爾自己引發了這場悲劇。她不僅承認這一點,而且責怪自己沒有早一些看出埃米爾插足瑪麗的婚姻。盡管已然心碎,亞歷山德拉仍鼓起勇氣前往埃米爾被殺的現場。她為這對戀人悲痛的同時又深感同情:“亞歷山德拉對這一幕肅然起敬,即使是當她為這一幕震驚到悲慟的時候也是如此。”
亞歷山德拉正直高尚的人格還體現在她的責任感、是非觀以及進取精神。作為柏格森家的長女,她肩負起維系家庭完整的責任,并以她的智慧、勤勞、寬容和奉獻讓家人免受饑餓。她學習如何在荒地上與悲觀的家庭成員一起努力耕種;她堅持研究耕作技術并付諸實踐;她忍受奧斯卡和盧的質疑和挑釁;她更為了當地居民的福祉犧牲個人幸福。在那樣一個觀念狹隘保守的地方,她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按自己選擇的方式生活。而當弗蘭克槍殺埃米爾之后,悲痛的亞歷山德拉拜訪弗蘭克,安慰并原諒了他,甚至向他提供幫助。如此高尚的人格在小說結尾處更進一步升華:當埃米爾之死使亞歷山德拉的所有努力和希望遭到殘酷試煉,她再次喚起強大的勇氣和不屈的精神:“我們在這條路上一起走了多少次了,卡爾?我們又將走多久啊!你是否感到一種歸屬感?你是否在這里感到內心的平靜?我想我們將會生活得非常幸福。”而在卡爾的支持和陪伴下,亞歷山德拉又重新獲得了內心的平靜和幸福。
三、辭格、措辭與結構
朗基努斯認為,文學作品的崇高性除了“莊嚴偉大的思想”和“慷慨激昂的感情”,還在于作品“辭格的藻飾”“高雅的措辭”以及“尊嚴的結構”。在他看來,這三者須為思想和感情服務,并且應當自然、簡潔、一致、高雅而莊重。《啊,拓荒者!》的語言、修辭和結構符合朗基努斯的這一標準,從而進一步證實了作品的崇高性。
這部小說的語言和修辭不僅自然、簡潔、一致、優雅,而且為主題服務。這從凱瑟對景色的描寫便可窺見一斑,例如凱瑟對漢諾威小鎮的描寫:
三十年前一月的某日,位于內布拉斯加草原上的小鎮漢諾威在風雪中屹然挺立。灰色的天空下,風吹雪纏繞著灰色草原蜷縮作一團的低矮建筑。它們毫無秩序地分布于這堅硬的草皮上,其中一些看上去像是近期才有人入住,另一些則像是想要離去,向著開闊的草原進發。沒有一棟像是要扎根于此。狂風呼嘯著穿過房底和房頂。
可以看出,作者不僅惜用定語,且慎露情感。這段描寫簡潔利落,卻足以勾勒小鎮艱苦的環境和蕭條的氛圍。接下來的一段描寫更能凸顯作者自然、簡潔卻有力的文風:
路指向西南方,直抵鉛灰色天空中那隱約閃耀的暗淡、濕潤的光線。這光線照在兩張年輕、傷感的臉上,使他們此時靜默無聲:光照進女孩的眼睛,她似乎滿含痛苦的困惑望向未來;光照進男孩憂郁的雙眼,他似乎已然在回望過去。他們身后的小鎮仿佛未曾存在地消失了蹤跡,草原的浪濤也落在他們身后,苦寒的村莊卻將他們擁入懷抱。
在這一幕中,人物與情景相融。作者對人物的情感雖著墨不多,但充分體現了人物的特質,即只有亞歷山德拉心態樂觀。正如前文解析小說的開場一幕,這段描寫的修辭與措辭同樣簡單而高效——象征、對比和隱喻都為主題服務,并與故事情節相契合。不僅如此,作者表達的情感和含義自然、簡約而到位。
此外,該小說的結構完整、一致、統一且切合主題。小說共包括五個部分,分別是“荒野之地”“鄰間良田”“冬日回憶”“白桑葚樹”“亞歷山德拉”。第一部分“荒野之地”包含五個章節,主要描繪了內布拉斯加草原荒涼的自然環境,及其對柏格森一家(特別是亞歷山德拉)造成的困境以及這一家人的生存方法。在亞歷山德拉眼望星空的一幕中,作者充分展現了亞歷山德拉的決心,并不再詳細描寫她具體如何改造土地。包含十二個章節的第二部分則主要描述亞歷山德拉的處世之道。與前一部分講述她如何戰勝自然的內容相比,這一部分對亞歷山德拉應對人際矛盾、背叛和挫折的描寫更能體現她高尚的品格和精神。篇幅較短的第三部分雖只包含兩個章節,卻在整部小說的架構中發揮轉折作用:亞歷山德拉和瑪麗分別完成了各自的轉型并漸行漸遠——卡爾離去后,亞歷山德拉決意平靜地獨自生活,而瑪麗對埃米爾的思念令她渴望與丈夫離婚。 對比和懸念就此產生。第四部分,懸念最終以悲劇收場,而瑪麗與埃米爾的悲劇對亞歷山德拉造成了巨大打擊,也印證了該部分的題目“白桑葚樹”。小說的最后部分通過描寫亞歷山德拉如何走出人生悲劇而將進取精神進一步升華:這不僅是一種強調勤奮、包容和尊嚴的精神,而且強調寬恕與勇氣、美德與高尚。至此,凱瑟構建了一個結構完整、統一且切合主題的故事結構,為頌揚進取精神和高尚人格服務。
四、結語
維拉·凱瑟懷揣著對內布拉斯加的熱愛之情,賦予了小說《啊,拓荒者!》偉大的進取精神。而通過人物塑造、語言修辭和篇章架構,作者偉大的思想與激昂的情感被充分表達,使小說具備朗基努斯所論述的崇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