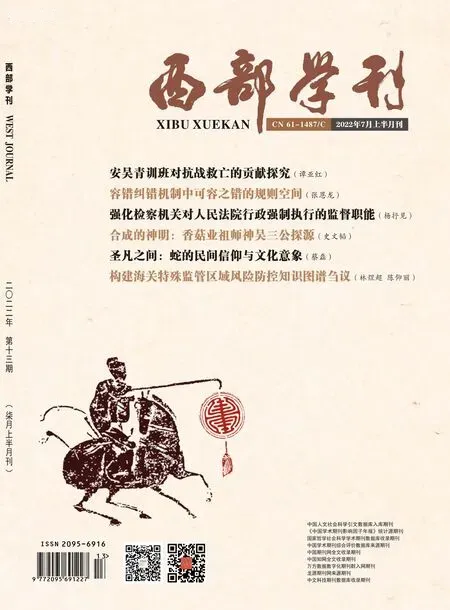安吳青訓班對抗戰救亡的貢獻探究
譚亞紅
安吳青訓班(以下簡稱青訓班)亦稱“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是中共領導下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開辦于國共交界區域內的一所青年干部培訓學校,是中共在國統區開展青年干部教育的偉大實踐。1937年10月,青訓班創設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行后的陜西三原斗口鎮,1938年1月遷至涇陽北安吳堡,歷經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安吳戰時青年訓練班和中國青年干部訓練班三個發展階段,經歷了由短期培訓班逐漸到正規教育的發展態勢,并具備了較完整的教學模式。青訓班的相關教學活動凝聚著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念,以黨的統一戰線理論為指導,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運用戰時教育的培養模式武裝青年,貫徹實施群眾路線,使得畢業學員普遍具有堅定的抗戰信念和實用的抗戰技能,他們深入到各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積極開展群眾運動和抗戰工作,在中國抗戰事業和中共在國統區的人才培養、抗戰宣傳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最終因國民黨反共活動加劇,青訓班不得不于1940年5月被迫遷往延安,改建為澤東青年干部學校而結束其辦學使命。
青訓班在兩年半的辦學時間內,共培養抗戰所需青年學員一萬余人,這些學員畢業后有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等深造學習的,也有奔赴國民黨黨部、敵后和抗戰前線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可以說,青訓班在極其復雜的抗戰大環境下,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培養大批青年骨干,為中共領導國統區的青年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大力辦學,培養抗戰有生力量
青訓班從1937年10月創辦,到1940年5月并入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共在國統區辦班14期,歷時30個月,辦班歷程分為三個歷史時期。
一是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時期。即從1937年10月到1937年12月,這期間青訓班共辦班3期,培養學員1000余人。由于處于初創期,青訓班的辦學地址不固定,曾先后在三原縣以西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農場、涇陽縣云陽鎮的城隍廟和花臺子短暫辦過學,這期間教學人員少,主要有馮文斌、樂少華、何志成和張抱平4人,承擔著學校的所有教學和班務運轉工作,二期后增加了方晨、董忻、史洛文、何志成等教工人員。一期培訓班教學內容主要為統一戰線知識學習、抗日相關軍事常識和群眾工作實踐,二、三期增加了馬列主義相關知識和中國革命史的學習,學習形式主要為課堂教學、討論和主題報告,學習條件艱苦,每日上課只有2—3小時。在初創期,青訓班在國統區的發展還是較為艱難的,其教學統籌工作與實施、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還都處于探索和發展期,有待進一步加強和完善。
二是戰時青年訓練班時期。即1938年1月到1939年1月,青訓班辦班10期,逐漸向正規化的模式發展,具有了日后中共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雛形。在這一階段,青訓班有了固定的辦班地址,即涇陽縣安吳堡,并遵照毛澤東擴大辦學規模、“來者不拒”的指示,廣泛吸收各類愛國青年,因此這個時期的學員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海外。由于學員人數激增,中共派遣部分有經驗的教員和干部到青訓班進行支援,并編寫了專屬的教學大綱和教學材料,學時相應延長,教學內容更加全面,使得青訓班的相關教學和管理機構逐步完善,教學模式逐漸健全,成為青訓班發展的鼎盛期。由于資金有限、人員激增,青訓班此階段的辦學條件還是比較艱苦,多為露天課堂授課。隨著抗戰形勢的嚴峻,青訓班在此時期廣泛吸收流亡在西安地區的婦女、農民、兒童、鐵路職工以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學習,并創設了不同連隊進行戰時教育,辦班模式更加豐富。
三是中國青年干部訓練班時期。即從1939年2月到1940年4月,由于此階段國民黨反共活動不斷加劇,致使青訓班學員來源大大減少,但仍有少部分青年沖破重重阻礙前來學習。因此,這一時期青訓班遵照中共指示,除日常戰時教學工作外,還重點開展青年干部的教育培訓工作,并組織了一系列抗戰救亡的相關實踐活動,如組建西北青年戰地工作團赴前線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開辦青年農場、印刷廠,組建軍事教導隊負責青訓班的安保工作等。由于1940年國民黨軍隊不斷逼近,青訓班不得不撤回延安。
安吳青訓班為中國抗戰和青年運動事業培養了12000余名有生力量。同時,青訓班在國統區的相關辦學實踐,不僅為中共在國統區吸納人才提供支持,也成為向陜甘寧邊區培養輸送人才的基地,大批青年在青訓班經過戰時教育和馬列主義相關知識學習、抗戰相關實踐后,進入延安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和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等進行深造,成為中共干部和抗戰事業的優秀儲備力量。除此之外,青訓班的教育方針、教育模式、組織機構、辦學精神等,也為中共在邊區開辦的高等教育學校提供了借鑒和參考,成為了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組成部分。
二、輸出人才,發展基層抗日救亡運動
據統計,青訓班共為陜西青年抗日救亡運動培養了2000多名干部,僅前3期就有700多人,這些青年干部畢業后,普遍深入陜西各基層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發展壯大中共領導下的青年組織,開展國統區青年運動和抗日救亡實踐活動。青訓班一期學員大多來自于西安民先組織和西安學委輸送的三原三中、西安師范等各中學的學生,他們在經過短期的戰時教育培訓后,大多返回原先的院校從事宣傳等抗戰工作,為青訓班后期的宣傳招生工作提供了幫助,也加強了中共在國統區的領導力量。從第四期開始,青訓班學員來源更加廣泛,但陜西學員仍占有較高比重,部分畢業學員被分配到國統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積極發展陜西青救組織,宣傳中共抗日思想。
1938年年初,由于日軍進犯山西地區,陜西出現了邊防危機,在中共陜西省委“保衛陜西”的號召下,關中各地區派遣一批青年干部赴青訓班進行培訓,并要求青訓班派出青年干部協助陜西各地方工作。在青訓班的上級組織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的支持下,青訓班向陜西各地派出了大批干部從事青年救亡和抗戰工作,使得陜西青救組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據記載,青訓班派出一批已畢業的學員到陜西三原、渭南、戶縣、長安等地從事青年運動,吸納青年群眾,發展青年救國組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7月,青訓班外派學員羅秀云到戶縣教書,通過談話等形式吸引辛墾小學60余人加入戶縣青救會。1938年10月,青訓班外派葉放、武孟明到蒲城指導工作發展青救會員,到1938年底,蒲城的青救會員中,小學教師有56人、學生有179人,還有農民265人。到1938年年底,陜西關中蒲城、渭南、涇陽、臨潼、三原等多地成立了陜青救各青救分會,他們積極為青年群眾爭取權益,開辦識字班、夜校等組織教群眾識字,學習抗戰知識,主動深入農民群眾內部,團結了部分農民、進步青年和師生群體,開展國民教育普及活動,領導青年群眾工作和發展壯大青年組織,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
青訓班在教學中不僅注重統一戰線、民眾運動、三民主義、馬列主義基礎、革命史等理論知識的課堂學習,還極其重視軍事實操課程和實踐教學活動,積極引導學生開展相關實踐,從而更好地為抗戰服務。1938年3月,青訓班在安吳堡周邊地區舉行了為期一周的軍事演習,將全部學員改編為青年自衛團,經涇陽嵯峨山、淳化縣、三原縣向安吳堡西北多地集結,舉行軍事科目演練,沿途深入廣大農村地區開展社會調查,了解國統區的農村實際情況,并編寫制定農村地區工作大綱,開展民眾運動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鍛煉和提高了青訓班學員的實際工作能力。1938年7月,青訓班派出18名學員,與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組織的平津學生流亡演劇隊步行到咸陽、彬州、禮泉等多地開展演出和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并一路向西在國民黨第二戰區軍隊開展救亡宣傳和動員工作。
1939年春,青訓班在淳化縣一處隱蔽民宅內秘密創辦了一所地下印刷廠,負責印刷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和中共陜西省委主編的有關宣傳統一戰線和青年運動的書刊,承擔《青救叢書》系列、青訓班教材和延安出版的相關書籍的翻印,以及《中國青年》《西北》等刊物的出版。青訓班相關書刊在國統區愛國青年群眾的傳播,對于中共突破國統區的輿論封鎖,擴大影響力,建立自己的宣傳輿論陣地,傳播青訓班和中共的真實情況以及抗日主張,爭取中共在國統區群眾特別是青年中的政治認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
三、爭奪青年,推進國統區青年干部隊伍建設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華北地區淪陷,中共堅定的抗日主張和積極的抗戰政策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他們紛紛涌入西安地區,試圖通過西安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出于對人才的重視和愛惜,中共開始廣泛接觸各類愛國青年學生,加緊了在國統區的人才吸收和培養。國民黨胡宗南部為與中共進行人才爭奪,培養抗戰所需人才,也在西安地區成立了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以下簡稱戰干團)。胡宗南認為戰干團在與中共斗爭以及爭奪青年人才當中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國民黨對于當時從西安地區奔赴延安的青年,會在交通要道實行截流,甚至動用憲兵、警察等進入旅館搜查,并通過威脅、許諾政治前途、強行扣留等手段引誘知識青年進入戰干團學習。1938年9月陜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致蔣介石的函電中提到:“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以及從陜北受訓后派往各處的青年,由咸陽等處盤查所截留后解送行,轉送戰干團,日來咸陽盤查所扣獲人數又益見增多。”[3]通過上述等手段,胡宗南創辦的戰干團在西安共訓練三萬九千多人,這些學員畢業后多被充實到陜、甘、寧等各基層組織或淪陷區從事救亡運動和“反共”活動。
據青訓班三期畢業學員楊帆回憶,他與戰友趙湘植在從西安“八辦”前往云陽鎮的路途中,遇到國民黨便衣特務的阻攔,特務惡意抹黑中共和其創辦的青訓班,并用政治前途誘惑他們去國民黨創辦的干培學校學習。在青訓班創辦期間,國民黨利用上述手段拉攏了一部分信仰不堅定的青年,使之最終走到中共的對立面。可見,中共開辦于國統區的青訓班,對于吸收和團結廣大愛國青年,加強中共的干部隊伍建設,以及在抗日戰爭時期沖破國民黨對國統區青年人才的壟斷,發展中共的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四、聯系群眾,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青訓班學員經常利用空余時間,幫助周邊農民進行農業生產、修繕道路和協助維護地方治安,還定期組織慰問軍烈家屬、舉辦文藝演出等活動,與周邊群眾建立了魚水般的親密關系。1938年5月,為開展涇陽縣周邊地區群眾工作,青訓班還下設了地方工作科。經過短暫且正規的培訓和指導后,地方工作科的學員從農民的切身需求出發,利用幫農民群眾干農活、家庭訪問談話、為農民提供救濟、請群眾看文藝晚會等多種形式從事群眾工作和抗日宣傳,與涇陽周邊農民群眾取得密切聯系,積極發展了多個農民支會和民眾夜校。學員李敬儀在青訓班學習時,每周三下午都會被分到附近民眾家里幫助農民秋收,在干農活的同時向農民進行政治宣傳,以達到開展地方工作的目的。1938年7月,青訓班在總結6月工作的會議上,曾列舉其在地方工作方面取得的相關成績,如發展64名青救會員,建立24個農民支會,建立3個民眾夜校,解決部分農民糾紛,注重統戰路線的實行以及動員農民群眾參與青訓班活動,與周邊各地方建立工作關系等。青訓班的上述實踐,證明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下,中共一貫實施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以及動員一切力量為抗戰服務的理念。
1939年,為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青訓班成立生產委員會,在淳化縣亮馬臺組織由350余名學員參與的大開荒運動,開展種糧種菜活動。不僅如此,青訓班還積極動員周邊群眾進行勞動生產,幫助農民春耕和秋收,改良農具和改善耕作方法,解決周邊農民生產上的困難,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青訓班學員通過質樸的語言和具體的行動為農民切身利益著想而深入農民內部的形式,是中共從事農民工作的一大亮點,極有利于農民在當時的特殊又復雜的抗戰環境中支持青訓班的辦學工作,對于中共在農民群眾中積極宣傳抗日主張,貫徹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擴大中共在群眾中的廣泛影響,加強中共與國統區群眾的聯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吸納黨員,強化黨的組織隊伍建設
1938年年初,青訓班開始貫徹中共積極吸收知識分子入黨的決定,但因為青訓班開辦于國統區,且堅定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因此在不破壞國共團結的原則下,青訓班在工作生活中,注意秘密吸收部分信仰堅定的優秀學員加入黨組織。據學員回憶,青訓班新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均在秘密環境下開展,且每次人數極少,黨員課程的學習也在黑夜中的暗室進行,黨員入黨保持著絕對的謹慎性和嚴格的私密性[4]。青訓班對新加入黨組織的知識分子開設黨員訓練班,進行為期半個月左右的教學,具體課程有中共黨史、統一戰線中中共的干部政策、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軍隊和農村中黨的相關工作、支部工作等課程,旨在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養,加強特殊時期中共對人才的吸收、培養和輸出,從而更好地為中共和抗戰事業服務。據相關資料記載,僅在1938年5—7月三個月的時間內,青訓班的黨員人數就增加了500余人[5]。青訓班發展的這些秘密黨員,后來到了國統區、延安以及各抗戰前線和敵后根據地,為擴大中共在國統區的影響力、中共組織的發展壯大起到了推動作用。
六、結語
創辦于國統區的青訓班,對于中共在國統區的人才吸收、青年干部的培養、陜西青年組織的發展、中共學校教育的實踐、中共在國統區話語權的擴大和延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堅定貫徹等,都提供了一定的實施基礎。安吳青訓班在國統區的抗戰救亡相關實踐,形成了中共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人才培養模式,這對于今日我們研究中共戰時教育的發展模式和抗戰救亡之相關實踐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