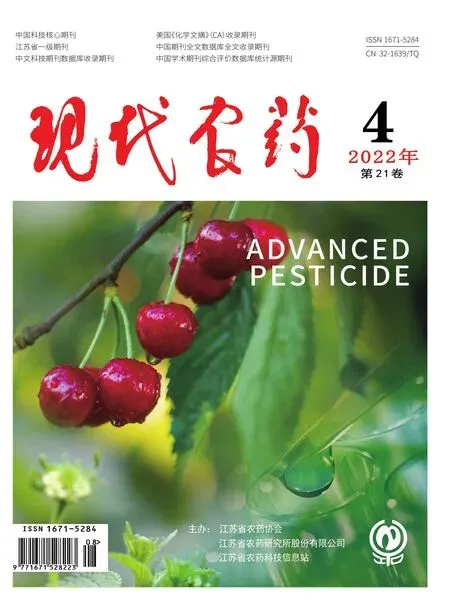我國4種應急防控沙漠蝗的化學農藥對鳥類初級環境風險評估
吳書蓓 ,周艷明 ,毛連綱 *,劉新剛 ,張 蘭 ,張燕寧 ,朱麗珍 ,蔣紅云 *
(1.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北京 100193;2.農業農村部農藥檢定所,北京 100125)
沙漠蝗(Schistocerca gregaria)為直翅目斑腿蝗科昆蟲,被認為是破壞性最強的遷徙性害蟲之一。其主要分布在沙漠灌叢地區,具有極強的長距離遷徙和快速繁殖的能力。在外界環境的刺激下,蝗群密度大,流動性強,造成的遷飛擴散危害可導致嚴重的糧食危機[1]。自2020年初開始,沙漠蝗已成為世界各地的關注熱點。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東非、西南亞、紅海周圍地區爆發了嚴重的沙漠蝗災情,3個地區共計有4 200萬人處于糧食短缺的困境。因此,FAO將此次沙漠蝗災列為2020年首要防控任務之一[1]。為防止沙漠蝗對我國農牧業造成嚴重危害,我國農業農村部、海關總署、國家林草局于2020年3月6日發布《沙漠蝗及國內蝗蟲監測防控預案》,該預案能夠對國內外蝗蟲發生情況進行實時監測,有效保障了生態安全[2-3]。
我國現登記用于有效防治蝗蟲的產品共計36個。其中,化學農藥有23種,主要以擬除蟲菊酯類和有機磷類殺蟲劑為主。由于措施單一和過度依賴化學農藥導致的抗性、殘留和蝗蟲猖獗等問題,這使得微生物農藥和植物源農藥逐漸受到重視,登記數量較往年有所增加,現共計13種[4]。除了登記的農藥產品外,食蝗鳥類的生物防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5]。然而,化學防治目前仍是應急防治蝗災的重要手段[4-7]。2021年3月,全國農技中心發布的《2021年沙漠蝗防控技術方案》中推薦使用高氯·馬、馬拉硫磷、高效氯氰菊酯等農藥來對蝗蟲進行應急防控[8]。在采用化學防治蝗蟲的過程中,若化學藥劑使用不當,則會引發一系列的環境污染和危害非靶標環境生物(如食蝗鳥類)安全等問題[9]。因此,蝗蟲化學應急防控對食蝗鳥類形成的潛在危害應當引起重視。
本研究通過檢索目前登記用于防治蝗蟲類的有效化學農藥產品信息,篩選得到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馬拉硫磷和吡蟲啉的化學農藥單劑;并全面評估了這4類藥劑在多種不同施用場景中對鳥類的初級環境風險,根據評估結果推薦有效成分用量,旨在為我國沙漠蝗等多種蝗蟲的化學應急防控提供合理用藥建議。
1 調查方法
1.1 農藥基本信息查詢
因我國目前暫無農藥登記在沙漠蝗上,根據《2021年沙漠蝗防控技術方案》[8]以及檢索中國農藥信息網,獲得登記防治對象為蝗蟲類且在登記有效日期內的化學農藥。查詢農藥標簽,統計同種藥劑的最大推薦有效成分用量、施用方式、施用次數以及作用場景(表1)。將目前登記有效的防治蝗蟲類化學農藥進行統計分類,在種類上發現單劑占絕對優勢,占比為82.6%,混劑占比為17.4%;在化學農藥類別上發現有機磷類殺蟲劑,如馬拉硫磷占比最高,為52.6%,其次是擬除蟲菊酯類殺蟲劑,如溴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以及少量新煙堿類殺蟲劑,如吡蟲啉。這與前人的查詢結果基本相符[6]。因此,本研究主要對目前登記占比較大的化學農藥單劑如馬拉硫磷、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以及吡蟲啉進行鳥類初級風險評估。登記信息及最大推薦用量如表1所示。

表1 4 種化學農藥登記信息
1.2 評估數據獲取
1.2.1 初級暴露分析
待測農藥品種的施用方式均為噴霧,初級暴露分析參考NY/T 2882.3—2006《農藥登記環境風險評估指南第3部分:鳥類》[10]。農藥噴霧暴露場景、不同作用場景和與其相應的指示物種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農藥噴霧暴露場景指示物種及其相關信息
1.2.2 初級毒性效應分析
通過檢索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官方報告數據[11-14]得到這些化學農藥對鳥類的急性半致死劑量(LD50acute)、短期飼喂半致死劑量(LD50short-term)和長期無可見有害作用水平(NOAEL)。查詢時間截至2021年8月8日。
1.3 數據處理
1.3.1 初級暴露分析
參照NY/T 2882.3—2016《農藥登記環境風險評估指南 第3部分:鳥類》[10],按式(1)~(3)分別計算噴施場景下鳥類急性、短期和長期的預測暴露劑量(PEDacute、PEDshort-term和PEDlong-term),mg a.i./(kg bw·d)。

式中:FIRbw·d為指示物種每克體重每日食物攝取量,g/(g bw·d);RUD90為第90百分位的單位面積施藥劑量的食物農藥殘留量,(mg a.i./kg食物)/(kg a.i./hm2);AR為推薦的單位面積農藥最高施用劑量,g a.i./hm2;MAF90為 RUD90對 應 的 多 次 施 藥 因子 ;RUDmean為單位劑量殘留量的算術平均數,(mg a.i./kg食物)/(kg a.i./hm2);MAFmean為RUDmean對應的多次施藥因子;ftwa為時間加權平均因子,默認值為0.53。
1.3.2 初級毒性效應分析
參照NY/T 2882.3—2016《農藥登記環境風險評估指南第3部分:鳥類》[10],根據查詢得到鳥類毒性試驗終點數據,按式(4)計算預測無效應劑量(PNED)。

式中:EnP為毒性終點;UF為不確定性因子。
1.3.3 風險表征
根據暴露分析計算得到PED和效應分析計算得到PNED,按式(5)計算風險商(RQ)。

式中:若RQ≤1,表示風險可接受;若RQ>1,表示風險不可接受。
2 結果與分析
2.1 鳥類環境風險初級暴露分析
為提供更為全面詳細的數據支持,本文評估了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馬拉硫磷和吡蟲啉4種藥劑在已登記及暫未登記使用的暴露場景。這4種用于防治蝗蟲的化學農藥對鳥類的急性預測暴露劑量結果如表3所示。同種藥劑在涉及多個藥劑推薦用量情況下,評估所用劑量均選用最高劑量。4種化學藥劑急性預測暴露劑量(PEDacut)e范圍為0.359~28.54 mg a.i./(kg bw·d),其中溴氰菊酯和吡蟲啉的PEDacute值范圍相近,而馬拉硫磷在所有暴露場景的PEDacute值均遠高于其他藥劑,這與其較高的施用劑量有關。4種化學藥劑對鳥類的短期及長期預測暴露劑量結果與急性結果相似,PEDshort-term值范圍為0.164~11.099 mg a.i./(kg bw·d),PEDlong-term值范圍為0.086 8~5.882 mg a.i./(kg bw·d);馬拉硫磷因其施用劑量最高,PEDshort-term值和PEDlong-term范圍值分別為6.634~11.099和3.516~5.882 mg a.i./(kg bw·d)。

表3 4 種化學農藥對鳥類的預測暴露劑量
2.2 鳥類環境風險初級效應分析
通過數據庫檢索查詢到4種農藥對應的急性、短期以及長期毒性試驗數據,毒性效應終點(EnP)的選取參考NY/T 2882.3—2016《農藥登記環境風險評估指南 第3部分:鳥類》[10],當存在不同物種毒性數據時取幾何平均值進行效應分析,長期繁殖毒性則取最敏感物種的繁殖毒性終點值。溴氰菊酯等4種化學農藥對鳥類不同效應類型的預測無效劑量(PNED)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4 種化學農藥對鳥類的毒性效應數據
2.3 風險表征
4種化學農藥對鳥類風險評估結果(表5)顯示,4種化學農藥中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以及吡蟲啉按照登記用量在4種暴露場所使用,對鳥類的急性、短期和長期風險均可接受;馬拉硫磷對鳥類的急性和短期風險均可接受,而在長期繁殖毒性風險評估中以最高劑量施用,在4種作用場景的風險均不可接受。

表5 4 種化學農藥對鳥類的初級環境風險評估結果

(續表5)
3 討 論
本文重點關注化學防控應用可能出現的潛在環境問題,系統評估了施用4種化學農藥后對鳥類的急性、短期和長期的風險,并根據風險評估結果推薦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和吡蟲啉作為推薦用藥。馬拉硫磷在相應場景施用后會對鳥類長期繁殖存在較高風險,以臨界綜合風險系數(RQ=1)反推馬拉硫磷有效成分施用量,在農田或牧草上施用最高有效成分用量(AR)建議不超過466.5 g a.i./hm2;在草地中施用AR不超過314.5 g a.i./hm2;在荒地或灘涂上施用AR不超過454.9 g a.i./hm2;在林木中施用AR不超過278.8 g a.i./hm2。根據本次評估結果并結合前人研究報道[15],建議其單劑有效成分用量不高于278.8 g a.i./hm2。現已登記有多個高效氯氰菊酯·馬拉硫磷復配制劑,可開發低劑量馬拉硫磷與擬除蟲菊酯類或新煙堿類殺蟲劑復配使用,或者開發擬除蟲菊酯類和新煙堿類殺蟲劑的新劑型,從而滿足高效低風險的要求[4]。
本研究采用的評估方法還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本文環境評估僅采用了查詢的原藥毒性數據,未采用制劑毒性數據,評估結果同樣存在不確定性,今后可針對不同場景,選擇相應指示物種進行毒性測試,以期為食蝗鳥類的環境風險評估提供更精準的毒性數據;另一方面,因查詢數據較為單一,未根據施用場景選擇相應指示物種,以及未選用需要保護的食蝗鳥類進行風險評估,如牧雞、牧鴨以及粉紅椋鳥等,所以評估結果可能存在不確定性。此外,農藥噴霧不僅可通過經食對鳥類造成危害,還會通過飲水及吸入途徑進入鳥體內,因而對于鳥類不同暴露途徑的風險也需要引起重視[16]。
初級風險評估結果僅代表鳥類在實驗室中最極端條件下的風險,在此條件下評估結果不可接受并不意味著化學藥劑在實際施用過程中一定會對鳥類生長和繁殖造成影響,下一步還可以基于半田間和田間監測,獲得引起鳥類死亡和繁殖危害的田間試驗或監測數據,從而開展更高階的環境風險評估。在蝗蟲化學防治的同時,也需要注重與其他防治技術的協同,降低高毒化學農藥使用比例,研制開發新型高效低風險化學藥劑,在不超過蝗蟲防治生態經濟閾值的前提下,不斷完善蝗蟲防控技術體系,從而實現蝗災可持續防控的目標[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