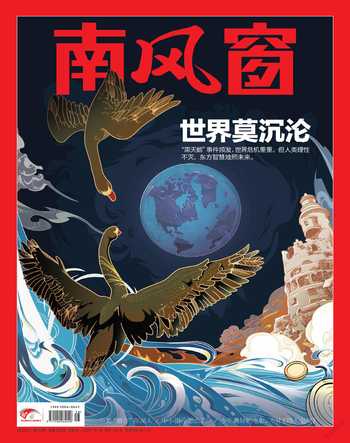全球經濟,正走向滯脹
湯興

滯脹,顧名思義,即“停滯”與“通脹”的結合。它描述的是一種低經濟增長和高通貨膨脹并行的罕見狀態。它曾在1970年代中后期,極大地打擊了發達國家經濟,并成為全球經濟結構、經濟政策調整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分水嶺。
最近一段時間,各界對1970年代的滯脹噩夢卷土重來的擔憂不斷升溫。這與去年此時,經濟學家們對2022年的經濟抱有較好預期的景象截然不同。
俄烏之戰,令自去年初就快速爬升的全球通脹走勢曲線更加陡峭,國際機構紛紛下調經濟增長預期。6月初,世界銀行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將2022年全球增長預期下調至2.9%,并警告全球范圍內可能出現1970年代的嚴重滯脹,許多國家將面臨經濟衰退。
廣州商學院校長、吉林大學橫琴金融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國家級人才獲得者李曉教授,在接受南風窗采訪時表示,半個世紀后,新一輪全球經濟滯脹正在拉開序幕。
不對稱性滯脹
李曉教授向南風窗預測:與1970年代的滯脹不同的是,本輪滯脹將具有更加明顯的“不對稱性”,帶有明顯的結構性滯脹特征。
此輪滯脹的深度和長度,在主要經濟體間很可能存在著明顯差異:美國為“淺滯脹”,歐洲陷入“深滯脹”,而日本則很可能進入“有滯無脹”或“有滯微脹”的狀態。
同時,在美國“淺滯脹”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大概率不會出現長時間深度滑坡。換句話說,本輪滯脹無論從程度還是持續時間上,都不會如1970年代那樣嚴峻。
關于這點,南風窗在采訪第三方學者、經濟學博士肖祖珽以及廣東財經大學學者陳美蘭時,均得到了相同答案。
李曉教授向南風窗分析道,本輪滯脹的“不對稱性”主要是由三個因素決定。
首先,是俄烏沖突對能源和糧食等大宗商品的負面供給沖擊,對不同發達經濟體的影響不同。與19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的供給側沖擊的普遍性相比,此次大宗商品供應端沖擊帶來的影響具有結構性差異。
具體而言,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向下游產業的傳導效應,在主要發達經濟體間的表現各異,即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至多是邊際性的,但對歐洲、日本經濟的影響卻會很大。
美國是能源大國,對天然氣進口和外國石油的依賴程度不高,同時美國也是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國。無論是能源自給率,還是糧食自給能力,美國的優勢都是其他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
而能源供給困境,會嚴重拖累歐洲尤其是德國的經濟復蘇。2020年歐洲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對俄羅斯的依賴度分別為31%、34%和21%。考慮到俄烏沖突很可能延續至冬季甚至明年,以及歐洲主要國家調整能源結構的決心,后續歐洲面臨能源危機的可能性較大。
歐盟統計局7月1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歐盟27國年化通脹率已達9.6%,較5月份的8.8%上漲了0.8個百分點,達到了有觀測值以來的最高水平。從通脹的分項來看,歐洲6月的能源價格同比上漲高達42%,遠高于其他項。同樣,日本燃料也高度依賴進口,日歐在能源領域解除與俄羅斯的關系非常艱難。
其次,是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產業結構差異。70年代后,美國經濟逐漸轉變為以第三產業為主,經濟結構日趨高度金融化,服務行業占據更多比重,制造業以高科技主導型為主,經濟產業結構對比70年代滯脹時期,存在著巨大差異。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向下游產業的傳導效應,在主要發達經濟體間的表現各異,即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至多是邊際性的,但對歐洲、日本經濟的影響卻會很大。
至于日本,在美聯儲加快緊縮步伐下,日本央行繼續維持貨幣寬松政策,使得日美利率差在短期內拉大,日元快速貶值。理論上,本幣貶值可以增加出口和入境消費收入,但由于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生產的比例大幅提升,降低了匯率貶值對其出口刺激的影響。也就是說,日元貶值對日本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非常有限。
受到疫情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日本經濟增長將持續陷入低迷。而在日元貶值的影響下,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價格上漲,會造成企業采購成本上升,最終傳導至商品價格。與此同時,由于多種復雜的結構性作用,日本通貨膨脹的內在動力長期不足,近期通脹率勉強達到2%。日本本輪通脹率提升,更多是基于外部供應不足的傳導效應,與其自身經濟基本面變化關系不大,故通脹率提升空間有限。因此,日本經濟很可能進入“有滯無脹”或“有滯微脹”的狀態。
最后,是美元體系的優勢。與半個世紀前相比,現階段美元體系的運行機制更加成熟和完善。這使得美國能夠更輕易和快捷地向外部轉移危機成本和風險。
從二戰后到1970年代,全球危機都是生產過剩危機,但從1980年代開始,基本被貨幣金融危機取代。在全球金融危機出現時,即便是美國自身引發的危機,美國的危機程度通常也不是最嚴重的,而且往往可以最先擺脫危機。它在獨自獲取巨大金融收益的同時,風險和成本卻讓全球市場來承擔,這是美國獨有的“霸權”。
具體來看美國經濟,李曉教授稱,當前美國經濟已經顯現出“準滯脹”特征。
從“脹”的角度來看,自2021年下半年以來,美國通脹“高燒不退”。今年6月,美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漲幅達到近41年來的峰值9.1%。當前,美國的核心通脹指標上漲正在變得更加廣泛。
從“滯”來看,美國多項經濟指標在傳遞衰退信號。
2022年美國第一季度GDP收縮1.6%,第二季度預計也將收縮。這意味著,美國經濟將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已經符合統計學上“技術性衰退”的定義。
而且,今年7月,美國兩年期國債收益率開始飆升,同時十年期國債收益率走平,兩者之間出現了自2000年以來最嚴重的倒掛。
李曉教授告訴南風窗,自195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美債收益率曲線的倒掛都曾在6~18個月內引發過美國經濟衰退。唯一的例外發生在1960年代中期,當時約翰遜總統實施“偉大社會”的構想,通過凱恩斯主義財政擴張理論的實踐,避免了經濟衰退。但是顯然,現在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那么,美國會進入什么程度的滯脹,持續多長時間?
對此,李曉教授的判斷是,美國很有可能會進入一次“淺滯脹”。鑒于俄烏沖突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幾乎是邊際性的,以及美聯儲治理通脹的經驗,美國的經濟衰退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通脹大概率會在明年上半年,最晚也會在下半年得到遏制。美國通脹率的走勢以及美聯儲縮表加息政策的力度與長度,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美國陷入滯脹的狀態。
當然,李曉教授補充道,我們需要考慮到疫情等不確定性因素。目前,只要疫情不發生致死率嚴重回升的沖擊,可以預期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不會很大。
如履薄冰的美聯儲
李曉教授表示,自上一輪全球滯脹半個世紀以來,美聯儲積累了豐富的治理通脹的經驗。其打壓通脹的決心對市場預期影響很大,但其在預判通脹的能力上仍然存在明顯不足。
與上個世紀相似,本次美聯儲在面對通脹上行的諸多跡象時,沒有及時采取行動。
2021年下半年,在通脹已經高企的情況下,美聯儲依然認為失業是美國經濟面臨的最嚴重問題,而通脹率上升不過是疫情沖擊下供應鏈中斷所觸發的短期現象。這種“通脹暫時論”的誤判一直持續到今年年初。
美聯儲在今年3月、5月和6月,分別加息25個基點、50個基點和75個基點,7月末預計會再次加息。其中,75個基點是美聯儲自1994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加息。
美國勞工部公布的6月非農數據,為美聯儲高頻加息提供了支持。數據顯示,就業市場繼續超預期向好,6月季調后非農就業人口增長37.2萬人,高于預期的26.5萬人。失業率持平為3.6%,繼續保持為202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就業形勢是居民收入、美國內需的根基。就業市場持續表現強勁,預計將促使美聯儲更加專注于控制通脹,并更為堅定地采用“前置、快節奏”加息策略。
2021年下半年,在通脹已經高企的情況下,美聯儲依然認為失業是美國經濟面臨的最嚴重問題,而通脹率上升不過是疫情沖擊下供應鏈中斷所觸發的短期現象。這種“通脹暫時論”的誤判一直持續到今年年初。
李曉教授認為,在誤判時機已經覆水難收的情況下,美聯儲需要在接下來的控制通脹上付出更大努力。但無論如何,美聯儲這一輪的縮表加息,將面臨兩個困境:
一方面,如何在加息與穩增長間取得平衡。加息會令美國的經濟不可避免地受挫;但若加息過少,通貨膨脹將無法遏止。
現階段,在美國經濟高度金融化的情況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增長已經發生嚴重脫離,金融市場一直在高位運行,泡沫很多,一旦快速刺破發生金融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同時,在實體經濟進入下行周期的過程中,一旦加息過猛,很容易使得經濟出現硬著陸。
另一方面,如何在加息與政府舉債成本之間取得平衡。近年來,美國居民、企業特別是政府債務的膨脹和擴張,都是在低利率環境下實現的。僅在疫情期間,美國政府的債務就增加了25%。一旦加息過猛,債務負擔的加劇很可能引發債務危機,從消費和供給兩個方面壓低經濟增長,加速經濟衰退。
據此,李曉教授判斷,在既要關注通貨膨脹高企,又要考慮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運行的情況下,美聯儲寧可多次加息,也難以一次性大幅加息去刺破金融市場泡沫或導致實體經濟硬著陸。
在李曉教授看來,最順利的情況是實現經濟“軟著陸”,即在不刺破泡沫和不讓實體經濟硬著陸的情況下,降低通貨膨脹率。這樣,美國只會經歷一段時間的“淺滯脹”,這給經濟帶來的痛苦程度是可接受的。美聯儲主席鮑威爾6月22日稱,近幾個月國際形勢的變化,讓“軟著陸”變得更具挑戰性。李曉教授稱,目前來看,美聯儲仍有希望做到。
發展中國家的危機
更嚴重的危險,正在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襲來,尤其是背負巨額債務的經濟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
結合以往經驗,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通常會造成發展中國家資金流出和匯率貶值,并誘發貨幣危機或者債務危機。這些經濟體,現在的脆弱性比疫情之前更大。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約60%的低收入國家已經陷入或處于債務困境的高風險之中。
世界銀行“公平增長、金融與制度代理”副行長兼預測局局長阿伊汗·高斯(Ayhan Kose)7月12日發布于VoxEU的分析顯示,基于153個EMDE樣本數據,EMDE總債務占GDP的207%,其中政府債務占GDP的64%,處于30年來最高水平。債務積累的規模和速度,加劇了相關風險。

自今年3月起,新興市場國家資金首次開始出現凈流出。截至7月,已經連續出現4個月資金流出。李曉教授認為,以土耳其、阿根廷為代表的部分新興市場,貨幣的貶值壓力將會日益增長,不排除爆發債務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同時,李曉教授指出,中國尚未出現類似的壓力或困境。在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連續資本外流的情況下,中國A股市場卻吸引了超過9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而且,中國雖然面對著些許通脹上行的跡象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卻并沒有明顯的滯脹跡象。
廣東財經大學學者陳美蘭則告訴南風窗,中國也陷入了兩難境地—受疫情影響,中國需要刺激經濟,但如果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會造成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經濟將面臨新的難題。不過,陳美蘭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靈活度高,在疫情沖擊下,也并沒有“大放水”過,還有空間。
陳美蘭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靈活度高,在疫情沖擊下,也并沒有“大放水”過,還有空間。
在陳美蘭看來,全球滯脹對中國來說是把雙刃劍,機遇與挑戰并存。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會帶來中國生產成本的上揚,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一定壓力。外部市場的環境變化,對我們外需的打擊也不可忽視,但在沖擊之外,也會給中國帶來不小機遇。
首先,這是促進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時機。外部沖擊可能會轉化為我們發展的動力。目前,中國新能源發電量占全球新能源發電量的19%,新能源汽車銷量也超越了歐洲成為世界第一。在原油價格高漲的情況下,中國新能源領域或迎來大發展期,有助于中國成為世界新能源的中心。
其次,這會給中國的結構性轉型提供全面契機。即使物價上漲,中國的出口價格仍有明顯優勢,中國的供給能力會有一個很好的釋放。
有觀點認為,我們可以借鑒日本在1970年代的轉型經驗。兩次石油危機迫使日本痛下經濟轉型決心,在能源結構調整、科技創新、產業結構調整及消費升級等方面出臺系列政策,轉型效果十分顯著。該國最先走出滯脹泥潭,70至80年代經濟增速位居大國前列;代表新興產業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取代之前的重化工業成為支柱產業。受益于轉型政策,日本經濟基本面好轉,驅動股市在這一時期一枝獨秀。高端制造及服務業的投資回報,在70年代后期開始明顯上升,逐漸跑贏大市。
不可避免的滯脹
李曉教授告訴南風窗,即使沒有俄烏之戰作為“最后一根稻草”,經濟滯脹也遲早都會到來。俄烏之戰和疫情等不受控的外部因素,只是將其到來的時間大幅提前。
李曉教授表示,此輪滯脹的發生,是貨幣量化寬松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疊加大國博弈、發達國家人口結構變化、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疫情和俄烏之戰沖擊等多重因素的綜合結果。
弗里德曼說“高通脹的本質是貨幣超發”。通脹歸根到底是貨幣數量現象,以較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或服務,是通貨膨脹的本質。
這一認知在上世紀的滯脹中被驗證。為應對飆升的通脹(在當時,美國通脹率一度升至15%),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壯士斷腕”,通過猛然將聯邦基準利率加到20%的手法,以美國經濟經歷衰退的痛苦為代價,打破通脹預期,帶領美國走出滯脹。
李曉教授向南風窗分析道,1970年代發生滯脹的重要背景是,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通過拋掉“黃金魔咒”,不僅擺脫國際收支對貨幣政策的束縛,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增長,更達到了不再必須去“掙到錢”,而是通過在全球資本市場“借到錢”來實現經濟擴張的目的。這導致國際收支逆差已經無法限制通脹。
“而今天,美國已經從‘借到錢演變到‘印出錢。”李曉教授說。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特別是疫情暴發之后,美聯儲為了阻止經濟衰退,采取了無限量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甚至開始直接入市購買國債和金融機構債等,由“最后貸款人”轉變為“最后做市商”。
李曉教授指出,歷史上惡性通脹的背后都有供給原因:貨幣供給過剩、商品供給不足,或者兩者兼備。商品供給不足,比如疫情導致供應鏈中斷以及俄烏沖突導致的大宗商品供應問題,經常為人們所關注。而貨幣供給過剩卻在一定程度上被經濟學家們忽視了。
真正創造信用(比如說廣義貨幣)的,不是中央銀行,而是商業銀行。從這個意義上看,對于那些貨幣經濟發達的經濟體而言,儲蓄是信貸的結果,或者說對于資產購買和投資而言,儲蓄并非是必要的前提,投資者并不依賴個人存在銀行里的資金,而是可以從私人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融資。這與那些以儲蓄作為投資唯一來源的欠發達經濟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伴隨著西方發達國家貨幣放松管制,商業銀行和諸多影子銀行擁有了創造、定價和管理信貸的權利,導致了金融行業的肆意擴張,甚至大部分金融交易同實體經濟的商品和服務沒有直接關系。
伴隨著西方發達國家貨幣放松管制,商業銀行和諸多影子銀行擁有了創造、定價和管理信貸的權利,導致了金融行業的肆意擴張,甚至大部分金融交易同實體經濟的商品和服務沒有直接關系。
另一方面,在這些發達經濟體中,銀行借貸是一個雙向的過程。雖然商業銀行可以提供各種優惠條件,但真正觸發信貸增長的是借款人而不是商業銀行,這取決于借款人的信心。所以,市場預期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當市場經濟走弱,尤其是市場預期和信心不足的時候,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和服務的現象就會發生。
當投機活動猖獗,資本市場泡沫巨大的時候,一旦泡沫破裂,市場流動性就會突然短缺。資本市場的流動性稀缺和實體經濟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又將導致嚴重的通貨緊縮。這也正是貨幣的詭異之處,由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只有一步之遙。
李曉教授認為,我們需要看到更加嚴重的問題:世界經濟并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真正走出來,我們不能只看到GDP有所恢復。
全球性信貸泡沫作為引發金融危機的動因,從來沒被真正消除。相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操作,一直使得資本市場的泡沫處于加速膨脹狀態。央行并沒有真正強化對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監管,而是采用了一系列貨幣工具,來幫助銀行和金融機構清理資產負債表,進而使它們可以繼續獲得廉價資金用于投機活動。
李曉教授說,本輪通脹或者說本輪滯脹,是美聯儲從2008年以來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必然結果。2020年在疫情沖擊下,它更是“開閘放水”,推出多輪大規模刺激政策。
美元體系的運行和央行的貨幣擴張—這些導致危機的本質因素,不能在本輪滯脹研究中被忽視。
李曉教授強調,很多睿智的經濟學家都已經感受到一場金融危機正在向我們走來,只不過不知道它會在何時、以什么方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