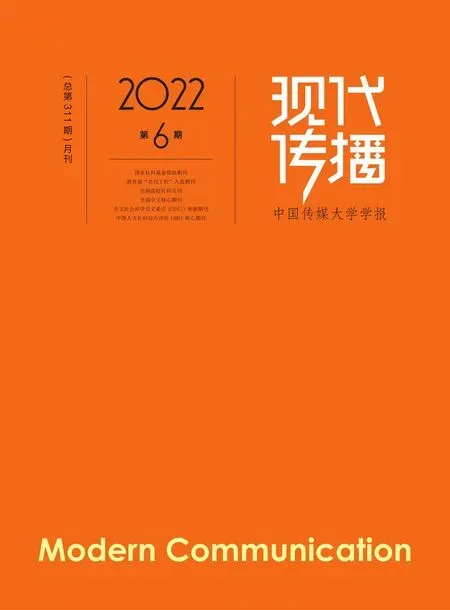中國影像故事的“敘事—共情—跨文化”互動機制模型*
——基于對“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的分析
周 翔 付迎紅
一、間性哲學思維下的共情敘事與共情傳播
共情現象起初在心理學及神經科學領域得到關注。心理學學者Decety和Jackson認為:“共情是指理解和回應他人獨特情感體驗的能力……共情可被認為是兩個個體間的互動,其中一方經歷和分享另一方的感受。”①Gladstein進一步區分出認知共情和情緒共情,分別指“在理智上接受另一個人的角色或觀點”,以及“以同樣的情感對他人的情感作出反應”。②這意味著在情感上你和他人有著相同的感覺、產生相同的情緒,認知上你能理解他人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鏡像神經元參與模仿,輔助體會他人情感,該系統被視為人與人之間產生共情的神經基礎;③其活動還富有哲學意味,這一系統激活了“個體在世界和自我的交互,以顯現心靈的本質”④,也為解釋、理解主體的內在體驗提供可能。但是,對共情的闡述還需要超越生理基礎,承認其受到更大范圍的社會文化交互影響。我們或許可以首先從人文哲思中牽引出共情思維。
(一)間性哲學思維:共情智慧生發之域
為破解當前全球本土化存在的跨文化悖論,即“普遍性”與“特殊性”難以統一、全球化與本土化難以平衡,跨文化傳播學者單波提出轉向一種文化間性,推動多元文化身份的互信交往,維持不同文化間的互惠交流以此共享共同的世界和文化的多樣性。⑤史安斌也指出,為適應劇變及當前全球社會與文化的復雜,理應將“跨文化傳播”升級為“轉文化傳播”,因“跨”仍基于西方中心范式支配下的“現代化”話語體系下,而“轉”通過一種“賦能”凸顯了動態結構下不同文化主體間的平等對話。⑥可見,在文化互惠如何可能的問題上,學者們尋求的解決路徑蘊含著文化間性的思維與溝通、對話的共情智慧。
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關于自我與他者、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命題的討論成為現代哲學的重要轉折點,自我是如何與他者、與世界互存受到了關注。自我與他人并存,并經過意向交流建立關系,構成了一個世界,主體之間可以通過一種“移情”來促成某種共識。⑦哈貝馬斯則在反思近代認識論哲學中的主體性基礎上拓展了胡塞爾的主體間性理論,他認為個體要在主體間性關系中與他者照面,此外他還批判了工具理性對交往領域的宰制及由其引致的價值困境并提出了一種交往理論范式,形成一種以主體間性為核心的理性。⑧
文化間性是主體間性理論在處理文化層面問題上的一種延展,文化各主體尊重和包容他者的差異,不同的文化間能夠借由協商通達一條多元、開放的道路,并且在這種相互作用和關照中重新審視自我。文化間性呼應了主體間性強調的主體與主體的共在而將不同文化的共在作為前提,文化間性中的差異哲學還凸顯了差異的重要性,多元文化在動態的相互作用中實現交流對話。⑨主體間保持對話反映了社會、歷史、文化的交互關聯,且文化間性超越了跨文化而更具包容性。⑩不論是“主體間性”還是“文化間性”,兩者都指向了主體的共在、文化的共存,借由對話使“你”和“我”成為“我們”,也由此更好地駕馭多樣性。這種間性的哲學思維為闡釋共情提供了哲學基礎。
中國古典哲學中也存在有待汲取的共情智慧。儒家理論體系中的“惻隱之心”“忠恕之道”等思想與共情觀有著相似的原理。《易經》的審美理想和價值表達所追求的和諧統一的融合理念為共情奠基,這與傳統西方范式劃分感知主體和感知客體的思維有所差異,向自然的走進、對融合的擁抱促成發展出持續的對話溝通。
溝通、對話式的哲學思考豐沛了共情的基理,從這個維度來看,主體間互相走近對方、保持對話是有必要的,共情智慧的培養理應成為不同文明深度交往的開端。拉近文明間距離并實現共情互動,以尋求可達致認同的價值理念,而傳播者拓寬交流、交往可能的基石也在于挖掘蘊含共情思想的理念。
(二)強化互動、通感與多樣的敘事共情與跨文化傳播
海外學者在喚起共情上探索出多樣化的敘事技巧。Suzanne Keen所提出的敘事共情理論包含了關聯性戰略共情、大使式戰略共情、廣播戰略共情三種共情敘事策略;其中,廣播戰略共情號召“每一個受眾通過普遍化表述來強調共同的弱點和希望,能夠感受到自己為某一個群體的成員”。強化共性以促成內群體認同,這承襲了共情更易增加群體內歸屬感的認知,也與跨文化傳播者們找尋相似文化脈絡的沖動不謀而合。互動敘事與共情間的聯系亦被強調,互動的體驗尤其滿足青年受眾對更具互動性和個性化的傳播形式的偏好。Lutsenko借助于敘事學,透過角色認同、過度沖突范式、敘述者視角闡釋、情境共情等方式加強讀者對作品的共情水平,這在不同層次的敘事作品中也得以體現。
由敘事視角切入研究共情和跨文化傳播從而將文本置于動態的關系中,這有助于理解共情的實現過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明和道德觀在面臨倫理沖突困局時產生了更加多元化的敘事要求。Clair等強調以更包容的敘事方式鼓勵采集多種敘事、收集背景故事、發展跨文化關系。這種方式允許傾聽各種各樣的敘事,包容對立觀點的出現,從不同視角講述故事以獲得更全面的敘事。對于理解分化或調和的政治來說,記憶在政治話語中醞釀的情感力量及其共情能力至關重要。并且,這種話語的吸引力來自民眾的記憶和情感,經由社會和歷史的話語轉換為民眾自身的記憶。譬如,“一帶一路”倡議訴諸民族遺產,將整個中華文明作為一種積淀長久的歷史力量加以利用。同時,使用記憶資源觸發共情應避免將記憶過度政治化。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沖突僵局下,雙方長期沉浸在各自固有的敘事中。Fischer在思考如何改善這種分裂的政治關系時肯定了民間力量在記憶敘事中調和者的作用,面對深刻的矛盾呼吁建立共情意味著“任何試圖轉變沖突的嘗試都需要承認對方的歷史敘事”。
紀錄片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敘事方式,已發生“自我陳述”向“他者敘事”的轉向,“小敘事”、強化“共通感”等敘事策略加強了紀錄片國際傳播的效果。發展身體在場式的敘事手段、由外國人在第一現場講述中國故事這樣具體化的敘事能夠帶動受眾投入,增強共情體驗。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他者敘事”的路徑創新無疑為傳統敘事提供了新的契機。紀錄片《美國工廠》展現了一條從前置情緒共情走向后置認知共情的通路;在突破跨文化屏障時,敘事對象、溝通手段、情境三種要素需要得到配合調適,并在敘事中與他者對話,合塑形象,實現共情效果。另外,多模態表達方式如短視頻敘事經驗日益運用于當下對外傳播。CGTN 在新聞評論的對外傳播中以多種可視化手段追求評論的敘事創新。而CCTV非洲頻道也在借由正在崛起的非洲敘事塑造形象,加大海外受眾的共情體驗與對媒體品牌的認可,提升跨文化關系。
本文以“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為研究對象,重點以《穿越海上絲綢之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影像故事樣本展開分析,探索如何在跨文化敘事層面講好中國故事,找尋不同文明間可增進文化認同的敘事共情點以及發展共情的敘事策略,進而發展跨文化關系、拓展意義共享空間。此外,本文試圖超脫案例樣本經驗性材料,“以點帶面”抽象出一個整體性通達跨文化共情的敘事邏輯。
二、“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敘事共情分析
(一) “自我”與“他者”雙重內部視角講述“我們”的故事
通過第一人稱的自我敘述形成集中于主人公的單一焦點和內部視角,這種敘事技巧最能促進角色認同和讀者的共情。“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代表性作品《穿越海上絲綢之路》中常見第一人稱“我”或復數代詞“我們”的自我敘述來講述個人或群體與絲路故事。投身大海的航海家翟墨的個人故事、流離在外的王式鐵觀音海內外族人歸鄉的家族故事等都呈現了一條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絲路,他們自我評價的經驗與感知營造了與觀眾更親密的互動氛圍,觸發觀眾在情感上的共情。《絲路,重新開始的旅程》也通過普通工人、商販、手藝人、企業家等不同民間面孔的自我陳述譜寫了60個各具特色的絲路故事。
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主持人薩姆·威利斯重走“海上絲綢之路”,親臨中國及沿線國家的現場,以“身體在場”的敘事方式實地參與不同文明的日常生活場景構建,行走于多種文化之間,實現多元化的“絲路”精神跨文化適應過程。透過第一人稱“他者的話語”來講述“一帶一路”故事,借由這種方式,海外觀眾對于“一帶一路”的認知不是“他者的想象”,而是通過他們自身文化的主體對中國文化及沿線各國文化的深描來感知中國故事,與沿線觀眾共感、共情。
此外,強調角色認同與情境共情的敘事技巧不容忽視。相對外化的關于人物經歷和心理狀態的陳述,敘事情境中對人物的內部或外部透視有助于受眾的共情體驗。《穿越海上絲綢之路》第三集《原鄉》中的角色人物王琳娘講述了父親對故土深深的眷戀,離散多年的親人在故鄉重聚的場景觸發了觀眾尤其是飄零在外的海外華人尋找精神家園的期盼,人物主體自身所陳述的對原鄉的熱愛與深情配合畫面語言符號資源容易建立起受眾對片中呈現的敘事情境、角色故事的共情。
(二)傳遞、喚起、增強共情的視覺語法三重意義
紀錄片語料中往往會運用到各種符號資源。對具體語境中的語篇意義而言,視覺影像與組合相伴的符號資源構成了一個動態的有機整體。Kress與Van Leeuwen率先提出多模態視覺語法系統的語篇三種意義:再現意義(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動意義(interactive meaning)及構圖意義(compositional meaning)。
1.再現意義:敘事再現“生活世界”,傳遞情感共情
再現意義反映了語篇中事件、人物、環境等之間的關系,可分為敘事再現與概念再現。敘事再現中,參與者被向量連接起來,可以展現出參與者的動作、參與者間的互動以及事件的變化過程。由此,敘事再現又可分為行動過程、反應過程、言語過程和心理過程。而在概念再現中則不存在向量,反映的是參與者之間一種靜止、固定的關系,表達的是一種屬性、類別或意義。
在《穿越海上絲綢之路》中,畫幅大多以敘事再現的形式展示敘事過程,參與者間構成強烈的對角線,形成向量。紀錄片中多展現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們彼此互助的場景,參與者發出向量信號,敘事的行動過程和其他參與者的反應過程被反復呈現,如再現人們鼓掌歡呼、相互擁抱的動作和喜悅的神情,這種情緒的直接表達傳遞了一定的情感力量,不同膚色、不同文化的人交流共享歡愉的場景,極富共情感染力。
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著重表征人物、環境和事件之間的交際關系。該片中有一個片段,剛果人博伊卡、英籍主持人威利斯與中國友人在廣州街頭攀談,三人的目光向量聚焦在畫面中心,他們與背后布滿了中國商店的街道環境構成一個整體,畫面呈現了日常生活中一個極為平常的場景,也反映了人與人之間、不同文化之間展開交往的直接窗口。紀錄片回歸到日常生活敘事中,建構了影視空間中西方與東方、“我們”與“他們”交錯混合的“生活世界”,讓海外觀眾置身于這個場景中感受異文化、激發情感共情。
2.互動意義:構建親密關系,喚起共情
互動意義指互動參與者和表征參與者相互作用的關系,體現參與者之間的人際關系。這兩類參與者存在于每種符號行為中,前者是圖像制作者或觀看者,后者是所表征的代表即構成交流主題被觀看者討論的對象。互動意義關涉接觸、距離和態度(視角)三個層面。接觸主要構建了一種參與者與觀看者目光實現接觸的關系,依照目光是否對接可分為“索取”與“提供”兩類圖像,“索取”類互動參與者與表征參與者有目光交流并可直接向觀看者傳遞信息,而“提供”類則弱化了參與者間的互動。從距離方面看,距離的遠近暗示了互動參與者與表征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在態度層面上,態度可由圖像或畫面的拍攝視角來建構。水平角度通常以正面角度切入意味著一種卷入,意圖將觀看者融入圖像世界;垂直角度反映參與者與觀看者的權力關系,平視視角代表平等關系,仰視凸顯參與者的權威,俯視則凸顯觀看者的強勢。
紀錄片《一帶一路》《穿越海上絲綢之路》融合了豐富的鏡頭景別并不斷切換組接技巧,在描繪一些更具共情張力的情境時,畫面會由遠轉近,將觀看者納入畫面世界中以增添共情力度。由敘事再現中法航海家時隔30余年見面重聚畫面,著重建構了一種親密的社會關系。畫面定格在中心人物上呈現其肖像、表情,中心人物直視觀看者,與觀看者建立了“接觸”關系,傳遞一種“索取”交流的信息。近景鏡頭拍攝也使得參與者、觀看者被構建出一種個人距離的關系,另外拍攝畫面是正面的、平視的視角,觀看者與畫面中人物呈現平等關系,被引入到情境中與畫面中人物同處一個世界,擁抱過去激情的歲月和跨越文化、跨越光陰的友誼,喚起人類渴望交流的共情力。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推出了一個主持人作為絲路故事的講述者的角色,令其以西方的視野來審視東方題材,吸收了西方紀錄片的敘事邏輯和故事化的敘事方法。另外,該片十分注重強化表征參與者與互動參與者的互動關系。表征參與者威利斯的框架大小盡可能縮小,他的目光與觀看者實現了直接接觸,觀看者“卷入”威利斯所處的世界,拉近了二者間的距離。尤其對信息表達較為間接的高語境文化而言,信息傳播對環境更為依賴,傳播者和接收者是否處于同一文化體系對傳播效果有一定的影響。在此片中,維持表征參與者與觀者的親密關系不僅在視覺語法上縮短了傳受的距離,在文本信息的譯碼與解碼上省去了譯介這一可能造成文化干擾的環節,利于信息意義的完整表達,也更易為西方受眾搭建一個共情環境。
3.構圖意義:整體布局增強吸引力和共情力
構圖意義涵蓋信息值、顯著性和框架三個部分。“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綜合運用了符號資源,并在全局構圖上協調布局、協同感官合作。在《穿越海上絲綢之路》第8集“輪回”中,原斯里蘭卡總理森納那亞克的孫子查圖克展示了承載中斯歷史的一根拐杖,拐杖作為傳遞歷史友誼的見證物被置于畫面右側,體現的是新信息,這個象征符號同時被置于前景位置,拉近了與觀看者的距離。在框架方面,畫面人物王路東與查圖克兩個表征參與者的向量方向指向畫面中央,分隔線條不明晰,兩個人物構成了一個視覺上的整體,讓觀者感知到二者同屬于一個部分,觸發觀看者對遙遠的歷史的記憶,提升觀看者的認同感和共情。類似地,《共筑未來》《共同命運》等紀錄片畫面也盡可能淡化畫面中各成分的分離,著力給觀眾呈現在空間上同屬一個整體、畫面各成分相容的局面。
(三)“陌生化”敘事技巧與敘事語境構建跨文化復合身份
“一帶一路”題材紀錄片呈現了某種“陌生化”敘事的技巧,以“他者”作為主體介入,來講述中國故事。“陌生化”是俄國形式主義伴生的核心概念之一。領袖人物什可洛夫斯基認為,藝術的手法能夠把事物“陌生化”,這種藝術化的加工利于感受對象的生動性和豐富性。不管是對于中國受眾還是海外受眾來說,由外國人講述中國故事,陌生的敘事主體呈現了陌生的敘事視角,有利于掙脫舊有思維方式的束縛以及對中國故事的意義負荷,由此重新認識中國故事的鮮活性。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外的成員就不再是一個被懸置的“他者”,“我”與“他”的分隔對立被消解,跨文化主體在傳播交流中重構了多樣化的角色身份,并融合形塑了一種超越中外文化的復合人格和新的文化身份。“陌生化”技巧也帶來了一種單一文化不具備的敘事視角,通過一種跨文化協作來彰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并實現文化交流中的跨文化適應性。“陌生化”技巧在跨文化傳播中的使用有助于減少橫亙在中外文化之間存在的文化逆差,在多種文化間跨界生存,調和文化需求的復雜性。如紀錄片《對望:絲路新旅程》,在中外合作制片的模式下實現“自我陳述”與“他者敘事”的結盟,聯通“自我”與“他者”,為受眾帶來別樣的審美體驗,促成跨文化對話的意義共享和共情感受。
當然,這種敘事技巧的使用還需建立在對敘事語境的充分理解之上。語境還具有動態性的本質,在不同文化群體交際互動的狀態下也在持續發展,理解語境的動態本質也為展開更具針對性的跨文化傳播提供基礎。在特定的語境下,互動雙方所遵循的規則應由雙方相互協商而成,而非文化的一端向另一端的單向適應或語碼轉換。在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殊性的基礎上,理解和接受文化差異更易建立起主體間的“關系共情”,這涉及雙方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三、發展跨文化關系的新可能:“敘事—共情—跨文化”互動機制模型
在以上對紀錄片敘事分析基礎之上,本文進一步圍繞“敘事”“共情”和“跨文化”三個要素提煉出一個講好中國影像故事的模型(見圖1)。

圖1 講好中國影像故事的“敘事—共情—跨文化”模型
具體而言,在敘事與共情的互動層面,透過敘事結構、敘事外部物理條件與視覺語法再現敘事內容的三重作用完成共情的自下而上的情緒分享過程和自上而下的認知調節過程。在敘事結構上,呈現敘事主體行動構成的空間敘事在還原敘事情境時空關系、歷史與地理關系從而喚起共情上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比如在紀錄片影像中,借助“表征性空間”的建構呈現承載著特殊文化印記、精神的文化景觀空間符號與敘事者行動脈絡,易于激活民眾記憶和情感能量、傳達共通意見和信念、深化敘事情境共情體驗并實現不同文化主體的相互融通。
情感共情的喚起相對而言較為快速,而共情的認知調節層面則常被忽略。在敘事的內容層面上,生活敘事回應了認知共情的有效性。生活敘事不僅是在視覺語法上對敘事參與者互動過程的再現,也是對多元文化主體建立關系、經驗協商和共享的基礎領域的直接顯現。這要求敘事回歸到鮮活的、現實的人能夠體驗到的生活世界,以本質的人的生活意義為中心,恢復個體的人的主體性。敘事必然要還原文化主體本真的世界,由此聯通不同文化群落的生活經驗和共情心理,走向與他者不隔膜、彼此相通的共同存在。這樣的彼此敞開提供了“自我”與“他者”共通的知識、觀念等認知基礎,利于“我們”關系的建構與主體間交流質感的提升。
模型中,“敘事”與“跨文化”兩個要素則在語境與主體的嵌入下構成互動。敘事為超越不同文化圈層、認識他者、反思自我引導了話語實踐方向,跨文化為敘事超脫單一、靜止的故事文本豐富了視野。不管是在講故事的敘事起點還是凝聚跨文化認同的目標上,語境的復雜性和敏感性始終裹挾其中。共享語境與針對性語境共同為跨文化傳播效果的實現助力,利于超越、調和跨文化差異。意義的傳遞根植于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針對性語境信息的提供則豐富了故事的多元性和不同文化主體的復調合鳴。作為敘事、跨文化主體的“自我”與“他者”深層介入至故事的講述及不同文化主體的互動中。在跨文化互動中,“自我”與“他者”在各自的敘事中實現在場,“自我”的經驗和理念與“他者”緊密勾連,在“他者”的映照下審查自身并形成了相互認知的基礎。講好中國故事也在“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張力下進一步推動跨文化目標的實現。
在“敘事—共情—跨文化”的互構中,共情承擔了作為一個連接體的中介橋梁作用。有效的跨文化傳播不止停留在信息傳播層面,更關注信息傳播的質量,而透過有活力的敘事引證、重塑中國故事資源可喚起不同群體的共情。可以說,喚起共情是“一帶一路”故事最終達成跨文化溝通理解及內化認同必經的通路。在共情的驅動下,不同文化主體在跨文化交往中實現持續對話交流的基礎。“一帶一路”故事的跨文化抵達在共情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凝聚共識的跨文化共同體是最終目標。在共情路徑的指引下,與他者文化進行碰撞,關照不同文化主體的異質性,借此審視自身文化,在互動協商中共造新的意義空間。不同的文化主體間互相融合、滲透,通過一種更具包容性、更可行的復合體意義空間的創造,各主體能夠在相互期望的框架內形成更廣泛的共識,由此可在跨文化實踐中彰顯主體間性與文化間性。
同時,“跨文化”“共情”也在互動中綿延出一種關系共情的狀態。這種跨文化關系共情并不意味著拋卻本土的文化,而是把自己置于對方的語境下來理解和接受差異。無論存在著何種差異,尊重和包容是基本素質。關系共情始終是雙向的,不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而總是來自相互依賴的雙方參與者,來自雙方循環的互動。在“間性”智慧的關照下,“共情”與“跨文化”保持著對話關系。“共情”“跨文化”二者追求的是開放的、未完成的永恒對話,反映的是不同文化主體、多種聲音交叉的“復調”對話,而非擁護統一意識、統一思想的單調獨白。
注釋:
① Decety J.,Jackson P.L.ASocial-NeurosciencePerspectiveonEmpathy.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15,no.2,2006.p.54.
② Gladstein G.A.EmpathyandCounselingOutcome:AnEmpiricalandConceptualReview.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vol.6,no.4,1977.p.77.
③ Decety J.,Michalska K.J.NeurodevelopmentalChangesintheCircuitsUnderlyingEmpathyandSympathyfromChildhoodtoAdulthood.Developmental Science,vol.13,no.6,2010.pp.895-896.
④ 馮艷霞:《從神經元活動到社會化的心靈》,《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4年第1期,第32頁。
⑤ 單波、姜可雨:《“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論及其解決路徑》,《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第46頁。
⑥ 史安斌:《從“跨文化傳播”到“轉文化傳播”》,《國際傳播》,2018年第5期,第2頁。
⑦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 255頁。
⑧ 參見[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哈貝馬斯精粹》,曹衛東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⑨ 鄭德聘:《間性理論與文化間性》,《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第74頁。
⑩ 蔡熙:《關于文化間性的理論思考》,《大連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