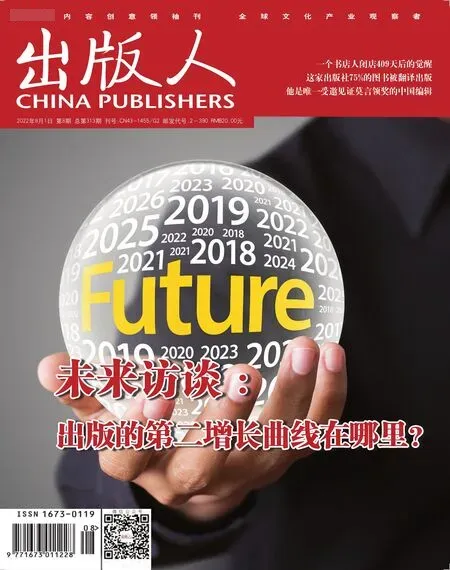青少年需要什么樣的《紅樓夢》
文|李文倩

《紅樓夢》的青少年版的改編,是一件必要必須必然的文化盛事,要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探索創新,并兼顧兒童心理學、接受美學等多學科觀照和審視。《紅樓夢》的詮釋與接受,本身就是一個難題。對此,魯迅先生曾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對作品內容的豐富性和多義性給出了一針見血的評價:“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由此可見,即使是成年人,在《紅樓夢》的觀感上,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
隨著近兩年“青春國學”熱的興起,傳統文化如何在青少年中傳播傳承,成為一個關注點。而古典名著改編為兒童文學作品,對于青少年學習傳統文化,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由此,研究古典名著在兒童文學中的改編,就成為一個并不新鮮的“新話題”。作為“四大名著”之一,《紅樓夢》是國人的必讀書,對于青少年的文學啟蒙尤其引人關注。然而,由于青少年的價值觀、人生觀尚未成形,他們需要什么樣的《紅樓夢》,應該給他們什么樣的《紅樓夢》?這就成了一個問題。
《紅樓夢》改編的難點
同樣是作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記》的兒童文學改編,實踐是最多的,形式最為多樣,研究也最豐富。盡管較之其他作品,《西游記》的復雜性和多義性絲毫不少,但其神話外殼和人物塑造,天然非常貼近兒童文學。尤其在后來的影視、動漫類改編中,更凸顯了其正能量的價值,廣受少年兒童和家長的喜歡和推崇。同樣的,《三國演義》之于“仁義”,《水滸傳》對應“正義”,雖是以偏概全,卻都可以剝離出一個相對簡單的主題和線索,進行兒童化改編。
然而,《紅樓夢》的情況就有些不容樂觀了。因其“大旨談情”,《紅樓夢》的兒童文學化并不順利,反倒是阻礙重重。由于社會偏見和傳統道德的束縛,加上《紅樓夢》自身的龐大復雜深邃,它很難在兒童閱讀中得到鼓勵和提倡。相應地,對《紅樓夢》的兒童文學改編的研究寥寥可數,實踐亦乏善可陳,市面可見多為一些原書的改寫刪節版,遠遠沒有系統化和科學化,且難以抽出一個“政治正確”的主題。內容改編難是其一,其次則是形式難。《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無論是影視化還是漫畫式,名著重構的工作難度和工作量都比較小。但《紅樓夢》改編的文學性與兒童性,則是一個疑難。
同時,作為我國古典小說的登峰之作,《紅樓夢》復雜的敘事結構、眾多的人物、藝術的爐火純青等等造詣,恰恰為其改編造成了巨大的難度。改編淺,容易流于淺薄;改編深,容易礙于傳播;改編少,容易失之煩瑣;改編多,又難以傳其精髓。在兒童化和通俗化的道路上,《紅樓夢》的改編無異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其實講述紅樓故事,不一定要求全責備,更不必遮遮掩掩,應把重點放在紅樓啟蒙,幫助青少年兒童了解紅樓文化、走進紅樓人物、體味紅樓美學、品讀紅樓人生。引起青少年的紅樓興趣,普及相關文化知識,這便完成了《紅樓夢》改編的主旨和大意。
簡言之,青少年版的《紅樓夢》應該傳達什么樣的主題和價值,又應該采取何種形式呢?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條根本的原則就是,內容上取精華而棄糟粕、留情而祛色,形式上貼近兒童、喜聞樂見,將《紅樓夢》由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改編為啟迪人性美、人情美的入門書。
《紅樓夢》改編的重點
《紅樓夢》的兒童文學化,首要的是內容的再消化、再吸收、再創造,以期達到和現代對話、和兒童對話目的。
首先是語言的改寫。《紅樓夢》采用通俗文寫作,文白夾雜,盡管讀起來障礙不大,然而青少年接受起來,尚有難度。然而,《紅樓夢》的語言又極富色彩,給人以美的享受。在改編的過程中,既要注意保留其滋味,又要進行現代化和兒童化轉向。太文了,難以接受;太白了,又如清水煮菜,缺少趣味。這就給改編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改編者的文學語言修養和文化底蘊必須要深,要則是能夠最大限度上保留紅樓語言的美感和韻味。比如,其中寶黛釵之間以及眾多丫鬟小姐諧趣橫生的日常對話,以及恩恩怨怨的打趣調笑,處理得當就會興味盎然,完全采用現代漢語平鋪直敘就全然少了內涵韻味。改編《紅樓夢》,雖然不必字字珠璣,但也要以“信達雅”為宗旨,方能開辟出一片天地,而不是簡單地古今轉換、畫虎類貓。
其次是內容的改寫。這也是《紅樓夢》改編的“大手術”所在。大量的情節需要刪除,大量的人物需要隱藏,大量的線索需要舍棄。簡單說來就是刪繁就簡、突出主線。保留神瑛侍者和絳珠仙草下凡的神話外殼,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以寶黛愛情為主線,鋪陳金陵十二釵的人物命運,描寫其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而對于秦可卿淫喪天香樓、風月寶鑒、寶玉摔玉等情節,則可以大刀闊斧刪節,以保持敘事的專注度。不重要的人物或者故事,適當保留痕跡和線索,不做展開,避免節外生枝。
正如梁靖華在《以鄭淵潔〈紅樓夢(少年兒童版)〉為例談兒童文學對〈紅樓夢〉的改寫與取舍》一文中指出的:“可以說,《紅樓夢》原著是立體的,是無限的,是現實的,是廣闊的,依附著一個完整復雜的世界;而兒童版《紅樓夢》是平面的,有限的,‘故事性’的,簡單的,更純粹地像是作為‘故事’而存在。”講好紅樓故事,可以最大限度上貼合青少年的需求,符合其成長階段,保留“紅樓情”的美麗線索,而不特別凸顯“紅樓夢”的悲劇特質,實現老樹發新枝。
最后是形式的創新。隨著讀圖時代和小視頻的沖擊,《紅樓夢》兒童文學化的形式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過去,連環畫、小人書等形式,應該說都在經典的兒童文學化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如今,這種形式似乎也并沒有過時,但是也不能因循守舊,需要與時俱進。漫畫、視頻等形式,都應該嘗試。
《紅樓夢》改編的突破點
少年讀紅樓,看到的是家長里短;青年讀紅樓,則看到借物抒懷;成人讀紅樓,側重的是對人生和社會的理解和認識。所以《紅樓夢》青少年版的改編,其突破點就在于故事,也就是新奇、有趣、生動。
近年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少兒啟蒙第一書:紅樓夢》,湖南美術出版社的《紅樓夢連環畫》,中國畫報出版社的《十二集新經典系列漫畫:紅樓夢》系列,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的童話大王鄭淵潔改寫的《紅樓夢》,都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同時,網絡上關于“林黛玉進賈府”等紅樓故事的視頻制作,也打開了經典傳播和解讀的另一扇窗口。
突破口之一是主線條和完整性的兼顧。《紅樓夢》人物眾多、線索繁復,保留太多無法彰顯故事主線,保留太少又會影響故事的完整性。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如何有效地保留名著的原貌,又不顯得過于浩繁,需要作品改編的強大功力。整個紅樓故事的主角是寶黛釵,但這絕非紅樓故事的全部,寶黛釵故事之外還有數不清的枝枝蔓蔓和理還亂的因果情緣。刪什么,不刪什么,刪多少,刪到何種程度,都是有待考量和不斷優化的。
突破口之二是展示性和故事性的兼顧。《紅樓夢》中,亭臺樓閣、珍寶古玩、穿衣打扮等諸多方面,饒有興味,但又篇幅浩繁。這些情景需要擇其要者,予以展示,以保留作品的文化味。然而這些內容也不能太多,容易造成閱讀負擔,給傳播和接受帶來困擾。筆者認為,應該以紅樓故事為重,靈活采用制圖、漫畫、視頻等形式,再現寧榮二府、大觀園、主要房間內飾等,使得書中情景得到有效展示,而又不至于拖累故事敘述,又饒有興味、形象直觀。
突破口之三是小說敘事和詩詞楹聯的處理。《紅樓夢》原著中存在大量詩詞、楹聯作品,需要逐一甄別、認真摘取,以最大限度保存紅樓夢的美感和厚重。這些作品既是構成紅樓主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展示人物命運和內心的重要途徑,也是作品文學性和藝術性的重要載體。然而紅樓詩詞眾多,應該擇其要者和通俗易懂者予以展示,最大限度做到作品原貌的呈現,又不顯得晦澀難讀。
總之,《紅樓夢》的青少年版的改編,是一件必要必須必然的文化盛事,要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探索創新,并兼顧兒童心理學、接受美學等多學科觀照和審視,通過對名著進行再發掘、再創造,打造一批“青字號”和“少字頭”版《紅樓夢》,為名著的傳播普及開辟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