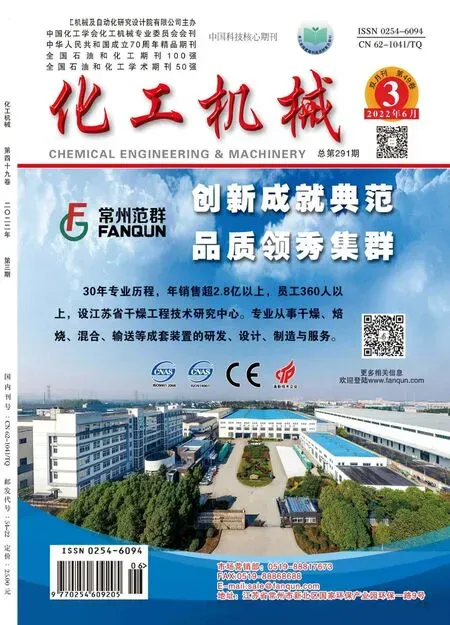熱采井口地面管線位移補償與影響因素分析
丁宇奇 賈 威 蘆 燁 楊 明 李百帥 徐鵬超 葉碧濤
(東北石油大學機械科學與工程學院)
熱采技術是稠油開發的主要方式,然而該方式會使井下套管被加熱并由此引起熱膨脹[1]。 隨著溫度升高,金屬材料的套管將會在溫差作用下產生軸向伸長和徑向變形[2]。當溫差足夠大、軸向作用力大于套管重力、 井口重量等外載荷時,套管將舉升井口,出現井口抬升現象。 井口裝置抬升會破壞井口完整性, 導致井口處地面流程泄漏,從而直接影響油井安全生產[3]。為了避免井口抬升導致井口原油泄漏,國內外已有許多學者從防止井口抬升和補償井口抬升量兩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例如改變固井方法[4]、優化井內套管材料性能[5]、使用熱應力補償器[6,7]及在井下使用套管伸縮裝置等井內措施[8],這些方法可以從源頭上防止井口抬升,但是由于地層的復雜性和井下裝置對精度的苛刻性,井下裝置在長時間的使用過程中很容易失效[9],而且井下設備的更換維修費用較地面要高。 因此,不少學者開展了地面井口補償裝置的研究,例如在井口管系設置補償器來補償井口抬升量。 但是補償器的種類很多,使用條件和補償能力也各不相同。 目前,在管線位移補償方面使用最廣泛的是方形補償器,方形補償器可以很好地完成補償熱力管網膨脹量的任務,而且其安裝運行成本低, 具有良好的經濟性[10]。方形補償器在補償較小變形量時效果較好,但在管線變形量較大時其補償效果并不理想。 對此,杜正明研究了不同類型的補償器在管線伸長量較大時的表現,發現波紋補償器能很好地解決大變形量下的管線補償問題[11]。 波紋補償器由于其結構的特殊性,在使用中要避免橫截面方向上的作用力,在管線受力較復雜的條件下容易損壞并造成管內流體泄漏。 針對這一問題,張再陽等使用旋轉補償器來補償熱力管系的伸長量,通過分析旋轉補償器在熱力管系中的受力和密封性能,得到了旋轉補償器可以在管系受力較復雜的條件下補償較大管系變形量的結論[12,13]。 在補償管系伸長量時,一般是將多個旋轉補償器組合在一起使用,合理布置這些旋轉補償器的位置可以在補償較大管線伸長量的同時節約投資成本。 張藜藜和盧磊對旋轉補償器在熱網工程中的布置進行了優化,提出兩種旋轉補償器與管道布置方式(Z 型和L 型), 并計算了管道布置中最佳的球心距,對工程使用中補償器的個數進行了優化[14]。 張廣新重點論述旋轉補償器在管網上的布置方式,分析單向式、雙向式及三球式等不同布置方式的優缺點,最終得到三球式布置方式可以簡化管線設計,節省投資,使管網運行更加安全可靠的結論[15]。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使用井口位移補償管系能在投資更少的條件下完成補償井口抬升量的任務。 但通過熱采方式開采出來的稠油溫度超過300 ℃,壓力超過10 MPa[16],而大部分管線位移補償器無法在這種工況下安全運行。因此,需要對稠油熱采管線補償器進行選型;同時,為了得到更大的井口位移補償量, 需要考慮管臂長度對補償量的影響。 為此,筆者針對稠油井口抬升問題,建立稠油井口地面管系有限元模型, 使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計算補償管系在井口豎直方向的補償量, 分析不同補償器結構和管臂長度對井口補償的影響。通過消除井口抬升對地面管線的影響,實現井口地面管線的動態密封, 解決由于井口抬升導致的地面管線泄漏問題, 提高稠油井口處地面流程穩定性,保證稠油的安全高效開發。
1 稠油熱采地面管線的位移補償分析
1.1 稠油管線有限元模型建立
選取井口補償管系結構如圖1 所示,主要由直管臂、旋轉臂和軸向旋轉補償器組成。 管道公稱直徑100 mm,直管臂1 長1 500 mm,旋轉臂1 和直管臂2 長均為1 000 mm,旋轉臂2 長1 260 mm,固定支墩高為500 mm。 為了準確描述管系結構特征,選用具有溫度和壓力載荷特性的管道單元對整體管系結構進行模擬,建立的管系整體有限元模型如圖2 所示。

圖1 井口補償管系結構示意圖

圖2 管系整體有限元模型
1.2 井口位移補償管系結構補償評價方法
為了保證管系位移補償量和結構強度,其最大補償量需要滿足:直管臂1 在井口處不發生彎曲變形; 補償管系在固定支墩處不發生水平竄動;直管臂2 不發生抬升,從而保證地面管線不發生泄漏;補償管系和補償器不發生破壞、管內介質泄漏。 由此,建立補償管系位移判別條件如下:
a. 直管臂1、2 保持水平;
c. 井口位移補償管系應力小于管系材料屈服強度;
d. 旋轉部件應力滿足危險路徑處一次局部薄膜應力、 一次薄膜加一次彎曲應力小于1.5 倍許用應力,峰值應力小于3 倍許用應力的強度條件;
e. 旋轉補償器密封件在管內壓力作用下不發生泄漏。
當給定管系結構同時滿足以上5 個判別條件后,方可確定補償管系的最大位移補償量。
1.3 井口位移補償管系補償量分析
所選取井口補償管系的管內介質壓力為16 MPa,溫度為320 ℃,管線和補償器材料Q20鋼的屈服強度為170 MPa。根據上述判別條件,對井口管線的最大抬升量進行迭代計算,最終得到滿足管系補償判據下最大補償量為560 mm。圖3為井口補償管系沿x、y方向的變形圖,圖4 為管系的等效應力分布云圖。
由圖3a 可知,直管臂1 左側變形量560 mm、右側551 mm,左右兩側變形量差值9 mm,此時可認為直管臂1 是水平的; 而直管臂2 左右兩端變形量差值為6 mm,小于直管臂1,因此滿足位移判別條件a。由圖3b 可知,固定支墩位置水平竄動8 mm,即可判定滿足位移判別條件b。由圖4 可以看出, 管系最大應力出現在旋轉臂2與補償器3 連接位置,應力值為67.9 MPa,該應力遠小于材料屈服強度170 MPa,達到了強度評價標準,因此可判斷滿足位移判別條件c。

圖3 井口補償管系沿x、y 方向的變形圖

圖4 井口補償管系等效應力分布云圖
整體管系模型分析中將補償器視為一個整體,但實際上該軸向旋轉補償器是由多個運動部件組成,且整體模型無法計算局部補償器的密封性能是否滿足要求。 因此,為了判斷補償器的強度是否滿足位移判別條件d、e, 需要單獨建立軸向旋轉補償器模型并對它進行強度校核和密封性能分析。
2 局部補償器受力分析
2.1 補償器強度評價
為了分析560 mm 抬升量下補償器強度是否滿足位移判別條件d, 需要單獨建立旋轉補償器有限元模型(圖5)并進行強度校核。 軸向旋轉補償器主要由外殼、芯管、密封填料和滑塊組成,這些構件均為軸對稱空心圓管構件。 然而,部分構件的厚度變化劇烈,同時由于補償器管口的力矩會對構件產生較大的水平方向上的作用力,構件在受力后容易在厚度突變位置產生較大的彎曲應力并發生變形甚至斷裂,因此在芯管厚度突變位置沿厚度方向建立路徑1, 滑塊拐角位置沿厚度方向建立路徑2, 外殼下端接管與主體連接處沿厚度方向建立路徑3, 并對這些路徑進行應力強度評定。
“通過科技成果的轉化,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公司競爭性業務發展,實現科技成果轉化落地。”據李文云介紹,本次科技成果轉化洽談活動還吸引了咸亨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9家國內著名的電力設計制造廠商參加,實現了公司科技成果“走出去”,而活動現場也是“供”“需”兩旺,現場達成合作意向達56項。

圖5 軸向旋轉補償器有限元模型
為了保證補償器模型的分析結果與整體模型中補償器受力狀態相同,需要提取整體模型中補償器與兩端三通連接點處的節點載荷,并將它作為邊界條件施加到補償器管口。 整體管系中3個補償器的邊界載荷見表1。

表1 整體管系中3 個補償器的邊界載荷
由表1 可以看出, 補償器3 與y方向最大力值所在補償器2 相差僅0.4 N,與x方向最大力矩所在補償器1 僅小2.5%;而其余各方向的力和力矩均為最大值。 因此,為了保證井口位移管系有補償器都能正常運行, 筆者選擇表1 中補償器3的載荷值作為力邊界條件施加到軸向旋轉補償器模型中進行計算。 在對軸向旋轉補償器施加溫度、壓力載荷和約束后,得到軸向旋轉補償器的應力分布云圖如圖6 所示,各部件危險路徑應力評定結果見表2。

圖6 軸向旋轉補償器應力分布云圖

表2 軸向旋轉補償器危險路徑的應力評定結果
從圖6 可以看出, 去除管口邊界效應影響后,軸向旋轉補償器最大應力位于外殼下端接管與主體連接處,最大值為60.98 MPa。從表2 可以看出, 路徑3 上的應力均大于路徑1 和路徑2,這是因為路徑3 經過了補償器應力最大位置,其強度評價時的一次加二次應力就等于補償器的最大應力60.98 MPa。 從3 個路徑的評定結果可知, 所有應力評定路徑均滿足強度評定要求,因此滿足位移判別條件d。
2.2 補償器密封性能分析
填料密封依靠壓蓋的軸向壓縮把填料壓緊,當填料與芯管發生相對運動時,填料產生徑向力擠壓芯管并與芯管緊密接觸, 從而實現徑向密封。 筆者對軸向補償器密封處的接觸壓力與稠油管線運行壓力進行對比,若接觸壓力的最小值大于16 MPa,則認為達到密封要求。 填料與滑塊接觸位置的接觸壓力分布如圖7 所示。 從圖7 可以看出,在管口載荷的影響下,芯管會產生一定的傾斜,導致填料與滑塊接觸位置的接觸壓力分布不均。 接觸壓力范圍為16.9~26.8 MPa,最小接觸壓力大于管內介質壓力16 MPa,填料密封可以達到密封要求。 由此可以判斷滿足位移判別條件e。

圖7 填料與滑塊接觸位置接觸壓力分布云圖
綜上所述,由直管臂兩端最大位移差值為9 mm 可以判斷直管臂1、2 均保持水平狀態;從直管臂2 僅移動了8 mm 可以認為, 直管臂2 在固定支墩處幾乎沒有竄動;結合整體管系最大應力為67.9 MPa,低于材料屈服強度,可以判斷井口位移補償管系應力滿足強度條件;局部補償器的所有應力評定路徑均滿足強度評價條件,由此可以判斷補償器滿足強度評價條件;最小密封壓力為16.9 MPa,大于管內介質壓力,由此可知補償器密封性能滿足管系運行要求。 結合1.2 節的5 個判別條件, 最終得到井口管系最大位移補償量為560 mm。
3 熱采井口地面管系位移補償量影響因素分析
3.1 管臂長度
結合位移判別條件a、b 可知,管系重量會直接影響最大位移補償量。 因此,筆者將通過改變管線長度來改變井口位移管系的重量,通過分析補償管系的變形情況研究管線長度變化與最大補償量之間的關系。
在補償器2 位置不變的條件下,直管臂1 增長時,旋轉臂1 將縮短且斜率變大;直管臂1 縮短時, 旋轉臂1 將增長且斜率變小; 從直管臂2和旋轉臂2 的連接形式可以看出其運動規律與直管臂1、旋轉臂1 相同,由此可見改變直管臂的長度時旋轉臂長度必將發生改變。 根據這個特性將井口管系管道分為兩組,單獨改變直管臂1 或直管臂2 為一組, 同時改變直管臂1、2 為另一組,以直管臂1、2 長度為變量建立稠油管線最大補償量的目標函數F(t):

將管臂的改變量設為±500 mm, 補償量匯總結果見表3。由表3 可以看出,隨著直管臂1 的增長,井口補償量下降,當直管臂1、2 同時增加500 mm 時, 井口補償量下降幅度達到了23.4%;隨著直管臂1 的縮短,井口補償量增大,當直管臂1、2 同時縮短500 mm 時, 井口補償量上升幅度達到了117.7%。 由此可見,同時縮短直管臂1、2 能最大程度地增大井口位移補償量。

表3 井口位移補償管系的最大補償量
3.2 補償器結構
考慮到稠油井口管系結構的復雜性和載荷的多樣性,旋轉補償器是補償井口抬升量的最佳選擇。 旋轉補償器根據結構的不同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軸向旋轉補償器,另一種是萬向旋轉補償器。 其中,萬向旋轉補償器主要由外殼、芯軸和密封環組成,由于其芯軸是球形的,因此可以補償空間位移量。 萬向旋轉補償器有限元模型如圖8所示,在球形芯軸上與密封環接觸位置沿厚度方向建立強度評定路徑1, 以評定球形芯軸與密封環接觸引起的應力集中;在外殼上密封環凹槽沿厚度方向建立強度評定路徑2。

圖8 萬向旋轉補償器有限元模型
對局部萬向旋轉補償器模型施加與軸向補償器相同的邊界條件后,得到萬向旋轉補償器的應力分布云圖如圖9 所示,萬向旋轉補償器各危險路徑評價結果見表4。

圖9 萬向旋轉補償器應力分布云圖

表4 萬向旋轉補償器各危險路徑評價結果
由圖9 可以看出,最大應力213.35 MPa 出現在球形芯軸中間,該處的應力主要是由溫度和壓力引起的彎曲應力。 由表4 可以看出,路徑1 的應力未達到強度評價要求,說明稠油井口管系補償量在560 mm 時萬向旋轉補償器不滿足位移判別條件d。 由于萬向旋轉補償器的密封是由密封環、外殼和內部球形芯管共同完成的,并且密封面積隨著內部球形芯管的變形而變化,因此不能單獨用接觸壓力的大小來判斷萬向旋轉補償器的密封壓力是否滿足要求。 為此,筆者建立球形芯軸與密封環、外殼與密封環沿最小接觸壓力路徑上的壓力值曲線(圖10、11),以曲線上接觸壓力大于最低密封壓力的路徑長度是否大于1/3 來判斷萬向旋轉補償器是否滿足密封要求。

圖10 內部球形芯軸與密封環接觸壓力曲線

圖11 外殼與密封環接觸壓力曲線
從圖10、11 可以看出,球形芯軸、外殼與密封環接觸壓力大于最低密封壓力的路徑長度明顯大于1/3, 因此可以判斷萬向旋轉補償器能夠達到密封要求,此時萬向旋轉補償器滿足位移判別條件e。 但是由于萬向旋轉補償器不滿足位移判別條件d, 因此560 mm 不能作為萬向旋轉補償器管系的最大補償量。 為了得到萬向旋轉補償器安全運行的最大補償量,逐漸降低井口補償量并提取整體管系補償器管口載荷從而施加到萬向旋轉補償器中以進行迭代計算,最終得到滿足位移判別條件a~e 的整體管系最大補償量為520 mm。
將軸向旋轉補償器和萬向旋轉補償器能安全運行的最大補償量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在保證補償器安全運行的前提下,軸向旋轉補償器井口最大補償量為560 mm, 比萬向旋轉補償器增大了7.7%,說明軸向旋轉補償器能在更大的井口補償量下安全運行。
4 結論
4.1 分別采用管道單元和實體單元,建立了稠油井口地面管系和局部補償器的有限元模型,以整體管系的變形與強度條件和局部補償器的強度條件與密封性能,確定了稠油井口地面管系最大位移補償的判別條件。
4.2 以直管臂長度為變量對管系位移補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隨著直管臂的增長,井口補償量下降,當直管臂1、2 同時增長500 mm 時,井口補償量下降幅度達到了23.4%;隨著直管臂的縮短,井口補償量增大,當直管臂1、2 同時縮短500 mm 時,井口補償量上升幅度達到了117.7%。4.3 對比分析了不同局部旋轉補償器結構對于管系結構位移補償量的影響,計算結果表明軸向旋轉補償器和萬向旋轉補償器均能提供足夠的密封強度,但前者具有更大的位移補償量,相同管系結構下,其補償量可提高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