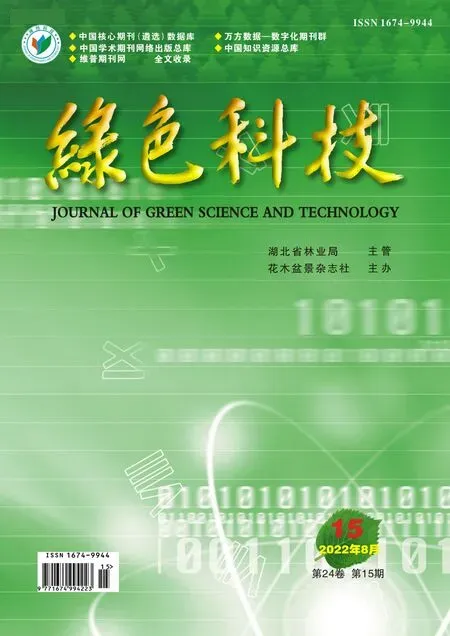營林發(fā)展策略對森林資源擾動的影響分析
馬 瑩
(曲靖市國有海寨林場,云南 曲靖 655000)
1 引言
林場林木是社會發(fā)展所需木材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時也是保護森林資源和穩(wěn)定地區(qū)生態(tài)平衡的重要措施。科學的營林發(fā)展策略可以提高森林體系結(jié)構(gòu)穩(wěn)定性,并最大化發(fā)揮林場的經(jīng)濟效益,但不同的營林發(fā)展策略會造成林場不同程度的擾動,進而影響林場森林體系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為此,本文將借助云南省曲靖市國有海寨林場的發(fā)展情況,對不同營林發(fā)展策略下的森林資源擾動變化進行探究,以期為相關(guān)人員或單位提供參考。
2 研究區(qū)概況
曲靖市國有海寨林場始建于1956年,地理位置位于云南省東部珠江源頭南盤江上游兩側(cè),即東經(jīng)103°42′~104°05′和北緯25°09′~25°43′。森林主要分布于麒麟和沾益2個高山臺地上,南北長59 km,東西寬37 km,海拔1919~2577 m,相對高差為658 m。年平均溫度14.5 ℃,年平均降水量1008.9 mm,年蒸發(fā)量為2140.3 mm;年平均日照時數(shù)2108.2 h。全場現(xiàn)有經(jīng)營面積26.5455萬畝,活立木蓄積達152.9萬m3,年生長量為4.6萬m3,森林覆蓋率達89.89%,林木綠化率達91.03%。根據(jù)《云南植被》分類系統(tǒng),該林場主要有暖性針葉林、半濕潤常綠闊葉林、落葉闊葉林和暖溫性稀樹灌木草叢等4種植被類型,主要群系有華山松林、云南松林、櫟類林和桉樹林等。
3 材料與方法
3.1 研究數(shù)據(jù)來源
以曲靖市國有海寨林場1995、2003、2014和2020年采用不同營林發(fā)展模式下森林演變記錄數(shù)據(jù)為例,并整合該林場1995~2020年間林場主要森林資源的樹種培育情況和木材利用情況的檔案資料。
3.2 研究方法
以曲靖市國有海寨林場建場時間為基礎(chǔ),結(jié)合我國森林分類經(jīng)營正式落實時間,選擇1995年作為對該林場研究的時間起點,將1995~2003年間該林場以生產(chǎn)木材為核心的營林發(fā)展模式計為模式1;將2004~2014年該林場以生態(tài)修復和建設(shè)為核心的營林發(fā)展模式計為模式2;將2015~2020年間該林場以保護森林為核心提供生態(tài)服務(wù)的營林發(fā)展模式計為模式3。從起止年間記錄的該林場二類調(diào)查數(shù)據(jù)中挑選出喬木林面積、森林覆蓋率、森林總蓄積量、造林樹種和生態(tài)功能等級變化等因子,作為評價不同模式下森林資源擾動情況的標準[1~4]。同時對各時期國有林場承擔的主要職能進行考慮,縱向比對分析上述3種營林發(fā)展模式下林場森林資源的數(shù)量、質(zhì)量以及生態(tài)景觀等因子的變化情況[5,6]。
3.3 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
用Excel 2021作為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分析對比的平臺,縱向?qū)Ρ攘怂?個年份下林場3個發(fā)展模式的森林資源擾動變化情況,以此分析出其變化規(guī)律[7,8]。
設(shè)該林場喬木林占地面積“Fi”,占比林場總面積“Di”的比值為“Yi”,則Yi的表達式為:
Yi=Fi/Di×100%
(1)
式(1)中:i表示第i年的調(diào)查記錄數(shù)據(jù)。設(shè)“Si”表示第年案例林場的單位森林面積,則森林覆蓋率“P”的表達式為:
P=Si/Di×100%
(2)
由公式(2)得到的P值只保留兩位有效小數(shù)。
本文中森林資源因子的增長率與下降率一般指本期調(diào)查值與上期調(diào)查值的增長量與減少量的比值,該計算方法可被應用到隨機時期與時期間相同內(nèi)容的對比當中。在判斷森林資源因子時,不同營林發(fā)展階段下林木的占比面積、覆蓋率、總蓄積量以及林木的單位面積蓄積量均可以通過公式(3)得出[9,10],即:
Cr(Rr)=(Ci-Bi/Bi-1)×100%
(3)
式(3)中:Cr表示增長率;Rr表示下降率;Ci表示本期的起始數(shù)據(jù);Bi-1表示時期上一時期的數(shù)據(jù)。
上述計算結(jié)果為正數(shù)則稱為增長率,若計算結(jié)果為負值則稱為下降率。
4 結(jié)果分析與建議
4.1 喬木林面積變化
結(jié)合案例林場3個不同營林發(fā)展模式下4個起止時間節(jié)點的林場二類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可知,案例林場的經(jīng)營面積始終處于動態(tài)變化。為便于比較分析現(xiàn)將3個模式下喬木林的各項數(shù)據(jù)匯總見表1所示。

表1 案例林場3個發(fā)展模式下主要時間節(jié)點的林木資源變化情況
由表1中數(shù)據(jù)可知,案例林場的喬木林占比面積從模式1實施起始年開始到模式3的終止期間漲幅17.01%,表明林場下喬木林營林情況總體呈上升趨勢。從各模式下不同時期的增長幅度變化角度來看,模式3期間的喬木林漲幅最大,為11.53%;而模式1和模式2期間的漲幅程度較小,分別為4.81和3.19。造成該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有:①因模式1與模式2下的林木采伐面積均小于實際造林的面積;②在1995年記錄的采伐跡地中有34.1%的土地荒山荒地工程轉(zhuǎn)變成喬木林地,在2013年轉(zhuǎn)為全額撥款事業(yè)單位后,案例林場開始停止林木主伐,重點對林分進行撫育;最后,在模式3下一些閑余空地、灌木林轉(zhuǎn)變成喬木林地[11]。
4.2 森林覆蓋率變化
由表1中數(shù)據(jù)可知,該林場的森林覆蓋率從模式1的起始年開始至模式3終止年間增長達到89.89%,林場森林面積總體呈上升趨勢。從漲幅角度來看,在模式3時期間林場森林的覆蓋率漲幅最大,漲幅可達12.01%,其次為模式1漲幅可達6.29%,模式2漲幅最小只有1.84%。造成該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與喬木林面積漲幅相似,但在模式2階段,因該林場進行營林轉(zhuǎn)型,需要增加用材樹種的采伐力度,并營造更具生態(tài)恢復能力的樹種,所以在模式2年間森林覆蓋率漲幅最低,各模式下的采伐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案例林場3種發(fā)展時期下采伐與資源培育的變化情況
4.3 森林總蓄積量變化
由表1中數(shù)據(jù)可知,案例林場的森林總蓄量整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發(fā)展趨勢。降幅程度最大年限為模式2期間,降低約43.44%,漲幅程度最大年限為模式3,增長達到119.02%。造成該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案例林場模式1和模式2均以木材收益為主生態(tài)建設(shè)為輔進行設(shè)計,實際林木的采伐量持續(xù)飄高,同時因模式1與模式2下的新栽林木樹齡較小,無法及時補充森林資源,進而會造成林場森林總蓄積量持續(xù)下降,直至模式3開始實行前達到極值點。在模式3下,因營林發(fā)展模式的主路線變更,導致采伐量急劇下降,同時模式1與模式2時期栽植的林木進入到中齡,從而形成林場森林總儲蓄量快速增加的態(tài)勢。
4.4 造林樹種變化
由案例林場3個模式階段造林樹種與林分情況可知,當林場的營林發(fā)展模式發(fā)生轉(zhuǎn)變之后,其林場的主要職能也會發(fā)生轉(zhuǎn)變,轉(zhuǎn)變的重點體現(xiàn)在森林資源培育的樹種與培育方式上。模式1下案例林場所種植的樹種多以杉、松、桉和相思為主,實際造林面積可達到846.6 hm2,占模式1總造林面積的87.64%,闊葉混交林的造林數(shù)量為24種,實際造林面積達到119.4,約占總造林面積的12.36%。模式2下案例林場營林模式以生態(tài)修復和建設(shè)為主,林場新育種的樹種多以生態(tài)功能較強的闊葉樹種為主,育種種類可達135種,實際造林面積約為1428.0 hm2,約占該時期總造林面積的97.1%。到模式3時期,案例林場種植的樹種替換為生態(tài)功能更加強大且兼顧商品價值的更高的土沉香、黃檀、閩楠以及格木等11種闊葉樹種,實際造林面積達到127.3 hm2。
4.5 生態(tài)功能等級變化
以林場下枯枝落葉層、林分林層、生物多樣性、植被蓋度和郁閉度等5個因子作為綜合評價指標,對3種營林發(fā)展模式終止年的森林生態(tài)功能等級進行分級。對3中營林模式的森林生態(tài)狀況進行評級,得分越高則證明林場森林生態(tài)功能越高,營林模式越符合自然生態(tài)規(guī)律,當評級中A、B級之和占比能夠超過60%,則可評價該模式的森林資源生態(tài)功能為優(yōu),詳細評價等級如表3所示。

表3 案例林場3個時期終止年主要森林生態(tài)資源的變化情況
由表3中數(shù)據(jù)可知,3個營林模式下終止年的生態(tài)功能評級得分以模式3最高,模式1次之,模式2最低。隨著營林發(fā)展模式的變更,該林場下A級生態(tài)功能的林分面積處于逐漸上升態(tài)勢,評分占比由11.36%增長至26.18%;B級生態(tài)功能下的林分面積占比情況呈先降后升態(tài)勢,最低值為32.43%,最高值達到66.25%;C級生態(tài)功能下的林分面積占比情況呈先升后降態(tài)勢,峰值出現(xiàn)在2014年,占比為33.53%,峰谷值出現(xiàn)在2020年,占比為5.64%;D級生態(tài)功能下的林分面積占比情況同樣呈先升后降態(tài)勢,峰值出現(xiàn)在2014年,占比為12.34%,峰谷值出現(xiàn)在2020年,占比為1.93%。由此可看出,不同營林發(fā)展模式對林場下森林資源的擾動存在影響,可通過科學的設(shè)計規(guī)劃降低擾動風險,提高森林資源整體結(jié)構(gòu)抗擾動強度[12]。
4.6 營林管理方式的建議
現(xiàn)階段我國國有林場的營林發(fā)展模式應當區(qū)別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發(fā)展方向,對林場的管理應當結(jié)合林木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實現(xiàn)科學化造林管理與采伐管理,在市場經(jīng)濟不斷變化和經(jīng)濟體制不斷完善的背景下,林場的經(jīng)營管理模式構(gòu)建應當做好轉(zhuǎn)變準備,在保障林場生態(tài)結(jié)構(gòu)穩(wěn)定的前提下,發(fā)揮林場種植林木的價值,例如林木本身的經(jīng)濟價值和碳匯價值[13~15]。現(xiàn)階段構(gòu)建新的營林發(fā)展體制時,應當明確犧牲森林資源換取經(jīng)濟行為產(chǎn)生的后果,通過不斷對生產(chǎn)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與林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的明晰優(yōu)化,讓林業(yè)能夠在未來的社會經(jīng)濟市場競爭中牢固自身市場地位,創(chuàng)新林業(yè)產(chǎn)業(yè)和管理方式,不斷激發(fā)出營林與造林生產(chǎn)工作者與管理者的主動性,以尋求更適合經(jīng)濟與生態(tài)并存的營林發(fā)展模式。
5 結(jié)語
本文借助云南省曲靖市國有海寨林場歷年發(fā)展數(shù)據(jù),對不同營林發(fā)展模式下森林資源擾動情況進行分析,明確不同時期不同營林方法對森林資源的影響情況。通過對3種模式下喬木林面積、森林覆蓋率、森林總蓄積量、造林樹種和生態(tài)功能等級變化等指標的分析,證實不同營林發(fā)展模式會對森林資源造成影響。上述分析中并未對如何建立評價體系和指標篩選進行研究,可在后續(xù)研究中給予完善,為其他森林資源管理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