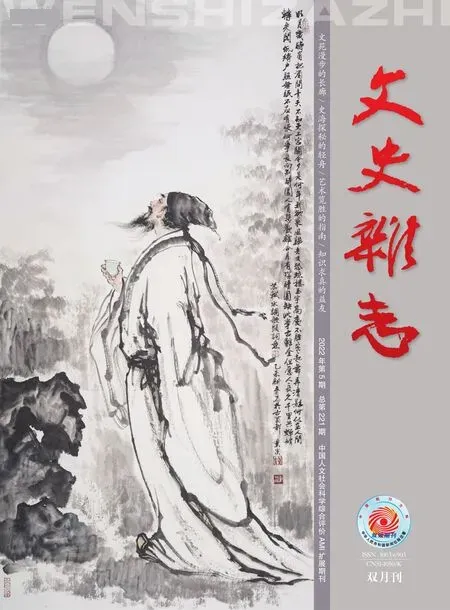從三國制式武器兼論《三國演義》劉關張兵器的文化重構
梅錚錚
漢魏三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亂世,這時期諸侯爭霸,群雄割據,各集團之間征戰討伐構成戰爭連綿不斷的時代特征。那么在冷兵器廣泛使用的當時,各諸侯軍隊的將士用什么兵器作戰?較之兩漢軍隊的制式兵器又有那些變化等細節問題,則往往被重要人物行為和重大事件所淹沒而被忽略。
矛、戟已成為當時軍隊的制式兵器
漢魏三國時代,車戰已然退出戰爭的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騎兵、步戰和舟船的作戰形式。加之冶鐵技術的長足進步,鐵質兵器被廣泛使用于戰場,從而改變了以往的戰爭形態。先秦時期最具殺傷力的重要兵器——戈,也隨之被淘汰出戰場;到漢末三國時期,幾乎絕跡實戰而進入儀仗衛隊的行列。翻檢與之歷史關聯密切的《三國志》《后漢書》等文獻,雖然不時還有使用戈的記載,但它更多的是作為戰爭和兵器的代名詞出現的。戈之退出戰爭主體乃歷史發展的必然,更是戰爭形態改變了作戰方式的需求。造成此原因的背景就是漢、匈之間經多年戰爭后,統治者清醒地認識到,組建強大的騎兵,使用更便于操控的兵器,才能提高殺敵效率,才是與草原民族交戰制勝的根本。像戈這種以割、啄方式殺敵的兵器顯然不能適應騎兵作戰的需要,于是使用以突刺殺敵的長矛、長戟,再輔之強弓、硬弩,遂成為漢匈戰爭中漢兵屢屢獲勝的重要作戰方式。當時裝備長矛、長戟的騎兵部隊,可以從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銅武士騎馬俑領略其風采。該墓發掘于20世紀60年代末,發掘者因未發現準確年號,故根據出土的各類器物將其斷代為“東漢(公元25—220年)晚期墓葬”,這其實表明發掘者更傾向于該墓葬為漢末三國時期。截至目前為止,像這樣大批成組、精致的銅質車馬俑在我國還是首次發現。其中持矛、戟、鉞等長兵器的武士俑達17個之多,實屬罕見。它們真實地反映了漢末三國時期軍隊武器裝備的具體形態。結合相關的歷史文獻得知,矛、戟已經成為當時軍隊的制式裝備而被普遍運用于戰爭中間。如在大眾熟知的三國名將中,善于持矛作戰的就有公孫瓚、張飛、趙云、典韋、程普、丁奉等。

圖一:兵器架中插兩支戟和一柄矛(選自《巴蜀漢代畫像集》)
除了矛外,戟也是騎兵、步兵常用的制式兵器。從考古資料得知,戟是一種由矛、戈組合而成的一種復合型兵器(圖一)。漢代劉熙解釋道:“戟,格也,旁有枝格也。”劉宋裴骃說得更明白:“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方上鉤曲也”。據文獻記載,早在春秋戰國、秦漢時期,戟一直是戰場上的主要兵器,它的出現最初是順應了車戰的需求;因為它同時具備矛的直刺和戈的砍、割、啄、鉤等多項攻擊性功能。必須強調的是,即使在車戰退出戰場的兩漢三國時期,它并沒有像戈那樣退出軍隊,反而表現出極強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漢末三國時期鐵質的戟替換了以往的青銅戟,前者比后者硬度更強,還能加長使用,戰斗力更加突出。文獻中這樣的實戰記載很多,如:張繡突然反叛偷襲曹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賊前后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余矛摧”,這即是借助了旁枝向上弧翹呈鉤刺之鐵戟來殺敵的突出戰例。它出現在文獻中往往用“大戟”“長戟”來描述。曹操高陵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銘文石牌即為明證。(圖二)另據《三國志·董卓傳附李傕、郭汜傳》裴注引《獻帝起居注》,李傕脅迫漢獻帝出宮,被郭汜率兵阻攔,“(李)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護衛。又如張遼和孫權在合肥大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沖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上述文獻所載“大戟”“長戟”均指插有長木柲的戟,這種戟對于步戰和騎戰都兼具防御和攻擊功能,為各個兵種所普遍使用。

圖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選自《曹操高陵》)

圖三:“七女復仇”圖中持手戟武士畫像石摹本(局部,選自《曹操高陵》)
此外,漢魏三國時期將士所用的戟還有長戟和手戟之分。區別在于長戟插有木柲,便于步戰和騎戰。手戟不插木柲,是隨身的便攜式兵器。目前所能見到手戟多集中于考古資料上,尤以山東、河南、江蘇地區出土的畫像石上圖像最豐富,河南安陽西高穴曹操高陵出土一塊“七女復仇”畫像石上有最直觀的式樣。(圖三)手戟攜帶使用方便,應是一種既能防身又能殺敵的兵器。手戟的使用屢見于當時文獻中,《三國志·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窬垣而出。”呂布給董卓當衛士,“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另,手戟因兩端有較長的戟刺和旁枝,所以還兼具佩劍斫的功能。《三國志·呂布傳附張邈傳》記載曹操攻擊呂布時,呂布讓陳登向徐州牧求救未果而非常憤怒,“拔戟斫幾”責問陳登。由此可知,手戟還能隨手投擲。手戟因不插木柲,形制短小,故方便將士隨身攜帶,且兼具斫、刺、投擲等多項功能,是以成為漢魏三國時期將士近戰搏殺的利器,當時最善于使用戟和手戟的要算曹操手下頭號猛將典韋。《三國志·典韋傳》不足九百字,而提到典韋使用戟與敵作戰竟有六次之多。其中記載曹操在濮陽偷襲呂布營寨,呂布親領援軍趕來,曹軍陷入困境。曹操急招募敢死隊員,典韋率先報名并臨危不懼沖在最前面,手下“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這算是手戟用于近戰殺敵的典型戰例。文獻中所提到的“韋手持十余戟”之戟就是手戟。該傳還特地強調:“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說明典韋所用的一雙手戟比平常人所用的形制要大,且重。晉朝張協曾寫過《手戟銘》曰:“錟錟雄戟,精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將。嚴鋒勁校,摛鍔耀芒。”銘中將手戟喻為可與越地生產的戟相媲美,是超過干將寶劍的鋼鐵雄戟。但到南北朝以后,戟和手戟退出主戰場,漸演為衛隊儀仗器物。
上引文獻已經充分證明,戟在實戰中是絕對銳利的殺敵兵器。但正如有矛就有與之相對的盾一樣,隨之就出現了與之相抗衡的另一種兵器——鉤鑲。劉熙《釋名》介紹說:“鉤鑲,兩頭曰鉤,中央曰鑲。或推鑲或鉤引,用之之宜也。”構造形制上,鉤鑲中間有一個像小盾一樣的鑲板,鑲板上有小刺,在兩端各伸出前端帶彎的長鉤。這種形制使鉤鑲集盾、鉤、刺等功能于一體,屬于一種組合型兵器,其實物在四川、江蘇等地出土數量不少。我們說鉤鑲是戟的克星,關鍵是它兩端的長鉤能有效制約長戟。《三國志·典韋傳》中記載曹操偷襲呂布兵營,很快呂布就親率兵反擊:“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十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在此,應注意的是典韋等應募勇士的作戰技術動作:“持長矛撩戟”。何謂“撩戟”?這就與戟的構造形制關聯密切。戟橫格有小枝,其形制因與漢字“卜”類似,故學者通常稱之為“卜”字形戟,故勇士們以矛撩橫格小枝以化解戟的威脅。但真正在實戰中撩戟以躲避被戟刺傷的最佳兵器,并非長矛而是鉤鑲。鉤鑲的實戰原理是用一頭長鉤卡住戟的小枝將其撩開,再借助鑲板上的小刺沖刺對手;或長鉤撩開長戟后,配合環手刀進行劈砍,這樣的戰術動作在畫像石上有清晰的圖像(圖四)。因此,鉤鑲兼具防御和攻擊功能,是針對長戟的克星兵器。魏文帝曹丕在他《典論·論文》中曾專門提到:“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其中“鑲楯”即鉤鑲和盾。令人不解的是,鉤鑲在當時運用非常廣泛,可是不論是文獻還是后代文學作品甚至連大名鼎鼎的《三國演義》,均未有關于在戰爭中使用鉤鑲的文字。這可能與它出現的時代比戟晚,又主要集中在漢魏三國時期有關系。到南北朝以后,戟逐漸退出戰場進入儀仗,成為軍隊的列戟制度;加之矛的應用更為廣泛,這便使鉤鑲失去存在的實用性。盡管如此,鑒于大量考古資料和出土實物的現身,我們不應當對鉤鑲曾在漢魏三國時期戰爭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視而不見,故記錄在此。

圖四:持鉤鑲和刀與持戟者格斗畫像(選自《綏德漢代畫像石》)
《三國演義》對兵器的文化重構
三國之后,有關的人物、故事等即以各種形式在世上廣泛傳播,成為中華歷史文化中最具影響力、最接地氣的傳統大眾文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后世大眾最初所接受三國文化的過程中,坊間說書、戲曲表演、平話小說這些載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傳播作用,尤以成書于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影響最大。《三國演義》將群雄爭霸、伐謀征戰的過程,運用文學手法演繹成波瀾壯闊的英雄創業史,從而達到三國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正因為其普及面廣,受眾者多,從而使英雄豪杰的故事膾炙人口;甚至于對他們使用的兵器,人們也是了如指掌,爛熟于胸。需要指出的是,《三國演義》雖對三國文化的傳播功不可沒,但極易造成讀者對歷史的誤解,亦如章學誠所言:“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至觀者往往為所惑亂。”章氏所謂讓觀者“所惑亂”的地方,不外是指歷史真相和歷史常識這兩方面。畢竟文學不是史學,故事也非歷史,生花妙筆下故事情節僅僅是借用了歷史的外衣表達了創作者的思想傾向和對歷史文化的認知。過去的時期,由史學到文學之間的演變研究,前輩學者成果累累,洋洋大觀,論述精到。是故,這里不再從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異化去考證,乃另辟蹊徑,以文獻和考古資料為基礎,僅從漢魏三國制式兵器的變化,就《三國演義》中大眾耳熟能詳的劉關張兵器,予以文化解讀,或能原歷史的本真。
《三國演義》第一回劉備率眾起兵,“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給讀者造成劉備是揮舞雙股劍上陣的最初印象,然此實在是后人不了解歷史常識所造成的“惑亂”。中華歷史的發展進程告訴我們,劍作為兵器出現時代的確很早,民間尚有蚩尤造劍的傳說。拋開神話的內容從考古學獲知,至商以后青銅劍已成為戰場上的主要兵器。從考古資料得知,早期的劍長不過尺余,如巴蜀地區的柳葉劍,長安張家坡、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劍。很明顯,這些劍防身功能強于實戰。真正用于實戰的劍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長度逐漸加長,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其長度就有55.7厘米了。
到秦漢以降,劍在形制和材質上均發生了很大變化,表現在鋼鐵劍替代青銅劍,而且長度明顯較過去加長了。考古資料顯示漢代鐵劍的長度通常達到90厘米以上,比如滿城劉勝漢墓中的鋼劍長度達104.8~111.3厘米;洛陽燒溝漢墓出土鐵劍長度也達51.5~117.8厘米;重慶奉節趙家灣墓地出土鐵劍竟有127.2厘米長。漢代鐵劍較過去長度加長的原因,都是為增強殺敵的功效。但劍因本身形制輕薄,故砍殺威力小,作為短兵器在實戰中是不占優勢的,是以漢魏時期環手刀逐步取代鐵劍成為軍隊實戰制式兵器。再者,按照一般使用規律來說,所有兵器只要長度在70厘米以上,單手幾乎很難掌握了,這就是我們看到出土的漢代鐵劍劍柄都較長,此是利于雙手持握而刻意為之的。但隨之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就是雙手持握特別不利于騎兵作戰。因為在三國時期馬鐙尚未出現,那么將士騎馬時必須用一只手緊握韁繩來調控身體重心,另一只手才能揮舞兵器,這對于農耕民族的人而言難度技術極高;尤其是面對手持長兵器的對手,雙手握短兵器的人肯定不占便宜。戰場上講究“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分險”。作為戎馬半生,身經百戰的劉備,不會不懂得這最普通的戰場常識。由此可以推斷出,真實的劉備決無可能舞雙股劍騎馬上陣,一定另有長兵器,只是史料未曾明確而已。
文獻既未記載劉備使用何種兵器,這便給后代留下了很大想象的空間。填補這一空白的不是文獻和考古資料,而是具有強大想象力的民間文化。從元代開始,說書藝人講三國故事介紹劉備時就說:“為首將是前部先鋒劉備,手提雙股劍”,這應是至今所見最早說劉備手持雙股劍的文學作品。這樣的誤導也就將劉備的兵器定型化,并影響到后來所有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以及世人心理期盼。問題的關鍵點是,后人為何要將劉備所用兵器表述成雙股劍呢?這大概只能從文化上去追溯其淵源了。個人認為恐與漢高祖當初起兵有關。《史記·高祖本紀》就編造過劉邦“拔劍擊斬蛇”,起兵造反的神話。從此劍被賦予了神化的色彩,成為古代帝王將相文化中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兵器。譬如劉邦戰勝項羽建立大漢王朝后獎賞功臣,特批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此后,但凡對朝廷有功者或某些權臣都能享受如此特殊待遇。《晉書》記載:“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后惟朝帶劍。”漢代以后,男子佩劍不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特權的象征,比如董卓、曹操等。因此,自稱“漢室宗親”的劉備經艱苦創業,而終成劉漢天下的繼承者,成為蜀漢開國之君,他當然要有與眾不同的兵器。這么說他手持雙股劍上陣不僅在情理之中,也是對漢室正統的繼承之表達。
《三國志·張飛傳》記載:劉備兵敗長坂被曹軍追擊,緊迫之間“(張)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據此可知,張飛常用兵器是矛,在元代說書藝人的底本中表述為:張飛“用丈八長槍撮梢兒把定輪轉動,眾軍不能向前”,又說他“手持丈八神矛”,明確了他的兵器矛(槍)外,還強調其長度為“丈八”,《三國演義》更直接說成“丈八蛇矛”。前文已述矛為當時軍隊制式裝備,很多將領都善用長矛。那么后代作品何以要強調張飛使用的是“丈八蛇矛”?考古資料表明,漢代的鐵矛都很長,劉備的祖先河北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鐵矛總長為1.96米;洛陽燒溝漢墓的鐵矛頭就有47厘米長,“從鐓的末端開始計算量至矛頭尖端其長度為250厘米”,即總長竟達2.5米。據考古資料表明,三國時期1尺合今約24厘米左右,“丈八蛇矛”就是長4.32米的矛。但當時這樣的長矛并不稱矛而是叫矟。《釋名》:“矛長八尺曰矟,馬上所持。”很顯然,它的正式名稱應該稱“馬矟”,是當時軍隊的制式兵器。《三國志·張飛傳》只說了張飛“瞋目橫矛”,并沒有明確矛的長度是多少,顯然此矛就是一般的長矛而非馬矟。但稍后,矟與矛在名稱上被混淆了,《晉書·劉曜載記》記載:前趙大將陳安與劉曜手下將軍平先、丘中伯格斗時“(陳)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將馬矟說成丈八蛇矛,可能是矟音shuò,讀若“槊”,有時也寫成“槊”,垣榮祖就有“昔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之說。因矟與蛇音近,加之將士上陣揮舞姿態動作猶如長蛇般靈動,故當時歌曰:“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后人不知,故將丈八之矟詐稱成了“丈八蛇矛”。由此可見,《三國演義》稱張飛兵器為“丈八蛇矛”并非是三國時代的標準稱謂,而是采用晉以后的說法。后代作品若依時代準確名稱稱“矟”,則顯得較為生僻,改稱“丈八蛇矛”不僅與“豹頭環眼”的張飛相配,還彰顯出濃厚的文學色彩,更直觀且貼近大眾。至于說到清代以來的《三國演義》各種版本出現張飛畫像時,更刻意將其矟的矛頭畫成雙刃帶曲線若蛇一般,那就距歷史真實更遠了。
自羅貫中《三國演義》問世后,書中“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涂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的關羽形象令人印象深刻。除去“紅臉”“美髯”這與眾不同的相貌外,所使用的青龍偃月刀,更是他馳騁沙場威風八面的“標配”兵器。關羽用此斬顏良、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水淹七軍……造就他威震華夏、武功蓋世的“戰神”形象,令后人頂禮膜拜,崇拜無比,給推上了“關帝”“武圣人”的神位。
關羽使用何種兵器?史無明載。傅惜華先生《元代雜劇全目》中收錄有關漢卿《關大王單刀赴會》和無名氏《關云長單刀劈四寇》的劇目。元代說書藝人講述三國故事也說:“林中走出一隊軍來,約一千人,立馬橫刀。張表急問:‘來者是誰?’‘我是漢先鋒手下一卒,關某字云長。’”表明至遲在元代人的眼中,關羽是提刀上陣的。到《三國演義》中更藝術化地寫道:“云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艷鋸’,重八十二斤”。從此關羽使用青龍偃月刀被定型化、典型化,關云長單刀赴會的情節也屢見諸各類文學藝術作品中,成為膾炙人口的故事而流傳廣泛,影響深遠。
后代文藝作品之所以將刀認定為關羽兵器,可能源自三國史上孫、劉兩家的一次談判。《三國志·魯肅傳》記載,劉備占據益州后,先前為對抗曹操而結成的同盟已貌合神離,兩家在荊州諸郡的歸屬等問題凸顯出來。為解決矛盾,“(魯)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需明確的是,文獻中的“單刀俱會”,是指參與談判的將軍帶著自己佩刀在約定地點會談,既是和平談判則無需拿上陣的長兵器。可惜后人不加詳查,誤將隨身佩刀當長刀。這種謬解流傳開來,就造成關羽帶著自己的長刀去和魯肅談判的錯誤印象。
詳考漢魏三國時期的文獻,結合考古資料獲知,那時刀大致分為無木柲和帶木柲的兩種,前者如環手刀。環手刀在西漢就出現了,漢魏三國已是將士的制式兵器和基本裝備,有大量考古實物出土為證,但這屬于短兵器。而后者因帶有長木柲,通常被稱為“長刀”或“大刀”。帶木柲的刀何時出現今不可考,至遲漢魏三國就有。《三國志·典韋傳》說:“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上引《晉書·劉曜載記》亦有“七尺大刀”的記載。雖然文獻記載言之鑿鑿,但至今尚未有考古實物出現。那么關羽上陣所用的是否是這種長刀呢?《三國志·關羽傳》中有“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的記錄。據此,學者推測關羽的兵器應是長矛或長戟類的刺兵。依據是,古人用詞嚴謹,若關羽使刀,其相應的詞當用“砍”“劈”這類從上往下或橫向動作的詞,不應用“刺”這種表示直、沖的動詞。然而專家的合理推論卻被強大而有深厚大眾基礎的傳播文化所淹沒,因為根深蒂固的民間文化早已為他重構或叫“定制”了一把帶美學意味的“青龍偃月刀”。
結語
文獻、考古資料為探討漢魏三國軍隊制式兵器,提供了最堅實的歷史實證。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三國演義》中人們熟知的劉、關、張的兵器,實是經過了后代于文化上的重構。文學作品虛構故事情節無可非議,但表現在劉、關、張所用兵器這樣的細節上,這虛構就是別具深意且經過精心安排而帶有很強的思想傾向了。其用意首先是強調蜀漢的“正統”,貫徹作品尊劉貶曹的宗旨;其二是強調典型人物的典型性兵器:劉備的雙股劍意在突出漢室宗親的“唯一”;張飛的丈八蛇矛,乃為強調他于萬軍中斬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的“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的勇猛;關羽的青龍偃月刀這種特種兵器與“面如重棗”、赤兔馬、綠色戰袍等元素共同組合,則精心塑造出忠義千秋、威震華夏的三國戰神的偉岸形象。
從漢魏三國時期軍隊制式兵器到文化重構的兵器,我們發現歷史的真相往往是有意被模糊。因為真相在流傳的過程中,始終被文化的面紗所籠罩;因為它源于民間,深刻著民族的靈魂,故而有著頑強的生命力而被后人所認同。馬未都說過一句經典的話:“歷史沒有真相,只殘留一個道理。”這,正為本文作了最好的詮釋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