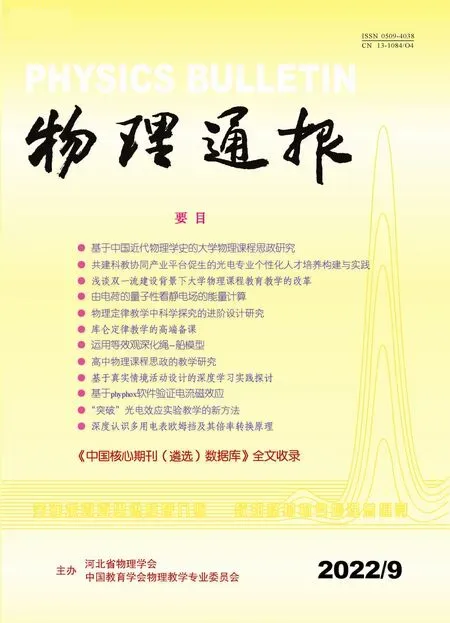基于中國近代物理學史的大學物理課程思政研究
張夢月 李 政
(文華學院基礎學部 湖北 武漢 430070)
2016年12月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主席講到:“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1]教育部在2020年5月28日印發了《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簡稱《綱要》),為各大高校進行思政教育、立德樹人提供了關鍵性的引領作用.由此可見,課程思政將成為高等教育的長期性和關鍵性工作.
《綱要》中講:“以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愛人民、愛集體主義為主線,進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2]那么中國物理學史便具有天然的優勢.中國物理學史融合了科學與人文,打破了傳統大學物理課堂的“文理壁壘”:中國物理學史建立的過程及其涉及到的愛國物理學家,可以發揮課堂的人文價值,根植學生的愛國主義;而各個物理學家所攻堅的科研領域又呼應了大學物理中的知識點.因此將中國物理學史融入到大學物理的課堂,對學生的思想引領和價值引領至關重要.
1 回國拓荒 躬耕基礎教育
1.1 人物介紹
第一批回國拓荒的物理學家介紹如表1所示(按照回國先后順序排列).

表1 第一批回國拓荒的物理學家
1.2 回望歷史
20世紀20年代,這些留歐美后回國的物理學者,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物理學機構,并以自己的機構為主陣地開啟了中國最早的物理學本科教育,在中國本土進行了最早的物理學探索,如夏元瑮在北大開啟物理學本科教育,饒毓泰在南開創立物理系,胡剛復在南京高師創立物理系.
1.3 思政育人切入點
第一批回國拓荒的代表人物蘊含的思政育人切入點如表2所示.

表2 第一批代表人物蘊含的思政育人要素
1.4 教學策略
創建歷史情境,從學生已知的歷史知識為出發點,遵循“有因有果”的原則,切勿為了彰顯教師的博聞強識,對歷史“張口就來”,最后導致“教師不知道在說什么,學生不知道教師在講什么”的結局.將歷史情境放在正課后,學生深入地理解知識點后,才能意識到先驅者所做事情的重要性、艱巨性.
在講完X射線的衍射后,可向學生提問:“中國第一位對X射線有突出貢獻的學者是誰?”從而回望歷史:胡剛復是1909年首批被錄取的庚款留美學生.進而講解胡剛復師從杜安教授測量X射線,同年進入哈佛大學師從杜安教授專攻X射線光譜方面的研究,他利用測定普朗克常量h的X射線分光計,和由高壓蓄電池組的電流激發Coolidge管產生穩定的X射線源,精確地測定了金屬物質的臨界吸收頻率、臨界電離頻率,以及與X射線有關的最高特征輻射頻率.1918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先后在12所大學擔任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為中國培養了多位物理大家,如吳有訓、施汝為、何增祿等.
在學完普朗克假設、黑體輻射公式后告訴學生,近代的一位中國物理學者也為量子物理做出了貢獻,為中國人爭了光,他就是葉企孫.1912年民國成立,庚款計劃繼續進行,葉企孫就在1918年考取庚款赴美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就讀,專攻普朗克常量和磁導率的研究,并利用X射線連續譜短波限法測量了普朗克常量.
X射線連續譜存在一個最小波長λmin,稱為量子極限,其數值只依賴于外加電壓V,如果一個電子場中獲得的動能Ek=1 eV,當其到達靶子能量會全部轉化成輻射能,由此產生的最大能量顯然是
那么

葉企孫和帕爾默(H.hpalmer)在教授杜安(W.Duane)的指導下,采用方解石晶體,提高X射線強度,用了較窄的狹縫(λmin的測量誤差小),從而大大提高了測量精度,他們測量的普朗克常量
?=(6.556±0.009)×10-34J·s
此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16年之久.
葉企孫同時是一位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科學家,在抗日戰爭中,他和他的學生也為抗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和犧牲.1937葉企孫及其學生在天津從事抗日活動,組織地下軍火工廠,為冀中游擊區制造炸藥和地雷,給抗日根據地裝配和輸送無線電收發報機.他的學生熊大縝為根據地制造了大批量地雷、手榴彈、復裝子彈、擲彈筒彈,受到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的多次嘉獎.
2 播撒種子 筑牢物理根基
2.1 人物介紹
第二批回國進入各高校任教的物理學家介紹如表3所示(按照回國先后順序排列).

表3 第二批回國進入各高校任教的物理學家
2.2 回望歷史
在1924至抗戰期間回國的這批學者,進入了第一批回國者創辦的物理研究機構,壯大了師資力量,開展了物理學的本科、研究生教育,依托各大高校將物理學的種子灑在了中國大地.并且國內的物理教育、科研機構也有所發展,中國物理學科的百年基業已初步奠定[3].
2.3 思政切入點
第二批回國的代表人物蘊含的思政育人切入點如表4所示.

表4 第二批代表人物蘊含的思政育人要素
2.4 教學策略
康普頓效應指在散射X射線中除有與入射波長相同的射線外,還有波長比入射波長更長的射線,叫做康普頓效應,康普頓因此獲得了1927年諾獎.實際上康普頓在1923年5月發表的關于康普頓效應的文章并沒有受到物理學界的廣泛支持和認可,因為他只用到了一種散射物質:碳,缺乏普適的實驗證明.吳有訓在康普頓的指導下,歷時7個月,獲得了15種元素所散射出來的X射線光譜圖.后康普頓將吳有訓的散射圖和自己石墨散射的X射線光譜圖并列,作為證實自己理論的重要依據,于1924年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國際物理學術大會上宣讀了他和吳有訓聯名撰寫的論文《被輕元素散射時鉬Kα線的波長》,康普頓這才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認可.以至后來的很長時間,一些國家依然把康普頓效應寫成“康普頓-吳有訓”效應,以此紀念吳有訓為“康普頓效應”所做出的貢獻[4].
在粒子物理章節或者在物理前沿課程,亦或是“測量物質吸收系數”的大學物理實驗課程中,可向學生介紹中國近代物理奠基人:趙忠堯.
趙忠堯1927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師從諾獎得主密立根.在密立根給的課題“硬γ射線通過物質時的吸收系數”中,通過實驗發現硬γ射線通過硬元素測出來的吸收系數比通過輕元素測出來的吸收系數高出40%,大量能量不翼而飛.為了研究能量去哪里了,趙忠堯經過大量實驗,觀測到硬γ射線在轟擊重元素時會產生一對正負電子對,而這對電子對在被激發后會立即湮滅.可以說趙忠堯是發現反物質并且觀測到正反物質湮滅現象的世界第一人.但由于當時物理學界沒人相信電子可以帶正電,連密立根也不相信并扣下了他的實驗論文.直到1937年作為趙忠堯的同班同學,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因為正電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83年安德森承認,正是因為趙忠堯的啟發,他才在1932年用云霧室測出了正電子的軌跡[5].
3 生根發芽 造就百年基業
3.1 涉及人物
中國物理學會成立后及抗戰期間高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如表5所示.

表5 中國物理學會成后及抗戰期間高校培養出來的學生

續表5
3.2 回望歷史
經過表1和表3中的兩批物理學者開拓荒林,近代中國已經逐步培養一批畢業生,他們恰恰也是近代物理乃至新中國成立后各個物理分支專業中的先驅人物.
3.3 思政切入點
近代中國培養出的一批物理專業先驅人物代表蘊含的思政育人切入點如表6所示.

表6 近代中國培養出的第一批物理專業先驅人物思政育人要素
3.4 教學策略
在普通物理的“等離子體與受控核聚變”章節,教師會給學生介紹前沿物理:受控核聚變的展望.我們知道要使核聚合在一起,就必須具備很高的能量克服庫侖斥力的作用,等離子體由于自身的優勢是核聚變的首選反應物,但實現高溫、高密度的等離子體,并將其長時間約束在一起并非易事.激光慣性約束便是一種方法,而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這種方法的創始人,便是我國物理學家王淦昌.
王淦昌畢業于清華,留學于德國,任教于西南聯大.新中國成立后,被秘密受命參與到原子彈的研制工作中,隱姓埋名17年.原子彈研制成功后,王淦昌在1978年后開展強流電子束慣性約束核聚變和氟化氪(KrF)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基礎性研究工作,為后來的慣性約束聚變獲取核能做出了開創性工作,而這一研究項目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題,被列入了國家“863”計劃.王淦昌3次與諾獎擦肩而過,本可以在國外潛心研究學術獲得至高榮譽,但他卻說:“我的祖國正在遭受苦難,我要回到祖國為她服務.”
4 結束語
一路走來,篳路藍縷.一代代中國物理學家為了科技報國,嘔心瀝血,為了科技強國,鞠躬盡瘁.將這一艱辛的過程作為大學物理課程思政的資源及教學策略,可以堅定學生愛國、愛黨、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決心,可以植根學生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祖國的責任感.其次,現代物理學家和現代中國物理發展的現狀也具有挖掘的意義,如薛其坤院士及其團隊發現的量子反常霍爾效應、華中科技大學教授羅俊測量的萬有引力常量G.總之,講好中國故事,培養學生愛國主義,堅定四個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