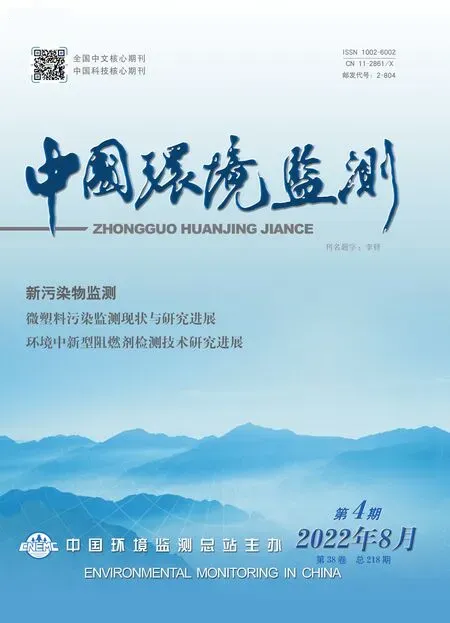北京城市副中心典型海綿體地表水與地下水交互作用研究
姜 媛,李海軍,任永強,楊 慶
1.北京市地質礦產勘查院,北京 100195 2.北京市地質環境監測所,北京 100195
海綿城市(Sponge City)也被叫做“水彈性城市”,其概念中的“海綿”表征的是城市帶有的吸附功能[1-5]。海綿城市建設是通過運用低影響開發(Low-Impact Development,LID)的理念及措施,對雨水進行回收利用,以改變降水地表徑流特征的方式,來達到緩解城市內澇、補給地下水資源及保護地表水源等的目的[6-7]。
隨著我國海綿城市建設工作的推進,到目前為止,國內已有海綿試點城市30個,海綿城市建設區域超過600 km2。現有海綿城市建設仍處于前期發展階段,在海綿城市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方面還有許多不足。總體來說,對于海綿城市這一熱點問題,國內外學者大多從LID設施本身的結構、作用機制、對徑流量的影響及模型模擬的角度開展研究,而對海綿城市建設對地下水水位和水質的影響卻少有研究[8-13]。在海綿城市建設過程中,城市雨水和再生水中可能包含復雜多樣的污染物成分,若這些成分通過海綿體進入地下水,勢必會給地下水帶來潛在的污染風險,對城市水資源造成很大的破壞[14-16]。因此,需要加深海綿城市建設對地下水的影響研究。
在海綿城市的建設過程中,如果把整個城市當作一個可以吸水、蓄水、釋水的“海綿”,從生態要素的角度出發構建一個生態整體,那么城市中建設的LID設施依據其本身的工程設計構造,以及與地表、土壤的接觸關系,可以分成點要素、線要素及面要素3個層次。點要素是海綿城市中分散布局的海綿要素,其鑲嵌在城市的建筑設施當中,如研究區域內的綠色屋頂、蓄水池、濕地斑塊等可產生局部效果的LID設施;線要素是海綿城市的水資源線性聯系通道,如研究區域內的水系、植被緩沖帶、植草溝等海綿要素;面要素則是海綿城市中的大型面狀海綿要素,如研究區域內的濕地、調節塘、下沉式綠地等[17]。
根據北京市通州區海綿城市建設相關規劃,選擇后北營海綿小區(點狀海綿體)、蕭太后河花莊段(線狀海綿體)、北運河上游濕地生態區(面狀海綿體)為研究對象,研究不同海綿體中地表水與地下水的交互作用。
1 采樣和分析
1.1 采樣點布設
1.1.1 點要素海綿體
通州區后北營安置房小區為通州區海綿型小區的建設試點,小區內建設有透水瀝青路面、蓄水池、植被緩沖帶等LID設施。本次研究選擇該小區作為典型點狀海綿體,在其內部的集水綠地中,沿地下水徑流方向和垂直徑流方向布置了5組監測孔(圖1)。監測孔采用一孔三井的布設方法,即每組監測孔均有孔深分別為10、20、30 m的3眼監測井,共15眼監測井。

圖1 后北營點狀海綿體監測孔布置平面圖Fig.1 The monitoring wells ofpoint sponge in Houbeiying
1.1.2 線要素海綿體
以蕭太后河花莊段的自然修復帶作為線狀海綿體的典型代表,按照與地下水流向一致的方向布設了一排共6組分層監測孔,監測孔之間以10 m為間隔(圖2)。監測孔采用一孔三井的布設方法,即每組監測孔均有孔深分別為10、20、30 m的3眼監測井,共18眼監測井。

圖2 蕭太后河線狀海綿體監測孔布置平面圖Fig.2 The monitoring wells of line spongein the Xiaotaihou River
1.1.3 面要素海綿體
選取北運河甘棠大橋附近的北運河濕地生態區作為面狀海綿體的典型代表,按照與地下水流向一致的方向布設了17組監測孔(圖3)。其中,A、B、C組均包含孔深10、20、30 m的3層監測井,D組為孔深50 m的單層監測井,E組為孔深50、80 m的2層監測井。

圖3 甘棠面狀海綿體監測孔布置平面圖Fig.3 The monitoring wells of plane sponge in Gantang bridge
1.2 采樣
2018年5—9月,每月分別對上述監測井及北運河河水進行一次取樣測試。其中:5月降雨較少,對應枯水期水樣;6—9月為雨季,對應豐水期水樣。最終共計采集到330組地下水樣品和15組地表水樣品。
1.3 分析測試

2 結果和討論
2.1 典型海綿體地下水水化學特征
典型海綿體區域地表水及地下水主要化學成分分析測試結果見表1。

表1 典型海綿體區域地表水及地下水主要化學成分
對表1中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作Piper三線圖。從圖4可見,點狀海綿體地表水的水化學類型以HCO3-Na型為主,線狀海綿體地表水的水化學類型以HCO3-Na型和HCO3-Ca型為主,面狀海綿體地表水的水化學類型以HCO3-Na型和HCO3-Na·Ca型為主。


圖4 典型海綿體Piper三線圖Fig.4 Piper maps of typical sponges


2.2 典型海綿體地下水水化學特征形成機制分析
地下水水化學特征的形成受多種因素控制,如含水層的地理位置、基巖、礦物組成和氣候情況等。從圖5可見,各典型海綿體區域地下水采樣點主要分布于巖石風化作用機制帶,表明研究區域地下水的水化學成分主要受到巖石風化作用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蒸發作用和降水作用的影響。其中:面狀海綿體埋深10 m和20 m含水層受蒸發作用影響的程度高于其他含水層,主要是由于其地下水位多年平均埋深分別僅為3.13 m和3.36 m;點狀和線狀海綿體地下水位多年平均埋深均大于10 m,含水層受蒸發作用影響較小。在各典型海綿體陽離子[Na+/(Na++Ca2+)]圖中,部分采樣點在Gibbs范圍外。結合陰陽離子間的比例系數可知,其含水層發生了陽離子交替吸附,說明存在外界輸入補給。


圖5 典型海綿體區域地下水Gibbs圖Fig.5 Gibbs maps of groundwaterin typical sponge regions
2.3 典型海綿體地表水與地下水相互關系分析
圖6顯示,面狀海綿體樣品中,埋深10 m和20 m含水層地下水折線的變化趨勢與地表水折線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地下水的Na+濃度低于地表水,主要是由于地表水在入滲過程中發生了陽離子交替作用的逆反應,Na+被吸附,含水層介質中的Ca2+被交換出來。含水層水位差在0.2 m以內,說明這兩個含水層的水力聯系極為密切,并且補給來源與地表水密切相關。埋深30 m含水層折線的變化趨勢與埋深10 m和20 m含水層相似,說明埋深30 m含水層受到地表水自上而下的補給。埋深50 m和80 m含水層折線的變化趨勢與地表水不一致,說明這兩個含水層與地表水及上部含水層的水力聯系微弱。

圖6 面狀海綿體Schoeller圖Fig.6 Schoeller maps of groundwaterin typical sponges
2.4 典型海綿體地表水對地下水影響距離分析
從各期監測數據的Piper圖可得出,取樣點距離河岸越遠,其水化學成分與地表水就相差越大,其中,Cl-濃度差異最大。在自然界中,Cl-不易與其他組分結合,是一種穩定的水化學離子。因此,選擇Cl-為指示因子,根據其濃度在水平方向上的變化,判定地表水對地下水的影響范圍。
以Cl-濃度曲線圖中變化趨勢最大的點為分界線,擬合兩側各點的趨勢線,將兩條趨勢線的交叉點定為地表水對地下水的大致影響距離。趨勢線的可靠性可通過R2來確定。R2位于0到1之間,越接近1說明趨勢線越可靠。
由圖7可見,線狀海綿體埋深10、20、30 m含水層的Cl-濃度均表現為由近河端向遠河端逐漸降低,且最大拐點都出現在TZM-60號井。以埋深10 m含水層為例,擬合其近河端一側及遠河端一側的Cl-濃度回歸趨勢線,根據交叉點的位置,判定蕭太后河對線狀海綿體地下水的影響距離在90 m左右。同理可知,北運河對面狀海綿體埋深10 m和20 m含水層地下水的影響距離為100 m左右,對埋深30 m含水層地下水的影響距離為80 m左右。

圖7 研究區監測井分組氯離子濃度曲線圖Fig.7 Chloride concentration curve of monitoring wells in study area
3 結論
海綿城市建設作為系統解決城市水安全、水資源、水環境問題的有效措施之一,已成為實現生態低碳城市建設的重要途徑。但伴隨著地表水及雨水的下滲,城市徑流中的污染物會通過海綿體進入地下水,給地下水帶來污染風險。
從影響深度上看,典型海綿體地下水受大氣降水影響明顯。其中,埋深10 m和20 m含水層地下水與地表水聯系密切,埋深30 m含水層地下水與地表水聯系較弱,埋深50 m和80 m含水層與上部含水層無明顯水力聯系。從影響范圍上看,線狀及面狀海綿體地表水對地下水的影響距離為80~100 m。隨著含水層埋深的增加,地表水對地下水的影響程度減弱。
綜上,北京城市副中心線狀及面狀海綿體埋深10 m和20 m含水層地下水受外界影響顯著,因此,當存在地表污染源或地表水水質較差時,應予以重點關注。埋深50 m和80 m含水層地下水雖然受外界影響較小,但依然存在被污染的可能性。建議在城市副中心海綿城市后續建設過程中,對該區域地下水進行長期監控,同時加強對海綿體周邊污染源的治理,并盡可能多地建設雨水自然凈化設施,以減少海綿城市建設對地下水可能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