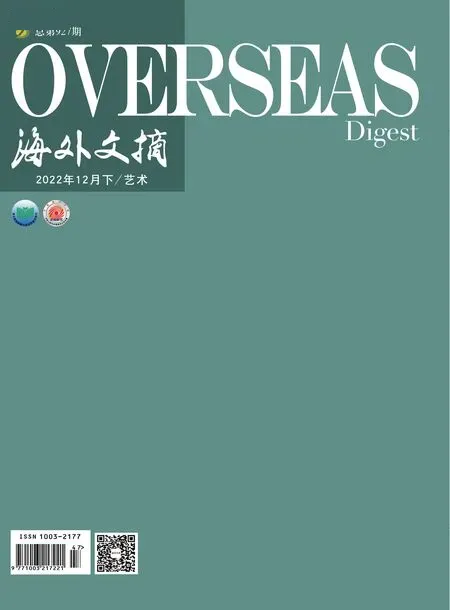羅萬藻生卒年辨析及其文學思想初析
□何映芳/文
羅萬藻,明末有名的古文家,與艾南英、陳際泰、章世純結“豫章社”,大力改革八股文,有“陳艾章羅,天下制藝”的美譽,稱“臨川四大家”,又稱“江右四家”,其文有“清微澹遠如疏雨微云”。本文從其個人大致生平經歷對生卒年進行辨析,并對其時文創作、詩歌創作方面的思想進行提煉,初析其文學思想,以期對羅萬藻有個一初步全面的認識。
羅萬藻,字文止,江西撫州臨川人,明末古文家。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胸懷大志,十三歲時就博通經史,但他父母因其體弱多疾,沒有讓他過早參加科舉,十九歲才成為郡弟子員,后被督學駱臺晉、蔡云怡首推拔貢,名聲大噪。當時文壇風氣腐庸,他立志興振文風,與艾南英、陳際泰、章世純結“豫章社”,大力改革八股文,“天下翕然宗之”,稱“臨川四大家”,又稱“臨川四才子”。天啟七年(1627),鄉試中舉,多次進京應試不中,令人扼腕。1636年,崇禎皇帝讓大臣們舉薦賢良之人,祭酒倪元璐非常賞識羅萬藻的才華,首推保舉他入仕,但他無意官場,應詔不赴。后來,他感念國家戰亂、內憂外患,棄筆從戎,應詔任福建上杭知縣,操練鄉兵,制定城防之策,圍剿招撫山賊,受百姓愛戴。1645年,提拔為禮部祠祭司主事。1646年,摯友艾南英去世,他悲痛不已,“哭之而為之殯殮”,數月后也病逝了。有識者謂:“公才可以元,而當文體破壞之余;度可以相,而際時事倥傯之日。其謀猷,人告可以坐平大難致太平,而厄于遇合咸用為公惜焉。[1]”
1 羅萬藻生卒年辨析
關于羅萬藻生年,大部分地方標注的是不詳,卒年1647年;在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中,羅萬藻生卒年為1583—1646年。經筆者翻閱古籍,在《四庫全書》收錄的羅萬藻《此觀堂集》中,卷首有金溪吳堂為羅萬藻撰寫的《羅艮庵先生本傳》,文中有言“崇禎丙子,上命諸大臣舉賢良方正士,鴻寶倪公首以公名,應詔不赴。[1]”崇禎丙子年即1636年,祭酒倪元璐保舉羅萬藻入朝為官,羅萬藻婉拒未去。后“又八年,始從考選,受上杭令,時年已六十四矣。[1]”意思就是說“過了八年,羅萬藻經過考選,任命為上杭知縣,這時他已經64歲了。”古人一般年歲按虛歲計算,1644年羅萬藻已經64歲了,以此可推,羅萬藻生年應為1581年。
關于卒年,主要爭議在于1646年或1647年。《羅艮庵先生本傳》記載:“及千子作于延平,哭之而為之殯殮。因思千子夢中句隱寓清江山讖也。公亦用是傷感,乃自號‘艮庵’,蓋時止焉,而無意于人間也矣。是歲負病,不踰月而逝。[1]”“千子”即羅萬藻好友艾南英,史載艾南英逝世于1646年8月[2]。羅萬藻因艾南英之死傷感亦無意于人間,當年就抱病,不到一個月就去世了,那么羅萬藻就是跟艾南英同年即1646年去世,文末的“卒年六十有六”也印證了這個觀點。那為何很多地方用1647年呢?陳際泰第三子陳孝逸在其《癡山集》卷二《羅文止先生小千園集序》中寫道“‘昭武四先生’,獨祠部游道山最后。丙戌冬,接祠部急問。孝逸走索其家,得遺集若干篇……[3]”“祠部”即羅萬藻,因南明唐王朱聿鍵曾提拔羅萬藻為禮部主事而得名。“丙戌冬”就是順治三年(1646)的冬季或者冬月,根據明史記載,艾南英死后,羅萬藻“哭而殯之,居數月亦卒”與“丙戌冬”并不沖突,“冬”可能已經達農歷年末,在公元上已經進入1647年,將羅萬藻卒年定為1647年倒也不算錯誤。不過,鑒于使用同一標準進行規范,筆者認為生卒年定為1581年—1646年較為妥當。
2 羅萬藻文學思想
2.1 時文創作觀
羅萬藻的一生,學識廣博,致力為文,勤于著述,成果頗豐,現存《十三經類語》《此觀堂集》,存目于《四庫全書總目》,另有《羅文止稿》制義專集。在時文創作中,他崇尚古雅,倡導唐宋派文風,去陳取新,獨辟蹊徑、自成一體,取得較高成就。
(1)主張經世致用。羅萬藻作為湯顯祖的弟子,繼承了湯顯祖為文現實性很強的特點,文章要能夠切中時弊,尤其要反應現實社會或者說更加講求文章的實用性。明朝成化年間,科舉考試經義文章格式逐漸定型,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組成,稱為“八股文”,又稱“制義”或“時文”。羅萬藻與艾南英、陳際泰、章世純等參加豫章社,致力于著書立說、評選時文、刊布檄文等,通過文章表達積極參與政事,表達政治主張。如羅萬藻所言:“文之有社,士所自為政之地也。教養道詘,學宮廣厲之具闕然,豪杰之士高視遠踞,見其具亦復非笑,三歲一比士,往往不足服其所為,故相憐相引,連而為一社。[1]”而作為豫章社成員,羅萬藻的時文創作主張也往往會將“通經”和“舉業”聯系在一起。他說:“予少見八股之業,字句章段,起結過送,軟腐相承,別為一種習氣之物,欲以六經秦漢之致澤之,而深浸時文之相,此予初志也。[1]”說明他的本意是通過儒家經學來改進八股文創作。他倡導“代圣賢立言”,強調立論的思想性和道德性,以此提高時文創作立意,提升在科舉考試中的實用性。他在尊經學古的同時也反對貴古賤今,強調文隨時變。他說:“夫文章之道,日益之事也。益而不已,則或變其體以相出。夫前人之所未足而益之,與其所既益而變之,此作者之事、文字相趨之理也……故史遷益丘明而變,固之變遷,曄之變固,而損益互見,古有之矣。[1]”他認為,每一種文體的產生、發展、變化都是依時依勢而來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文體在變化發展過程中,都會有優缺點顯現,沒有必要貴古賤今,而應該隨文體的發展演變以及時代發展而變化,才能創作符合體裁發展和時代需求的文章。
(2)注重“法”“理”“神”“氣”。羅萬藻為文偏向于師法唐宋,提倡文章要遵循一般規則和法度,保持文體正而品格高。他在《韓臨之制藝序》中說:“自唐宋而下,所謂抑揚、開闔、起伏、呼應之法,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儒設之,遂以為家……今制藝之文,其法不得不以諸儒為帝祖,至夫工致蜿蜒、華情爛漫,皆法立而后從之者也。[1]”所以,他提倡以以唐宋派文章創作抑揚開合、起伏呼照之法為依歸,師法的基礎上再談修辭及其他。他在《梁公狄聯捷稿序》中說:“公狄之制藝具在,其為世務經濟之文,半其為性學名理之文,半當其為經濟之言。規條古昔,苞蘊今茲,精魄主張更傳而入,于細而所謂名理之言。[1]”也就是說,創作文章重要的是能通經講理,即要研讀經典,深入闡發圣賢經義,追求說理的深度,要“性學名理”,也要“世務經濟”,能夠借古鑒今而富含哲理的文章才能夠流傳下去。他的理與情相通,也是性情之理,是人之自然情感流露。他還說:“出入有度,而神氣自流。[1]”提出:“蓋經散而為章,析而為句,句必有重字,章必有重句,深討之士與之曲折而得其神,此時胸識離于訓詁之物,必相千萬數矣。而其氣象散見于唐虞三代之間,述于當時圣賢之口,無一事一語不與吾所謂一章一句者表里出入。[1]”他指出,通過章、句、字去理解經義得其神,通過領悟圣人言得其氣,有神氣才能氣象萬千、表里相通。他還在《曾行可制藝序》中說:“文章以氣為主,世頗傳之,而不精于其說。夫輕重緩急之所踞者,理也;而貴賤雅俗之所陳者,氣也。語理者必兼氣。[1]”人以氣節立世,文以氣而傳之。從內因來說,文學創作是自我情感高度積蓄狀態下的意氣渲發,是一種情感機制狀態下以“氣”的自我表達,在此基礎上的輕重詞辯而形成理,所以“語理者必兼氣”[1]。他的時文創作也反映了他這一觀點,正如清代方苞對羅萬藻時文的評價:“淳潔之氣盎溢言外,惟其沉酣古籍,而心知其意。[4]”
(3)追求創新。湯顯祖曾說:“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羅萬藻也沿襲了湯顯祖這一“文奇觀”。他主張師古不泥古。一方面是前文所說的文隨時變,另一方面,他反對對時文矯枉過正和機械模擬。他曾在《國表序》說:“嘗見洪、永至成、弘之間諸名元正派而外,奇軼之文傳于今者古色班剝,意當時必未嘗以其非格而斥之耳。使當時斥之,今日學者之席安得此先輩而奉之乎?戊辰以來,矯枉過直之病,當事所不免。[1]”以此來委婉規勸艾南英評選時文莫要過于苛刻,防止矯枉過正。他主張學習先輩大家之文,但反對刻意外在的相似或者流于形式的模仿。他說:“徒欲效其所為約且簡者,以為高古淡質盡在于是。[1]”他贊成艾南英用成、弘、正、嘉之文來救正晚明時文的理論主張,批評了后復社張溥、周鍾提倡的以經、子詞語入時文的現象,主張因時而變,不該過于拘泥,容易流于模擬,而應在種種限定中尋求雄奇變化創新,令文章才思煥然,以此匡正崇禎元年以來偽經、偽子入時文的傾向,挽救晚明時文。
2.2 詩歌創作觀
因明代科舉考試對于詩歌的排斥,明代的讀書人又多以科考為主要學習目標,對于詩了解不多,能寫詩、善寫詩的人就更少了。羅萬藻作為時文大家,專攻制義文章,于詩學一道,沒有專攻。但他對于詩的創作繼承了湯顯祖感于世事、情景交融的思想。他自知不善于詩,也清楚明白整個明代善詩者少,好詩亦少。他認為詩和文創作都與人的才氣有關,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術業有專攻。他曾在《崖西詩序》中說:“予初不知詩,亦未嘗敢易言詩也。將詩之難言歟?抑予之才未至是歟?古文諸體,惟詩格律最嚴,唐世專以取士。雖李、杜諸人之才,于他文終不擅美。非其才不足也,詩盡之也。入明以來,學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藝,而以其制藝之余及詩。自有諸科以來,獨制義格律之嚴,與詩正敵爾。夫人事有所用,銳異之氣,于焉畢竭。故一代之傳業在是。[1]”所以明代的詩創作質量不高,不是因為才氣不夠,而是因為才氣集中工于制義,用余力創作的詩顯得后繼無力,怎可能跟唐代專攻于詩的相媲美呢?雖然在時文創作中他主張創新,文隨時變,但對于明詩拘于模仿的問題他并沒有提出相應的觀點。
他認為個人的經歷遭遇和社會環境對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他說:“使文人果閉戶作詩,山川人物,胸腹未觀,固不如一行作吏,東西南北,惟遇之使,從此勞逸殊方,險夷異感,人情同獨之致,見聞常怪之徵,感發陶練,情深韻老之于此道為宜也。[1]”他以唐代蘇味道、李嶠和李白、杜甫進行舉例驗證,說:“古今詩人,蘇李禘祖、甫白郊宗。然后世能言之士,視蘇、李之時,如天閶初啟,其所言獨道,甫白蓋其開疆擴境,創法垂憲,得于遭遇游歷,廢興治亂之感,以發性情而老思理。天才雄挺,功詣良多。其取資正不淺矣。[1]”蘇味道、李嶠在于他們的初創,所言獨到,開創特色;而李白、杜甫能夠拓展詩歌,創建根本法則的原因在于他們的人生遭遇、游覽經歷,還有唐朝興盛動蕩變化與個人的獨特性情結合在一起形成的。
此外,羅萬藻還認為詩歌是情致而發。他認為古人關于忠孝的言論,是因悲涼而激越的感情而編寫的,有理有序;還有那些雄文博學的人,脫口而出有音律,應是天人感應之致。《詩三百》之后有《離騷》,《離騷》之后有詩文,詩文之后有詞賦。屈原義兼親賢,如果不是遇到上官子蘭這樣的人,也不會作出《離騷》這樣憂怨之作,成就其以憂國憂民而流芳百世。他還以南宋愛國詩人謝翱為例進行論證。他說謝翱“以其哭不朽”[1],后世評說謝翱詩集《晞發集》的水平直追盛唐。他認為,如果謝翱不是經歷宋代滅亡,感于文天祥之死,也作不出這樣的詩歌。因此,他提出:“由此言之,情不絕,語必不至。文字皆然,而況詩之道乎![1]”
3 結語
在明代后期的背景下,科舉考試的板式化逐漸禁錮了文人的思維思想,時文逐漸趨于僵化死板、生搬硬套,而詩歌地位不受重視,作詩全憑模仿,沒有新意和靈氣。作為湯顯祖的弟子,羅萬藻在文學上的一些觀點都深受湯顯祖影響,但又有其自我的思考和觀點。在時文創作上,他以挽救晚明時文為己任,更注重時文的現實用途,師古不泥古,講究“法”“理”“神”“氣”結合,提倡創新。同時,作為明代的時文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時文,少涉獵詩,但也對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詩歌創作源于人的遭遇經歷和社會環境變化,發乎性情,情致而發。而對于明代詩歌的衰敗,在他看來,因為每一代文人專攻不同,明代學子致力于研究創作時文,所以詩文創作成就不高,簡而言之,就是時代造就,人力有限。■
引用
[1] 羅萬藻.此觀堂集[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一百九十二冊)[Z].濟南:齊魯書社,1997.
[2] 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 陳孝逸.癡山集[A].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四十九冊)[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4] 方苞.欽定啟禎四書文·文武之政[Z].武漢:湖北崇文書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