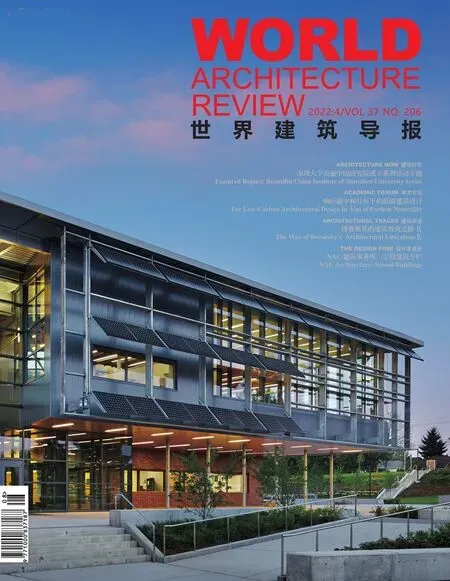科倫坡無保障住區的住房問題概述
作者 | Author:沙利尼·庫瑞 Shaleeni Coorey (sbacoorey@gmail.com,scoorye@uom.lk)/ 斯里蘭卡莫拉圖瓦大學建筑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University of Moratuwa,Sri Lanka;香港大學建筑學博士 Doctor of architecture,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圖1:a.Udagam-Suramyagama 33 示范村鄉村住宅;b.Raddolugama 獨棟住宅;c.Gunasinghapura 城市步梯式公寓;d.Methsanda Sevana 高層保障房

圖2:a.Gunasinghapura 公寓;b.Bambalapitiya 公寓;c.Narahenpita Anderson 公寓;d.Maligawatta 公寓
1 背景介紹
根據2012年更新的調查和統計數據顯示,斯里蘭卡的土地面積為65610km2,總人口為20,277,597人,人口密度為323人/km2,年均人口增長0.7%。人口按照經濟成分可分為城市、農村和莊園種植園(estate plantation)類。根據 2001年人口普查顯示,城市、農村和莊園種植園人口占比依次為 14.6%、80% 和5.4%。科倫坡地區(Colombo District)聚集了全國最多的城市人口(54.6%),民族多樣,包含僧伽羅人(Sinhalese,76.6%)、斯里蘭卡泰米爾人(Sri Lankan Tamil,11.0%)、印度泰米爾人(Indian Tamil,1.1%)、摩爾人(Moors,9%)、伯格爾人(Burgher,0.7%)以及其他民族(1.6%)。科倫坡地區位于錫蘭島的西南部,總土地面積為699km2,城市化程度位列斯里蘭卡之首,其人口和人口密度也是各地區中最高的,分別為2,323,826人和3,438人/km2。斯里蘭卡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是位于科倫坡區的科倫坡市(Colombo City)。這里是斯里蘭卡的商業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土地面積37km2,常住人口555031人,并有50萬流動人口的日吞吐量。在遷都至科特的斯里-賈亞-瓦德納-普拉-科特之前,科倫坡市曾作為斯里蘭卡的首都兩百余年,至今它仍是國家的樞紐和中心。科倫坡市的人口密度高達13,364人/km2,與亞洲其他高密度城市不相上下。
根據城市發展局(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簡稱UDA)2010年的調查顯示,科倫坡共有68,812個家庭分布于1,499個無保障住區,這些無保障住區沒有清潔水、電、衛生設施等最基本的基礎設施,無法提供人類生活所必須的健康環境。生活在這一條件下的人口占科倫坡城總人口數的51%,他們分別聚集在1,506塊沒有明確產權的國有土地上。在過去的5年中,約有390公頃的優質地塊被這類居住區占領。此外,所有環境敏感型低洼地區,例如運河河岸、防洪區,以及公路、鐵路保留地和其他開放空間也都被無保障住區占據。城市貧困人口的住房是大多數亞洲城市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科倫坡也不例外。由于人口的涌入和城市化,提供足夠優質、適居同時又經濟、可持續的住房成為一項重大挑戰。公共部門非常重視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滿足需求的住房,但一直以來都將保證數量放在首位,因此缺乏關于提高住房質量的研究、開發和應用,這是科倫坡無保障住區住房建設中最關鍵和最緊迫的問題。大量的保障性住房項目正在建設中,但這些住房作為棲居之所卻沒有多少吸引力。相反,它們缺乏城市生活的活力、多樣性和穩健性,變成單調的大型混凝土“圍墻“,將社區困在其中。本文將討論城市住房政策的演變和公共部門干預,重點關注公共部門住房干預所面對的挑戰和暴露出的缺點,尤其是科倫坡無保障住區的住房建設。
2 斯里蘭卡住房政策概述
2.1 城市和鄉村的住房政策
斯里蘭卡的住房政策可分為城市住房政策和農村住房政策。城市住房政策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低收入者住房和中產階級住房。農村住房政策包含場地、服務和庇護所作為住房策略。“Udagam”示范村就是政府給出的此類農村住房范例(圖1)。城市住房包括有私有土地房產(獨立樓房)、步梯式公寓(公寓樓)和低層(3層及以下)、多層(4~8層)、中層(9~12層)、高層(13層及以上)公寓(圖1)。
2.2 城市住房政策
斯里蘭卡城市住房政策的發展可分為3個階段:從英國統治下獨立之前(1948年之前)、政治獨立后和內戰期間(1948-2008 年)、以及30年內戰結束后(2009年以后)。Herath &Jayasundera于2007發布的研究為城市高層住宅建設的出現劃分階段:1977年之前,1977-1998年間,1999年之后開發的住宅項目。他們觀察到科倫坡市的高層建筑的增長也分為3個階段:1)1999-2003年間,多層占比更高(49%);2)2003年起,中層建筑開始增長(9%);3)2003年之后,高層建筑(超過13層)顯著增多。
二戰前,斯里蘭卡的大部分住房建設均為私有。然而,二戰期間城市地區住房短缺情況凸顯,該局勢為國家逐步干預和控制住房建設創造了條件。在獨立后和內戰期間(1948-2008年),公共部門主導的住房建設集中在為公務員(中等收入水平)建造的低層(大多不超過4層)公寓。這些項目的主要特征表現為擁有大面積開放空間、寬闊道路和公共空間的線性街區。一些步梯式公寓也建于1977年之前的這段時間(圖 2)。
隨著1978年城市發展局(UDA)和1979年國家住房發展局(National Housing Deve-lopment Authority,簡稱NHDA)的相繼成立,公共部門主導的住房開發迎來了繁榮局面。UDA制定了必要的城市規劃和建筑法規,啟動了城市再生計劃,為城市發展騰出寶貴土地。1977年之后,公共部門通過 NHDA 開發了多個住房項目,例如 Manning Flats、Elvitigala Mawatha、Edmonton Road、Park Road 和 Torrington Flats。雖然這些仍是類似于1977年之前建設的低層步梯式公寓(圖3),但政策層面已經逐漸發生改變:最大化放開私企對住房的投資,而公共部門僅扮演輔助支持的角色。

圖3: a.Elvitigala 公寓;b.Manning 公寓;c.Torrington 公寓

圖4:a.位于Wanathamulla 的Sahaspura 保障房;b.區位圖(來自16 個瓦塔社區的居民搬遷至11 棟共600 戶的住宅樓中)

圖5:a.自由廣場,1980 年,第一座混合開發公寓;b.“王后”公寓;c.“國王”公寓

圖6:a.Havelock 城,2009 年,20-28 層/8 棟/1080 戶;b.Crescat 公寓,2077 年/2009 年,Crescat emperor— 35 層/ 1 棟/173 戶,Crescat Monarch — 30 層/1 棟/ 205 戶,Crescat Residencies — 24 層/ 1 棟/ 152 戶;c.Trillium 住宅區,2009 年,11 層,5 棟,300 戶;d.Empire 住宅區,2008 年,36-40 層/2 棟/104 戶
1977年是斯里蘭卡住房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這一年政府將住房列為新投資的關鍵領域之一,做出了在6年內建造100000套房屋的承諾,希望將斯里蘭卡創建為“有房社會”。100,000住房計劃(1978-1983年)作為先行項目,為西部省(科倫坡都會區)提供了多個大型公共城市住房綜合體。繼“100000套住房計劃”取得成功后,政府緊接著啟動了“百萬套住房”計劃(“Million Houses” Programme,1984-1989,簡稱MHP),為城市和農村地區建設住房。MHP不僅由政府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建造者家庭也最大程度地參與其中,是由地方當局管理和國家機構支持的以社區為中心的參與性住房計劃。在“百萬房屋”計劃取得成功后,政府又推出了150萬房屋計劃(1990-1995),其目的是解決社會各階層的住房問題。這一時期的住房政策設想在為城市地區提供更多住房的同時,改善農村/莊園住宅質量。NHDA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和基礎設施建設,協助升級和改善住房/生活環境。但由于1983年的經濟衰退,政府的角色從“提供者”轉變為“促進者”,在自助或參與式的基礎上進行干預。
1994-2005年,科倫坡推行緊湊型城市開發。可持續城鎮計劃(Sustainable Township Programme,簡稱STP,1997)由房地產交易有限公司(Real Estate Exchange Limited,簡稱REEL)推動,將貧民窟和棚戶區居民安置于高層住宅,以釋放更多用于商業開發的城市土地。2001年,Wanathamulla地區為城市貧民建造了第一座“高層高密度垂直住宅”,名為“Sahasapura”,高11層,由600個住房單元組成(圖4)。
30年內戰(2009年以后)結束后,私有住房數量顯著增加,主要分為高收入群體的“豪宅”和低收入群體的“剛需”兩種類別。由于公共部門批準了大塊土地可用于房地產開發,加上外國資本的投入,對高層住宅的需求表現顯著。科倫坡市在 1999 年的發展規劃修正案進一步推出了混合發展、潛力城區的高層開發、開放空間和城市濱水區、引入發展指南來規范每個規劃區域等多項措施。其中,混合發展包括公共開發和私人開發的超大型住房項目。此外,2005年的政府選舉宣言中還提出“每一個斯里蘭卡的家庭都應擁有自己的住房”,進一步推動了對住房的投資和開發。在此期間,政府還發布了“十年天際線發展框架”,以期滿足斯里蘭卡對房屋不斷增長的需求。該政策旨從人口密度、土地適宜性、環境可持續性3個層面確保居住環境的合理規劃。圖5~7展示了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2000 年多層住宅和混合開發類型的逐漸演變。
3 科倫坡的無保障社區/住區
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地考驗著住房供應。與多數發展中國家相同,城市貧困人口的住房供應成為科倫坡的一項關鍵問題。根據CMC地區的用地性質圖顯示,無保障住區廣泛分布在科倫坡北部和東部;科倫坡無保障住區的規模大多相對較小,少于50個住戶的占74%,只有0.7%的住區擁有超過500個住戶。這些無保障住區被劃分為貧民窟、棚戶區、無保障半城市化街巷、勞工群體(Labour Lines)或廢棄的生活區。這些具有明顯特征的窮人生活的住區在當地統稱為“瓦塔”(watta)。自“瓦塔”中生長出的社區被稱為“瓦塔社區”(watta community)。“Watta”在僧伽羅語中的意為“莊園”[1]。主流社會對這些社區持負面看法,認為他們物質層面貧窮,社會地位低下。然而Silva&Athukorala對科倫坡無保障住區所做的案例研究表明,他們是一個具有鮮明特征的、向上流動的社區,其中大多數是在當地扎根的長住居民,通過鄰里聯系、共享經驗、共同利益、甚至正式組織而聯系在一起。這里,以定期聚會的場所為中心發生著頻繁的社交活動,精品店、嬉戲廣場、公共浴室、打水處等設施一應俱全;在人口密集的居住區中,住房單元之間的緊密的物理距離加強了鄰居之間的相互照應。外部威脅促成了內部利益共同體,人們之間互相幫助,交換包括食物、衣服、珠寶和家用電器等物品;當有親戚或訪客時會相互借宿,或需要修建房屋時,人們會相互提供資金和人力的支援。
3.1 無保障居住區的類型

圖7:a.阿泰爾拱門,摩西·薩弗迪;b.雙子峰;c.科倫坡城市中心;d.辛納蒙生活
按照住宅類型,即形態、規模、物理條件、材料、所有權和區位,可將科倫坡的無保障住區分為4種類型。1)貧民窟:破舊的老公寓或單間的廢棄房屋。由永久性材料建造,通常是單間,緊湊地背靠背排成一排(圖8)。居住者具有明確的法律承認的居住權。2)勞工群體或廢棄居住區:這些是屬于地方當局或政府機構的廢棄住宅區,被零工從業者占用(圖9);由于長期缺乏維護,這些定居點處于衛生條件很差的廢棄狀態。3)棚戶區:棚戶區多建在政府或私有的未使用的地塊的邊緣處,多位于道路保留地、河流或運河岸邊,以及容易發生洪水的低洼地區;與貧民窟相比,棚戶區由當地可找到包括卡揚[2]、木板、錫、聚乙烯板和其他工業廢物等臨時建筑材料或廢棄物來建造(圖10)。這里只有最基本的市政服務,例如公共廁所和安裝在公共區域的水龍頭;這里的居民被視為未獲得身份的城市居民。4)無保障半城市街區:科倫坡郊區和二線城鎮的市政服務較差的住宅區;與棚戶區的不同之處在于,這里的居民擁有明確的合法產權,且地塊面積較棚戶區更大。
3.2 無保障居住區的住房供給措施
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市場中發揮著多重職能,既是政策制定者和監管機構,又是住房推動者和融資者,還是住房和基礎設施的開發商。除城市地方政府外,NHDA、UDA 和城市住區發展局 (Urban Settlements Development Authority,簡稱USDA)是涉及保障性住房的主要政府機構,但它們的職責多有重疊,發揮的作用也視政府資金支持而異。無保障住區可根據其地理位置和地塊發展需求分為3個類別:1)處于戰略位置、土地價值高的地區;2)處于待建基礎設施的保留地,如規劃鐵路用地;3)地處邊緣,住房充足,只需改善基礎設施。政府對這3個類別采取的措施分別為“重建” “搬遷”與“整合”。
自1948年獲得獨立以來,斯里蘭卡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尋找解決住房問題的辦法,并相繼出臺了政策、指定計劃和開展項目來解決科倫坡的住房問題。然而,事實證明這些計劃中的大多數只是臨時解決方案,并沒有對住房部門產生任何重大的長期影響。直到 2001 年,高層保障性住房(五層以上)才被列入斯里蘭卡政府的城市規劃議程。從那時起,科倫坡政府就一直試圖說服貧民窟居民搬遷到附近的高層公寓,以從他們手中收回那些有價值的土地。
自2009年內戰結束以來,斯里蘭卡政府一直優先發展城市,尤其是作為商業中心的科倫坡。政府第一時間對無保障住區居民進行重新安置,重點推行“雙贏“的緊湊型城市概念,其口號為“為人提供房屋,為投資提供土地”。改善城市無保障住區需要的不僅僅是通過貸款融資幫助個人住房進行升級改造。這些居住區大多是非法的,土地所有權的規范化是城市居民投資中的關鍵;這些居住區通常沒有基礎設施和市政服務,因此需要建設自來水系統、衛生設施、排水系統以及道路;這里的房屋建設也經常違反建筑法規。UDA已經通過提案并決定在這些地區實施更多的住房項目,并為物質、社會、經濟的基礎設施升級換代,在重視住房發展的同時也重視民生的發展[3]。
3.3 城市再生項目與城市貧困人口住房供給
2012-2013年,政府啟動了作為科倫坡城市更新計劃的一部分的“城市再生計劃”(Urban Regeneration Programme),重新關注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根據城市發展和住房部的進度報告(2021年),該計劃旨在5年內建造約 50,000套住房,以安置貧民區的居民,并為城市發展騰出寶貴用地(圖11)。該計劃的資金來自出售已釋放的土地,目標實現每英畝300戶兩居室,標準套內面積為400-500平房英尺。“城市更新計劃”已經啟動了若干住房項目。
3.4 城市貧困人口住房供給所面臨的挑戰
盡管政府填補了住房數量的缺口,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導致這些開發項目不盡如人意。值得注意的是,高層住房并不是普遍通用的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解決方案,這在一些國家行不通,但同時其他一些國家則表示通過此方法取得了成功,甚至一舉將低收入人群提升到中等收入狀態。Samaratunga &Hare于2013年發布的研究表明,高層低收入住房的成敗取決于以下4個方面:1) 社會和文化;2) 建筑、規劃和技術;3) 財務;4) 管理和運營。但不幸的是,這些經驗并沒有在“Sahasapura”之后住房開發項目中得到延續。Samaratunga &Hare指出,斯里蘭卡的城市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常更關注住房生產而非社會問題。何種標準使得房屋成為“家“,這對于任何社區都至關重要,對于城市貧困人口而言尤甚。科倫坡高層保障性住宅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包括下面若干方面。
3.4.1 缺乏參與方式
棚戶區規劃的傳統方法始于NHDA的規劃人員對該地區所有現有建造物、便利設施、道路、樹木等的詳細調查。在社區行動規劃中,城市低收入住區的人口是發展的主要資源,而非發展的物質目標或受益者。具有專業教育背景的從業人士可能難以開展此類研討會,而生活在這些住區居民真正參與決定了議程,主導討論并得出結論。將這些專業人士轉變為以人為本的規劃者,使他們可以與低收入社群互動并承認其意見和決策的價值,需要一定程度上擺脫知識的束縛。然而在現實情況下,社群并不能理解專業人士制定的計劃。這些計劃通常過程緩慢,且需要搬遷大量人口,在社群中造成相當大的挫敗感。
3.4.2 缺乏維護和服務
1990年代實施的早期計劃的住宅維護不足。居民普遍抱怨電梯缺乏維護(圖12),他們還不斷向政府提出公共區域需要保潔的訴求,但沒有得到任何實際行動層面的回復。
3.4.3 需滿足基本需求
與私宅相比,公共住房的設計在短時間內會發生數次變化,這主要由于人們對居住環境的感知被忽視了;大多數修改都是為了滿足人們基本居住需求之上的心理、身體、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需求。
3.4.4 需獲得交通、服務、便利設施和開放空間
對于已搬遷和將要搬遷的居民來說,他們非常擔憂子女們無法進入科倫坡最好的國立學校,他們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以及上下學的通勤。從居住生活方式的改善到自我提升,這些很大程度歸因于他們就讀的學校和社會關系。對于這些社區居民,失去優質教育資源是一項重大損失。那些已經上學的兒童,搬遷也意味著通勤距離的增加。一些家庭選擇將孩子轉到離新家較近的學校,因為他們負擔不起日常的通勤費用;而這些學校的教育質量與以前的學校相去甚遠,只能眼看著孩子的學習成績下降。另一些家庭不得不想辦法安排或親自接送,并找親戚或鄰居在課后幫忙照看,這些都是他們以前不必承擔的費用。
新開發住宅周圍沒有供兒童嬉戲的場地也是問題(圖13)。社區內不同年齡群體的活動設施對于大規模住區至關重要,如游樂區、運動場、體育設施,以及娛樂場所,如購物中心、電影院等。新加坡、香港的鄰里概念一直立足于確保居民可方便地前往社區商場和與社區相關的活動中心。他們的公共住房計劃理念是將具有不同經濟能力的人混合在一個社區內。資源共享,基礎設施便利化,以開放空間和娛樂場所的形式將這些次要功能結合在一起,以滿足所有年齡段居民的社會和心理需求,確保安全和健康的居住環境。通過混合用途開發可以確保學校、醫院和便利設施的可達性,公共和私人住宅組團的混合可達到這些服務和設施所需的人口密度。此外,連接混合社區集群的公共交通網絡進一步整合,為社區和服務提供了高水平的可達性。

圖8:貧民窟(無保障住區)

圖9:廢棄住區的場景
3.4.5 個性化的機會
公共住房的設計階段缺乏最終住戶的參與,只提供滿足相似需求的典型布局。盡管如此,最終用戶還是會進行一系列改造,以滿足他們個人的使用需求。但這一過程并沒有建筑師的參與,在沒有空間規劃和設計知識的指導下進行改建,導致最終的可居住空間和生活環境質量較差。有人認為,這些住區的住宅原型缺乏自我表達,導致對潛在買家沒有吸引力。在住房中里注入個人的自我表達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文化需求。
一些批評者還指出,人們急需一個住所來滿足他們的住房需求,在擁有住房后,人們會改造這里,尤其是房子的外部,以打造屬于自己的個性化的生活環境。這還揭示了居住者在社會-經濟層面的進步,主要表現為收入和社會地位兩個方面。
3.4.6 心理和社會文化需求的滿足
除去滿足住宅功能和活動空間外,空間還反映著居住者的身份。居住環境的領土化可以看作是居民改造空間這一行為背后的一項主要屬性。對廚房和私密空間的添加、修改和翻新一直是一個主要問題。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居民需求與物理空間之間的不匹配。改造行為是在沒有專業知識的情況下完成的,因此導致居住空間的進一步惡化。一些局部的修改和布置的變化,可能導致日照和通風的減少,活動受限。許多心理上的不滿反映在居住者身上,居民之間缺乏社會聯系。
居民通過增加或改建隔墻、柵欄門,改變外墻或大門的材料和顏色等,以彰顯個性,增強隱私和安全性。新的住區還缺少能夠整合社區的豎向連接和空間關系。原本人們居住在房屋彼此相鄰的社區中,但搬遷后的公寓是隨機分配的,這導致來自同一社區的家庭居住在不同的樓層,甚至不同樓棟。這意味著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社交、支持網絡被打亂。
由負面社會認知引起的社會污名是這些高層社會住宅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歐洲的戰后住房中有許多這類負面案例。但與歐洲城市不同的是,科倫坡住房開發中的種族和多元宗教沒有成為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住宅這里的居民缺社會認可,他們作為住在保障性住房的低收入人群被“看不起”,因缺乏一些所謂的城市特權而產生恥辱感。將住房分配給具有相似社會和經濟問題的低收入群體,加劇了這些社區的社會污名化,“禁區” “貧民窟”和“負面空間”等一系列污名進一步造成了惡性循環。搬來這里的居民被迫和“本地性”分離,再次搬出去又使得這類住房喪失了可持續性。因此,增加不同收入的群體和不同住宅類型的混合度,能夠幫助社區營造正面形象,這對于居住者的心理需求、形象和身份以及發展都非常重要。
3.4.7 功能空間需求及其增長和擴建
家庭成員的增長往往被忽視。隨著孩子的成長,他們對空間的使用目的和需求也在發生變化。缺乏適應性的空間導致居民無法實現功能和空間上的更多需求。這些住宅都是類似的兩居室戶型,將客廳面積壓縮至最小,家庭成員增加、邀請親朋好友做客、社交活動等都受到限制(圖14)。
3.4.8 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
有時,額外的空間可能起到改善家庭收入的作用。這些空間可作為店鋪或工作間,為家庭提供額外的收入。因此,一旦家庭安頓下來,這些以追求增加更多經濟貢獻為目的的改造就產生了,但往往例如通勤或以家庭作為創收場地的選擇之類的居民生計問題沒有得到滿足;這些住區也沒有考慮到出租車(tuk-tuk)司機的停車需求,新住房也缺乏開展家庭園藝、小生意的條件。這些住宅開發項目與現有的城市網絡、活動和功能隔離開來,這對于一個繁榮發展并依賴于當地環境和商業機會的社區來說非常不利。
3.4.9 社會互動和鄰里關系的機會
空間模式過于正式,缺少過渡空間、以及從公共空間到私人空間的逐漸轉變、缺少非正式活動的空間。街區的形式化剝奪了能產生更好鄰里之間的社會聯系的重要品質,而高層住宅缺乏空間過渡和空間等級。研究表明,上層的居民與其他層的鄰居彼此孤立。新住區還缺少能夠整合社區的豎向連接和空間關系,大多數街區的空間布局是線性和正式的;集中的形式和布局可以創造更多接觸機會,并避免單側的長線性走廊,集中式社交場所可以增強社區精神。入口空間是社區之間交流、互動和聯系的空間,在低收入住區發揮著重要作用。
搬遷至新住區的住房分配,失去原來貧民窟社區的社會聯系以及近鄰之間的聯系,這使得新家園成為陌生的地方,需要適應各方面變化:空間限制、生活方式的改變,垂直式生活方式、生活服務可達性、通勤以及新的鄰居。這種適應往往難以承受,而且在分配住房時,他們過去所擁有的社會支持和網絡被當局完全忽視。因此,必須考慮應對這些使低收入社區適應新住房具有挑戰性和不滿意的困境。
3.4.10 對隱私和安全的需求
高層住宅的隱私性也是一個問題。研究強調,作為交互空間的緩沖空間有利于形成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之間的隱私性,而這類空間在保障住房設計中往往被忽視。正如 Samaratunga &Hare (2013a)以及其他歐洲戰后住房的廣泛研究顯示,蓄意破壞、非法營生、暴力、毒品和有組織犯罪等問題導致了二戰高層住宅的失敗。我們在高層保障住房的試點研究中也發現類似問題,許多家庭抱怨孩子無法在吸毒、打砸等非法活動頻發的區域安全成長。他們擔心孩子和青少年的未來以及生活環境受到負面影響。
4 結論

圖10:棚戶區(無保障住區)

圖11:a Mihindusenpura 居住區;b Lakmuthu Sevana 居住區;c Sirisanda Sevana 居住區;d Sirisara Uyana 居住區;e Randiya Uyana 居住區;f Sirimuthu Uyana 居住區

圖12:Sahaspura 保障房內的場景
正如Nirilella所說,大量的住宅建設通常只考慮量的問題,例如收入水平、家庭規模、建筑面積、設計標準、成本、利潤或過剩等;然而,人們對住房質量的天然要求也應該被同等考慮,提升質量本就是大批量住宅建設要面臨的挑戰,對于在各個層面都以時間和成本為首的保障房項目而言則更甚。質量需求包括社會文化和心理要求,例如環境質量、身份、隱私、安全、社會地位等。任何人都希望擁有一個家,而不僅僅是一所房子,了解怎樣的標準、品質或框架才能夠營造出“家”的感覺很重要。“家”因社區不同而高度個人化,這些正是需要在未來批量住宅項目中實現。不過在這一語境下,部分批評者認為以單調、大型綜合住宅區的形式解決斯里蘭卡的住房問題是失敗的。政策制定者、地方當局、規劃者和建筑師不僅需要學習過去的國際案例,例如歐洲的“二戰后住房”,還需要從當地案例中學習,從策略、形式、尺度、類型、總體規劃和設計等各方面進行改進。滿足數量、時間和成本方面的需求不應以犧牲空間質量、功能要求、營生、社會活動、生活服務、交通和便利設施和安全性為代價。

圖13:保障住房樓間的公共空間

圖14:a.Sahaspura 的廚房;b.Sahaspura 一層的商店
注釋
1譯注:應該與在莊園中從事種植活動的農工相關。
2譯注:Cadjan,椰子樹葉編制成的席子,用作屋頂或墻面等圍護結構,常見于斯里蘭卡、印度等地。
3https://www.uda.gov.lk/urban-regeneration-programme.html.
圖片來源
圖1a:http://www.nhda.lk/index.php/en/component/k2/item/371-suramyagama-the-33rd-model-village
圖1b:Fernando,R.,&Coorey,S.(2019).Incremental Housing : the Underlying Force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Housing in Sri Lanka.
圖1c:作者拍攝
圖1d:Warakapitiya,Y.,Coorey,S.B.A.,&Perera,N.(2022).Pilot Study on the Issues relating to Low Income Housing-Colombo.
圖2a:http://www.nhda.lk/index.php/en/component/k2/item/371-suramyagama-the-33rd-model-village
圖2b:http://wikimapia.org/7146514/Bambalap-itiya-Flats
圖2c:https://www.ceylonproper-ty.lk/property/12011/anderson-flat-for-sale-in-colombo-5
圖2d: http://archives.sundayobserver.lk/2014/04/13/sec04.asp
圖3a:https://elvitigala-flats.business.site
圖3b:https://www.lankaproperty-web.com/sale/property_details-527630.html
圖3c:https://mapio.net/pic/p-83906831/
圖4:https://usda.gov.lk/awareness-programme-on-covid-19-prevention-control-sahaspura-housing-scheme/
圖5a:http://wikimapia.org/843565/Liberty-Plaza
圖5b:https://www.lankapropertyweb.com/rentals/property_details-353792.html
圖5c:https://www.raniyo.com/our-projects/queenscourts-colombo-3
圖6a:https://havelockcity.lk
圖6 b:https://www.sites.google.com/site/apartments4sales/crescat-apartments-colombo-3
圖6c:https://www.properties.360hitad.lk/property/apartment-for-rent-at-trillium-residencies-baseline-roadcolombo-8/
圖6d:https://www.skyscrapercenter.com/building/empireresidencies-south-tower/38648
圖7a:作者拍攝
圖7b:https://www.lankaproperty-web.com/sale/property_details-527630.html
圖7c:https://colombocitycentreresidences.lk/cccresidences-appoints-new-ceo/
圖7d:https://ultra.news/t-t/53608/hcl-tech-inauguratesswanky-new-office-in-colombo-with-10-floors-4k-seats
圖8,9,10,11: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URP)presentation -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
圖12:作者拍攝
圖13:Karunanayake,T
圖14a:作者拍攝
圖14b:Karunanayake,T (2018) B.Arch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oratu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