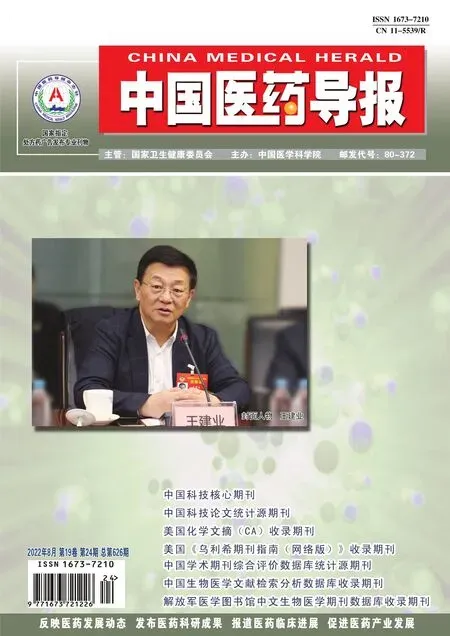基于U-net 卷積神經網絡宮頸癌磁共振臨床靶區和危及器官自動勾畫的應用
李 霞 劉 婭 王 聰 李振江
1.山東省菏澤市立醫院,山東菏澤 274000;2.山東省腫瘤醫院 山東省腫瘤防治研究院,山東濟南 250012
磁共振影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es,MRI)已成為宮頸癌ⅠB1 期及以上期別的標準診療方法,在影像診斷和腫瘤邊界鑒別方面有獨特優勢[1-2],并可提供治療評估及預后信息[3-4]。研究表明,基于MRI 確定的靶區,其體積要明顯小于以常規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確定的靶區[5-6]。應用MRI 圖像勾畫宮頸癌靶區,定義腫瘤靶區并進行局部加量,可將3 年生存率提高10%~20%,同時顯著降低胃腸道和尿道的毒性反應[7]。同時,由于治療過程中腫瘤消退、器官位置變化,對實時快速精確的臨床靶區(clinical target volume,CTV)和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OARs)勾畫的要求越來越高。應用深度學習算法較基于圖譜集自動勾畫方法準確性高、適應性廣,并提高輪廓生成速度[8]。基于卷積神經網絡提出的U-Net 體系結構[9-10],專門為醫學圖像設計,需要的網絡參數較少,訓練過程快。目前應用MRI 使用深度學習算法實現CTV 和OARs 勾畫,在宮頸癌放療中仍處于研究階段。本研究使用U-net 卷積神經網絡算法架構,以MRI 為基礎,建立宮頸癌感興趣區(region of interest,ROI)自動分割算法,并比較手動勾畫與自動勾畫的差異,擬為MRI 引導適應性放射治療提供自動勾畫技術支持。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4 月至2020 年12 月山東省腫瘤醫院根治性放療宮頸癌患者43 例。患者年齡20~65 歲,平均(48.6±9.6)歲;鱗癌34 例,腺癌9 例;國際婦產科聯盟(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4]分期為ⅡB 期13 例,Ⅲ期28 例,ⅣA 期2 例。納入標準:ⅡB~ⅣA 期的宮頸癌根治性同步放化療患者,放療前進行大孔徑MR 定位,定位圖像質量高,膀胱憋尿量為200~600 ml。排除標準:不能正常活動;具有MR 掃描禁忌證;既往盆腔手術或放療史;合并盆腔其他良惡性疾病或畸形。本研究已獲機構審查委員會批準(SDTHEC 201904001)。
1.2 定位方式及圖像采集
患者取仰臥位并使用負壓袋固定,治療前行大孔徑MR 定位。定位前充盈膀胱,排空直腸,掃描層厚3 mm。MR T2 序列分辨率352×352。每例患者獲得80~120 張盆腔MR T2 壓脂序列采集圖像,圖像覆蓋整個盆腔放療野。
1.3 圖像注釋
采用計算機進行簡單隨機抽樣,將43 例患者分為訓練集35 例,驗證集4 例,測試集4 例。由1 名有經驗的婦科放療醫師根據美國放射腫瘤學會[10]的宮頸癌靶區推薦及放射治療腫瘤組正常組織輪廓放射治療指南[11]進行人工勾畫ROI,包括CTV 和4 個OARs(膀胱、直腸、左股骨頭、右股骨頭),1 名有經驗的婦科放療醫師復核。
1.4 基于訓練數據集的U-net 模型開發
本研究網絡輸入為單層MRI 和勾畫數據,輸出為所對應的勾畫數據,使用同一個模型進行訓練。訓練集中的數據用于訓練模型,驗證預測數據與實際數據的差異,評價模型訓練的結果。測試集不參與訓練和驗證過程,作為獨立的驗證手段,用于驗證模型的適用性和魯棒性。
1.4.1 圖像取樣 訓練集圖片3 655 張,驗證集圖片340 張,將所有的數據重復取樣到(1.0,1.0,None)的體素后每次在單層數據中截取320×320 大小的圖像輸入網絡中。為獲得更多的數據量,避免模型過擬合,在輸入數據前對圖像數據進行圖像灰度浮動及圖像縮放形變兩種干擾[8]。在灰度浮動途徑中,將圖像上所有點的灰度值乘0.9~1.0 的隨機數,后疊加1 個-0.1~0 的隨機數。縮放形變途徑是將每一層的MRI圖像和勾畫進行仿射變換,所使用變換矩陣中任意兩個點之間的坐標值之差均在-0.2~0 的一個固定值,其中橫縱坐標分別為不同大小的值。
1.4.2 網絡構建 采用帶有殘差塊的U-net 網絡結構(圖1),包括編碼器和解碼器兩部分,且均由兩個卷積層的殘差塊堆疊而成,編碼器和解碼器之間使用特征圖躍層連接,融合高層語義信息和低層的邊緣細節信息。在訓練期間,在線進行縮放、旋轉、對比度亮度增強、高斯噪聲等增強手段,并采用標簽平衡方法對輸入樣本進行窗口采樣。訓練所使用的損失函數為Dice Loss,優化器為Adam,學習率為3e-4。

圖1 殘差U-Net 網絡結構示意圖
1.5 觀察指標
在測試數據集中分別計算Dice 相似性系數(Dice similarity coefficient,DSC)和勾畫時間,并對自動勾畫和人工勾畫的相似性進行比較。DSC 定義為DSC(A,B)=2A∩B/(A+B),其可對兩個感興趣區勾畫的相似度進行測量[9]。DSC 值為0~1,其中1 為完全重疊,0 為無重疊;DSC≥0.7 時被認為是輪廓之間具有較好的一致性[9,12]。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表示。以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模型訓練評價
模型訓練的Loss 曲線和驗證DSC 曲線如圖2 所示。訓練前期Loss 曲線下降明顯,800 次迭代時Loss值<0.1,之后緩慢下降。DSC 值前期提升明顯,迭代到達800 次之后開始震蕩上升,在3 600 次時達到了最優值。

圖2 訓練過程中模型的Loss 曲線和DSC 曲線
如圖3 所示,在訓練前期,膀胱已經有較好的效果,但CTV、股骨頭的分割效果還有待改進,直腸在不同的切片上表現不一。隨著訓練的進行,這些ROI的輪廓完整性、平滑度及勾畫精準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圖3 模型訓練過程中預測輸出變化
2.2 自動勾畫與人工勾畫耗時及DSC 值比較
患者平均自動勾畫耗時為(44.5±0.6)s,短于平均人工勾畫的(2 280.0±356.7)s,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自動勾畫與人工勾畫的DSC 值:直腸為(0.752±0.049);CTV 為(0.831±0.038);膀胱為(0.943±0.016);左股骨頭為(0.894±0.009);右股骨頭為(0.896±0.004)。
3 討論
放射治療的目標是動態跟蹤腫瘤的變化,但僅依賴放療前CT 來捕捉這種變化在治療過程中是不全面的[13]。MR 引導放射治療允許在治療過程中進行運動監測,通過實時解剖成像來提高放療精度。MR 軟組織對比度較CT 更優,精度更高[14-15]。人工勾畫每例患者的中位時間要超過1 h[16],隨著自動勾畫出現及發展使更頻繁的計劃調整得以實施[17-18]。自動勾畫在提高臨床醫生效率,減少勾畫不確定性等方面均有優勢[19-22]。
研究顯示,基于深度學習算法對OARs 自動勾畫準確度優于基于患者圖譜庫的方法[23-24];U-net 在性能和速度方面優于以往的其他分割方法[25-27]。本研究基于U-net 卷積神經網絡算法,以MRI 圖像為基礎,構建宮頸癌自動勾畫模型,并與人工勾畫結果進行比較。本研究結果顯示,自動勾畫與人工勾畫DSC 值最小為直腸(0.752±0.049),該結果與Wang 等[25]研究結果相似。可能是因為直腸是個體差異最大的器官,故DSC 值較低。同時本研究中CTV 勾畫也得到了比較理想的結果,應用構建模型自動勾畫ROI 后對CTV及直腸勾畫進行適度修改,膀胱、股骨頭勾畫較少修改后即可應用于MR 自適應放射治療過程,提高工作效率。在精準勾畫ROI 的同時降低患者長時間等待勾畫過程中的出現器官運動導致靶區變動。有助于個體化精確放療,在提高靶區照射劑量的同時降低OARs 受量。
本研究存在不足:患者入組樣本量少,且多為局部晚期患者;治療范圍內影像學表現有差異,導致ROI勾畫有個體差異。在之后的研究中將在增加入組量的前提下縮小入組期別差異,以期得到更精確的適用模型,針對性應用提高靶區勾畫效率。研究入組圖像為定位MRI,圖像質量及后續數據處理也有待進一步提高。
綜上所述,基于U-net 卷積神經網絡的MRI 圖像深度學習算法,自動勾畫效率高,與人工勾畫的差異較小,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協助MR 引導在線適應性放射治療實施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