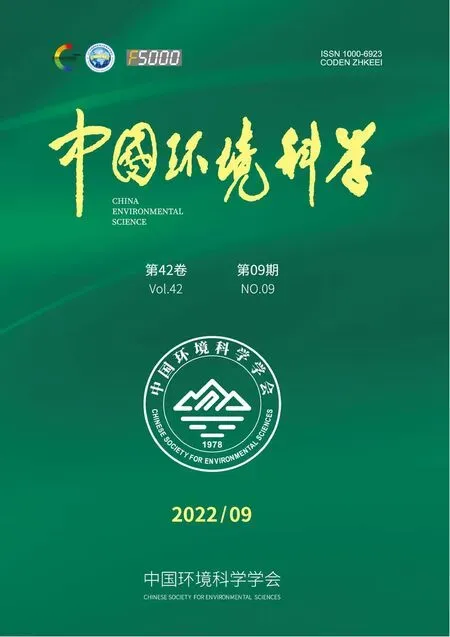碳市場對能源結構低碳轉型的影響及作用路徑
柳亞琴,孫 薇,朱治雙
碳市場對能源結構低碳轉型的影響及作用路徑
柳亞琴*,孫 薇,朱治雙
(山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選取中國2000~2018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構建了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基于多期雙重差分、三重差分等方法實證檢驗碳交易政策與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之間的關系及異質性影響,并進一步利用多重中介效應模型探討碳交易政策推動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作用路徑.結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可以顯著提升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水平且作用效果逐年增強.從作用路徑看,“四大效應”激勵作用彰顯,作用效果由大到小依次為結構優化效應、行為驅動效應、生態創新效應和環保支出效應;從異質性影響看,GDP增速較慢地區的政策實施加快了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影響明顯高于GDP增速較快地區;碳交易政策對東部地區的正向推動效應顯著,對中西部地區無明顯促進作用.
碳交易政策;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多重中介效應模型
能源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是我國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關鍵路徑[1].然而,當前中國煤炭消費量仍占據世界半壁江山,與多數國家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十一五”以來,中國大力加快能源消費清潔低碳轉型,持續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基本扭轉了煤炭比重長期維持在70%左右的局面[2],煤炭消費占比由2008年的72.4%下降至2020年的56.8%,但仍遠超27.2%的世界平均水平和11.2%的美國煤炭消費占比.中國亟需加快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而碳交易政策作為一種市場型環境規制手段,有助于我國通過較低的成本實現減排目標,同時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政策工具[3].基于此,本文研究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及傳導機制,對于我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低碳轉型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1 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關于能源消費結構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影響因素、變動趨勢預測和低碳化水平的測度三個方面.就能源消費結構影響因素而言,學者們普遍認為能耗強度[4]、產業結構[5]、城鎮化水平[6]、經濟發展水平[7]等因素對能源消費結構產生主要影響.就能源消費結構變動趨勢預測而言,主要關注于方法選擇,如許多學者通過馬爾科夫鏈[8]、能源消費彈性系數[9]、組合模型[10]等考察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動趨勢.其中,與單一模型相比,組合模型可以得到更精確可靠的預測結果.就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的測度方面研究而言,學界主要有以下兩種思路:一是使用單一指標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程度進行刻畫,如使用煤炭占比[11]、煤炭消費占比和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12];二是通過構建綜合指標來評估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程度,如苗陽等[13]利用AHP模型構建綜合能源結構評價體系;周四軍等[14]采用稀疏主成分分析測算地區能源高質量發展程度;李榮杰等[15]通過改進加權多維向量夾角方法構建了能源結構低碳化綜合指數.
碳交易試點政策對中國經濟和環境的影響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現有文獻對于碳交易政策的研究包括:第一,關于碳交易政策影響效應的有效性研究.多數學者認為碳交易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地區的碳排放[16],且其減排效應逐年增強[17],隨著空間計量模型的廣泛應用,學界開始將碳交易政策對鄰地產生的影響納入研究范圍.研究結果發現碳交易政策還具有一定的溢出效應抑制相鄰地區減排[18];第二,關于碳交易政策對于低碳經濟發展影響的研究.碳交易政策可助力地區整體實現綠色發展[19],并能夠通過激勵地區創新促進綠色經濟增長[20];第三,關于碳交易政策與其他方向的融合研究.胡江峰等[21]發現碳交易政策在促進企業提升創新數量的同時也可促進企業兼顧創新質量,但對于低質量創新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譚靜等[22]從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視角出發,研究發現碳交易政策對當地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倒逼”效應;還有學者證實了碳交易政策對綠色發展效率的促進效應[23-24].
碳交易政策至今試行9年之久,既往文獻深入探討了碳交易政策的治污減排效應,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關于碳交易政策對于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影響機制的研究卻極為匱乏.基于此,本文首先從生態創新、結構優化、環保支出、行為驅動4個角度提供了碳交易政策促進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驅動機制.其次,基于省級面板數據構建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運用多期DID模型,實證檢驗碳交易政策與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利用多重中介效應模型考察碳交易政策對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平行及鏈式作用路徑.最后,運用三重差分模型討論碳交易政策對不同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異質性影響.
2 理論機制
實現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是一場顛覆性的能源體系變革,不僅需要政府的頂層宏觀設計、相關政策制定,還需要企業積極響應以及公眾的參與.碳交易政策是科斯定理在政府治理環境方面的應用,該政策將會導致遵循成本最小化或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優化調整能源消費結構,長此以往還可促進各行業能源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最終推動整個地區實現能源消費結構綠色、低碳發展.基于此,參考范英等[25]對能源轉型驅動機制方面的研究,本文認為碳交易政策之所以能夠促進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水平提升,主要是存在“生態創新效應為引領、結構優化效應為內驅、環保支出效應為助推、行為驅動效應為補充”的4個重要機制.
2.1 生態創新效應
在理論層面,“波特假說”認為企業在適當的環境規制下,會傾向于從事更多技術創新研發活動,激發的“創新補償效應”能夠抵消部分甚至是全部的環境成本,從而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在現實層面,碳交易政策是一種市場型環境規制,作為逐利型主體的企業在邊際治碳成本高于邊際技術創新成本時,他們會有足夠的動機不斷改進生產技術工藝,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廣泛開展生態創新實現“綠色生產”方式變革.一方面,企業在實現清潔生產的同時還可出售富余的碳排放許可;另一方面,擁有生態創新技術的企業也可向其他高碳企業出售其自主研發的綠色技術,這兩者帶來的收益均可以緩解企業因政策帶來的附加環境成本壓力[26].短期來看,生態創新成本會加重企業負擔,但從長遠角度來看,生態創新不僅可以提高生產效率,還可降低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有利于加大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同時也有助于實現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
2.2 結構優化效應
碳交易政策的實施實際上是政府給予高污染、高能耗企業的一種信號,目的在于督促其進行低碳生產改造.一方面,在碳交易政策實施的背景下,作為“理性人”的企業會不斷地通過減排來壓縮生產成本,當開展減排的企業由點向面進行擴散時,那些不進行減排的“兩高”企業會因生產成本過高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最終被擠出市場.此外,這種優勝劣汰的淘汰機制也會使碳交易政策存在“環境壁壘”效應[27],行業準入門檻于無形中不斷提高,從而倒逼產業結構優化;另一方面,清潔產業的利潤空間隨著相關環境法規嚴苛而增大,便會誘使社會資源重新配置,致使生產要素流向清潔產業,加速產業結構優化,進而實現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
2.3 環保支出效應
環保支出作為一種特殊的工具同時具有經濟和環保雙重屬性而成為政府的重要選擇[28].其最直接的作用是改善環境狀況.另外,環保支出所體現出的政府偏好可引導一系列的非官方環保投資,間接地促進社會的環境治理[29].同時,“兩高”企業在感知到政府偏好的同時,也會積極調整原料投放或生產工藝以達到清潔生產的目標,有助于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除此之外,環保支出還可以通過影響產業結構及生態創新作用于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具體作用機理表現為:一是環保支出以一種投入型的環境規制方式對地區的技術創新產生激發作用[28];二是環保支出依靠其強烈的政策導向性引導著社會資金的集聚方向,從而有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30].
2.4 行為驅動效應
碳交易政策屬于環境規制中的正式環境規制,體現了官方治理環境的主動性.除此之外,公眾群體的力量也不容小覷,這種非正式環境規制行為目前已成為正式環境規制的重要補充[31].具體而言,公眾可能從以下兩個維度參與環保事業,一是公眾監督具有及時、高效、無利益糾葛等優點,極大程度上緩解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環境污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更好地輔助政府進行環保督查的同時施于企業更大的壓力[32];二是環保意識的提高會促使公眾在消費時傾向選擇同質產品中更具有綠色低碳特質的產品,便可“倒逼”企業開展綠色生產改革,推動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進程.進一步來說,公眾的終端需求決定了企業的生產方向,其對綠色產品的偏好可以影響企業的生產策略,直接激勵企業開展生態技術創新,研發環境友好型生產技術或“綠色”產品[33],在助力企業在市場上擁有絕對的競爭力的同時也有利于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
3 研究設計
3.1 模型設定
3.1.1 多期雙重差分模型 為了探究碳交易政策的實施能否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產生影響,本文采用多期DID方法,將碳交易試點政策視為“準自然實驗”,以各省實施碳交易政策的實際年份作為政策干預時間點,據此將研究對象分為處理組和控制組,進而對兩類地區在政策實施前后的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水平進行比較,設計模型如下:

式中:、分別表示政策實施年份和地區.gec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地區在年份的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核心解釋變量pro×time表示地區在年份是否啟動實施碳交易政策的虛擬變量,當且僅當省份在年份啟動實施碳交易試點政策時,取值為1,其他情況則取值為0,該變量的系數為待估政策凈效應,反映碳交易政策的實施對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產生的影響.X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自然資源稟賦、政府干預、城鎮化水平以及經濟活力.β為省份固定效應;θ為年份固定效應;為隨機擾動項.
3.1.2 多重中介效應模型 利用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對碳交易政策影響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中介傳導機制進行分析,引入行為驅動效應(ier)、環保支出效應(es)、結構優化效應(iso)、生態創新效應(ei)四個中介變量對其產生的平行及鏈式中介效應進行討論(圖1),模型設定如下:





式(1)用于檢驗碳交易政策影響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總效應,其中,系數1反映了碳交易政策影響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總效應,式(6)中的系數1反映了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影響的直接效應,總效應1也就是直接效應1與間接效應即中介效應之和.式(3)-(6)構成的多方程系統對四種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其中包括4條平行中介路徑和3條鏈式中介.具體來看,平行中介效應表現為“pro×time→ier→gect”、“pro× time→es→gec”、“pro×time→iso→gec”、“pro× time→ei→gec”,效應大小分別為21324354;鏈式中介效應表現為“pro×time→ier→ ei→gec”、“pro×time→es→ei→gec”、“pro× time→es→iso→gecit”,效應大小分別為224、334、313.

圖1 中介效應傳導機制
3.1.3 三重差分模型 通過引入三重交互項對碳交易政策對不同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異質性影響進行分析,本文將區域虛擬變量reg引入基準模型(1),與pro×time構成三重差分模型來探究碳交易政策在不同地區的實施效果,為全國碳交易市場的良好運行提供參考.模型設定如下:

在討論某地區時,則該地區reg取值為1,相反則為0.系數1表示碳交易政策對于某特定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影響的凈效應.
3.2 變量選取
3.2.1 被解釋變量 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gec).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是各類主導能源在替代與互補中,持續不斷地優化調整的系統性工程.它是指隨著我國加速推進能源消費清潔化,結構呈現出以綠色低碳替代高碳為特征的調整趨勢,僅僅使用煤炭或清潔能源消費占比來衡量能源消費低碳化的進程是有失偏頗的.所以,本文借鑒付凌暉[34]的方法構建了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來衡量其綠色低碳轉型進程.



最后,對年份所有向量夾角進行加權,構成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gec,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3.2.2 解釋變量 碳交易試點政策(pro×time),表示地區在年份是否啟動實施碳交易政策的虛擬變量,若地區在年開始實施碳交易政策,則pro×time取1,否則取0,其系數反映了碳交易政策的實施對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產生的影響.具體而言,上海、北京、廣東、天津于2013年實施碳交易試點政策,湖北和重慶于2014年開始實施政策,四川及福建也分別于2016年和2017年實施相應的試點政策.
3.2.3 中介變量
(1)生態創新效應(ei),即可實現經濟和環境雙重友好的技術創新,采用學界普遍使用的專利數量來衡量生態創新效應.參考曾剛等[35]的做法,利用“低碳、減排、環保、節能、可再生、生態治理、環境友好、循環利用、污染治理、清潔能源”等關鍵詞在大為innojoy專利數據庫篩選出相關發明專利的授權數.
(2)結構優化效應(iso),選取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值來表征.iso越小,說明結構優化效應越大.
(3)環保支出效應(es),使用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與GDP的比值來衡量.
(4)行為驅動效應(ier),參考首次提出非正式環境規制這一概念的Wheeler等[36]的刻畫方法,利用熵權法從人口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3個維度構建非正式環境規制綜合指數,以此衡量行為驅動效應的大小.其中,由于研究數據可得性的限制,受教育水平的衡量采取秦炳濤等[37]的方法,選取當地小學、普通中學及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總和與年底人口之和的比重來表示.
3.2.4 控制變量 設定自然資源稟賦(nre)、經濟活力(qos)、政府干預(gi)、城鎮化水平(ul)等變量作為影響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水平的控制變量,分別采取采掘業固定投資占總固定投資的比重、貨運量、地方一般預算支出與GDP的比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等指標來表征.
由于西藏及港、澳、臺地區數據缺失嚴重,本文選取2000~2018年中國30個省(市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相關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CSMAR數據庫、《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38]、大為innojoy專利數據庫、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另外,利用插值法和平均增長率法補全部分缺失數據.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4 實證分析
4.1 基準回歸結果
4.1.1 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影響分析 本文將模型(1)作為基準模型用以考察碳交易政策影響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實際效應,為了使研究結論更具穩健性,之后逐步加入地區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及控制變量,具體檢驗結果如表2的第(1)~(3)列所示.檢驗結果顯示:在上述三種檢驗條件下,核心解釋變量pro×time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這表明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對試點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以第(3)列回歸結果為例,碳交易政策的實施會使得地區能源消費低碳化水平提升17.1%.
4.1.2 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DID方法來估計結果的前提條件是實驗組和控制組要滿足平行趨勢假定,即碳交易政策實施之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保持相對穩定的變動趨勢.上述基準分析得出的是在一段時間內政策實施對于各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影響的平均效應,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加嚴謹,本研究引入平行趨勢檢驗模型,進一步分析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動態影響.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由圖2知,政策執行之前年份的pro×time系數的置信區間均包含0,系數也均不顯著,這說明在2013年以前,政策試點省份與政策非試點省份不存在顯著差異,滿足平行趨勢假定.2013年政策執行后,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并呈現出向右上方傾斜的趨勢,這說明了碳交易政策的實施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起到了誘發的作用,且作用效果逐年增強.
4.1.3 安慰劑檢驗 為排除其他不可知因素對研究結論的干擾,驗證碳交易政策促進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實際影響效應,采用了在所有樣本中隨機設置若干次虛擬實驗組的安慰劑檢驗.首先,在30個地區隨機抽樣得到“偽處理組”;其次,將此抽樣過程重復500次并進行回歸;最后,便得到500次回歸結果.本文將500次回歸產生的“偽政策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分布以及其值繪制于圖3中,從圖中可以看到,真實估計系數明顯偏離“偽政策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分布,相應值也主要集中在0.1,這意味著在10%的水平下不顯著.由此,表明本文得到的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偶然性,即可以排除其他政策或者隨機性因素對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影響.

圖2 平行趨勢假設的動態效應
實線部分表示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邊際效應,虛線部分表示95%的置信區間范圍

圖3 安慰劑檢驗
軸反映的是具體的分布密度值及值,軸反映的是“偽政策虛擬變量”待估系數值,圖中圓點代表了待估系數相對應的值,曲線表征了估計系數的核密度分布狀況
4.2 穩健性檢驗
4.2.1 擴大處理組 除上文研究的8個試點省份之外,深圳市作為全國首個正式啟動碳排放交易試點的城市,于2013年6月18日正式上線交易.為了使研究結論更具穩健性,本節將深圳市的各項數據從廣東省剝離出來后擴大實驗處理組進一步分析.研究結果如表3所示,回歸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時間固定效應及地區固定效應,pro×time的估計系數仍正向顯著,這與前文回歸結果相一致,再次驗證了碳交易政策可以顯著促進試點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

表3 擴大處理組后的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表4 政策執行時間調整后的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4.2.2 政策執行時間 考慮到上海、北京、廣東、天津及四川地區實施碳交易政策的時間接近于當年年末,可能會影響其政策在正式實施年份的執行效果.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具可靠性,本節將這些地區的政策實施時間調整至其政策正式實施的次年后重新檢驗.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pro×time系數仍顯著為正,說明碳交易政策的推行是試點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動力,進一步證明上文研究結論的可信性.
4.3 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影響機制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作用機理,運用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將生態創新效應、結構優化效應、環保支出效應、行為驅動效應作為中介變量進行研究.首先,運用逐步回歸法對模型(2)~(6)的中介變量進行檢驗;其次,當逐步回歸法失靈時,對模型進行bootstrap檢驗,若中介變量通過該檢驗,則證實存在多重中介效應;最后,利用各中介變量的bootstrap檢驗結果對其傳導路徑進行深入分析.
4.3.1 逐步檢驗法 表5中的第(2)(4)(5)列的回歸結果顯示,pro×time的估計系數均顯著,說明了碳交易政策的實施引發了生態創新效應、環保支出效應及行為驅動效應,即碳交易政策在驅動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過程可能存在中介效應.此外,借助溫忠麟等[39]的研究方法,對結構優化效應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發現結構優化效應通過了bootstrap檢驗,說明結構優化效應的中介效應存在.另外,第(6)列的pro×time回歸系數表示,碳交易政策對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影響存在直接效應(0.082);第(1)列的pro×time回歸系數表示,碳交易政策對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存在著顯著的正向總效應(0.171)影響.進一步分析發現,第(1)列的總效應大于第(6)列的直接效應,這說明存在間接效應,即碳交易政策推動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進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表5 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的影響機制檢驗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4.3.2 Bootstrap檢驗法 表6為碳交易政策驅動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過程中的傳導機制.可以發現,碳交易政策通過生態創新效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環保支出效應及行為驅動效應間接地推動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其中介效應之和即總中介效應為0.142.

表6 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的多重中介效應機制檢驗
注:***、**、*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數字是運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中介效應置信區間,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示顯著.
①生態創新效應的中介效應.生態創新效應單獨發揮顯著的正向平行中介效應即碳交易政策→生態創新→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41),占總中介效應的28.88%.這說明了生態創新為實現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注入了不竭的動力,碳交易政策通過倒逼企業進行生態創新以實現生產成本最小化,從而有助于地區實現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
②結構優化的中介效應.結構優化效應同生態創新效應一樣發揮著平行的中介效應即碳交易政策→結構優化效應→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57),占總中介效應的40.15%.這說明了碳交易政策的實施給重污染高能耗的企業帶來了生存壓力,運營成本的提高倒逼企業轉型,產業結構得到持續優化升級進而促進地區能源消費結構實現低碳轉型.
③環保支出效應的中介效應.首先,碳交易政策通過環保支出效應本身影響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即碳交易政策→環保支出效應→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25),可能原因是直接作用于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環保支出由于資金使用效率不足,導致未能有效發揮作用;其次,環保支出一方面憑借其政策導向性調動著各類生產要素向綠色清潔產業集聚,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另一方面以資金援助的方式縮減企業交易成本,激發企業開展更多的生態創新研發活動.由此產生兩條鏈式中介效應即碳交易政策→環保支出效應→結構優化效應→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17)、碳交易政策→環保支出效應→生態創新效應→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10).環保支出效應的累積中介效應為0.002,占總中介效應的1.41%.
④行為驅動效應的中介效應.碳交易政策在影響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中存在著顯著的行為驅動效應,該效應累計發揮的中介效應為0.042,其占總效應的29.56%.具體來看,包括碳交易政策→行為驅動效應→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36)的平行中介效應,以及碳交易政策→行為驅動效應→生態創新效應→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06)的鏈式中介效應.其中,行為驅動效應的平行中介效應作用力要大于其鏈式中介效應.以上結果表明,碳交易政策作為正式環境規制不僅可以通過影響公眾的綠色消費行為促進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還可以通過影響公眾對綠色消費理念的認同從而助推企業進行生態創新以實現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
綜上所述,在碳交易政策驅動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過程中,以上4種主要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貢獻度最大的是結構優化效應,最小的是環保支出效應,行為驅動效應和生態創新效應依次次之.具體分析各傳導路徑可以得出,碳交易政策→結構優化效應→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指數(0.057)這條路徑的中介效應最大,究其原因是我國目前最大的能源消耗主體是第二產業,碳交易政策的實施可以激勵地區高污染高能耗企業開展清潔能源的使用以及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由此可以有效降低地區能耗強度,推動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
4.4 異質性分析
4.4.1 經濟發展程度異質性分析 以30個省市GDP增速平均值的中位數為依據將研究樣本劃分為2類,即GDP增速較快地區和GDP增速較慢地區,以此考察碳交易政策在經濟發展程度相異地區的實施效果.表7顯示了兩類地區的三重差分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變量以及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的情況下,GDP增速較慢地區的碳交易政策可以顯著促進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政策的實施可使GDP增速較慢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水平提高36.4%,與之相對比來看,碳交易政策對GDP增速較高地區的作用效果較差,究其原因是我國經濟正邁向新的發展階段,各地區GDP增速都進入了減檔期,但對于GDP增速較快的地區來說,這些地區工作要務還是在于著力提升經濟總量,存在通過給環境約束力松綁換取經濟增長的現實問題[40],處于環境庫茨涅茲曲線的上升階段[41],即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環境污染,所以會對碳交易政策的紅利釋放有一定的阻礙作用,使得該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諸如北京、上海這類GDP增速較慢地區已經步入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先導期,較好地完成了經濟動力的轉化,努力踐行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雙贏,為碳交易政策的有效實施營造出較為優越的外部條件,因而這些地區的碳交易政策效果得到充分顯現.

表7 經濟發展異質性的三重差分估計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4.4.2 區域異質性分析 按照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30個省份劃分為東部、中部及西部,以此來探索碳交易政策實施效果的區域異質性差異.具體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碳交易政策的正向推動效應主要體現在東部地區,對中部及西部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雖然也存在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效果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其中原因可能在于湖北作為中部地區的唯一試點地區,其經濟發展對第二產業依賴程度較高,同時考慮到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之間的平衡關系,市場懲處力度也相對薄弱.此外,湖北碳交易市場還存在“為交易而交易”的虛假繁榮現象[40],由此致使政策作用效果不顯著.而西部地區仍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機遇期,能源消耗量較大.除此之外,重慶碳交易市場發育度較差,市場活躍度不足,同時還存在對未完成履約企業的處罰力度較弱導致市場有效性不足的問題[42],加之四川的碳交易政策實施較晚,其政策效果可能在本文研究時間段中未完全顯現,從而西部地區碳交易政策的實施未能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產生較為明顯的推動作用.

表8 區域異質性的三重差分估計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顯著.
5 結論與建議
研究發現:(1)碳交易政策的實施顯著地提升了試點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水平,且政策效應逐年增強.通過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仍然成立.(2)對碳交易政策影響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傳導機制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碳交易政策可以通過生態創新效應、結構優化效應、環保支出效應及行為驅動效應以平行或鏈式傳導機制對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產生影響.其中,生態創新效的中介效應占比為28.88%,結構優化效應占比為40.15%,環保支出效應占比為1.41%,行為驅動效應占比為29.56%.(3)異質性分析發現,GDP增速較慢地區的碳交易政策對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的作用效果明顯高于GDP增速較快地區;碳交易政策對東部地區能源消費結構低碳轉型產生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而對中部及西部地區而言,碳交易政策雖然存在正向作用力,但作用效果并不顯著.
針對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著力完善碳交易市場運行機制,針對不同地區制定差異化政策.對不同地區的現實狀況要做到“量體裁衣”,對于著力發展經濟以實現基本發展目標的地區,要考慮當地經濟和環境的耦合度,溫和地推進政策的實施力度以便更好地發揮政策效果.
(2)助力企業廣泛開展生態創新活動,激發低碳化生產的內在動力.政府應著力為全社會培育滋養創新的肥沃土壤,對積極進行低碳技術創新的企業予以補貼和獎勵.同時,還要加大力度消除科技成果轉化障礙,促使科技成果可以實現低成本轉化以及生態創新技術的普遍推廣.
(3)引導高碳產業開展綠色低碳轉型,嚴格控制高碳產業無度擴張.要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二高”產業的準入門檻,及時淘汰落后的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另外,在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過程中,要針對不同的產業問題進行循序漸進式調整,切忌發生“運動式”調整而致使整個社會發展陷入困境.
(4)建立健全環保資金專項配置體系,促進環保資金使用效率提升.政府應建立合理的環保資金配置體系,嚴格審批環保資金,確保環保資金流向環境治理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幫助企業克服環境治理過程中的難題.同時,還要設立環保資金實時動態監管機制,確保資金使用落到實處.
(5)加強全社會綠色發展理念的宣傳,鼓勵公眾踐行低碳生活理念.政府應充分利用好公眾自發產生的力量,引導公眾樹立低碳發展觀,積極倡導綠色低碳生活理念和消費行為.此外,還應拓寬公眾參與環保事業的渠道,鼓勵公眾對企業的各種不良環保行為進行多方位監督,同時建立公眾與相關環保部門的良好互動機制以解決政府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1] 徐 政,左晟吉,丁守海.碳達峰、碳中和賦能高質量發展:內在邏輯與實現路徑[J]. 經濟家, 2021,(11):62-71.
Xu Z, Zuo C J, Ding S H.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ity Empow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J]. Economist, 2021,(11):62-71.
[2] 李俊峰,李 廣,中國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問題回顧與展望[J].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2020,45(5):8-17.
Li J F, Li G. Review and prospect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0,45(5):8-17.
[3] 范秋芳,張園園.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對碳生產率的影響研究[J]. 工業技術經濟, 2021,40(12):113-121.
Fan Q F, Zhang Y Y.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on Carbon Productivity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1,40(12):113-121.
[4] 周彥楠,何 則,馬 麗,等.中國能源消費結構地域分布的時空分異及影響因素[J]. 資源科學, 2017,39(12):2247-2257.
Zhou Y N, He Z, Ma L,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hina's provincial scal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J]. Resources Science, 2017,39(12):2247-2257.
[5] Xia C X, Wang Z. Drivers analysis and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based forecasting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254(C):120107.
[6] 王風云,蘇燁琴.京津冀能源消費結構變化及其影響因素[J]. 城市問題, 2018,(8):59-67.
Wang F Y, Su Y Q. Chang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 Urban Problems, 2018,(8):59-67.
[7] 張倩倩,李百吉.基于路徑分析法的能源結構影響因素效應分析與政策優化[J]. 企業經濟, 2017,36(8):11-17.
Zhang Q Q, Li B J. Effect analysis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of energy structure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path analysis method [J]. Enterprise Economy, 2017,36(8):11-17.
[8] 翁智雄,馬忠玉,葛察忠,等.不同經濟發展路徑下的能源需求與碳排放預測——基于河北省的分析 [J]. 中國環境科學, 2019,39(8): 3508-3517.
Weng Z X, Ma Z Y, Ge C Z, et al. Projection on energy demand and carbon emission in various economic developing pathways——A case study in Hebei province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39(8): 3508-3517.
[9] 李洪兵,張吉軍.中國能源消費結構及天然氣需求預測[J]. 生態經濟, 2021,37(8):71-78.
Li H B, Zhang J J.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forecast on natural gas demand [J]. Ecological Economy, 2021,37(8):71-78.
[10] 謝小軍,邱云蘭,時 凌.基于ARIMA和BP神經網絡組合模型的能源消費預測[J]. 數學的實踐與認識, 2019,49(10):292-298.
Xie X J, Qiu Y L, Shi L. Predic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based on ARIMA and BP neural network combined model [J]. Mathematic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2019,49(10):292-298.
[11] Liu Y Q, Zhao G H, Zhao Y 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provinci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efficiencies based o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J]. Energy Policy, 2016,96:524-533.
[12] Xu G Y, Peter Schwarz, Yang H. Adjusting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o achieve China's CO2emissions peak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20,122:109737.
[13] 苗 陽,邢文杰,鮑健強.城市能源結構低碳化指標體系及實現路徑研究[J]. 生態經濟, 2016,32(5):53-57.
Miao Y, Xing W J, Bao J Q. Low-Carbo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Urban Energy Structure and Its Attainment [J]. Ecological Economy, 2016,32(5):53-57.
[14] 周四軍,戴思琪.長江經濟帶能源高質量發展的測度與聚類分析 [J]. 工業技術經濟, 2020,39(10):116-124.
Zhou S J, Dai S Q. Measurement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0,39(10):116-124.
[15] 李榮杰,李 娜,張 靜,等.地區能源結構低碳化差異的收斂機制及影響因素——基于加權多維向量夾角指數 [J]. 統計與信息論壇, 2020,35(10):90-99.
Li R J, Li N, Zhang J, et al. Regional Differences Convergence of Low-carbon Energy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Weighted Multi-Dimensional Vector Angle [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20,35(10):90-99.
[16] 曾詩鴻,李 璠,翁智雄,等.碳市場的減排效應研究——來自中國碳交易試點地區的經驗證據[J]. 中國環境科學, 2022,42(4):1922-1933.
Zeng S H, Li P, Weng Z X, et al. A Study of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Carbon Marke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ilot Carbon Trading Regions in China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42(4):1922-1933.
[17] 董直慶,王 輝.市場型環境規制政策有效性檢驗——來自碳排放權交易政策視角的經驗證據[J]. 統計研究, 2021,38(10):48-61.
Dong Z Q, Wang H. Validation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ies [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21,38(10):48-61.
[18] 李若男,楊力俊,趙曉麗.基于空間模型的中國碳交易減排效果分析[J]. 全球能源互聯網, 2021,4(5):486-496.
Li R N, Yang L J, Zhao X L.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Based on Spatial Model Analysis [J].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2021,4(5):486-496.
[19] 任亞運,傅京燕.碳交易的減排及綠色發展效應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9,29(5):11-20.
Ren Y Y, Fu J Y.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29(5):11-20.
[20] 廖文龍,董新凱,翁 鳴,等.市場型環境規制的經濟效應:碳排放交易、綠色創新與綠色經濟增長[J]. 中國軟科學, 2020,(6):159-173.
Liao W L, Dong X K, Weng M, et al. Economic Effect of Market- orien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Green Innovation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J]. China Soft Science, 2020,(6):159-173.
[21] 胡江峰,黃慶華,潘欣欣.碳排放交易制度與企業創新質量:抑制還是促進[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20,30(2):49-59.
Hu J F, Huang Q H, Pan X X.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and firms’ innovation quality: suppression or promo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30(2):49-59.
[22] 譚 靜,張建華.碳交易機制倒逼產業結構升級了嗎?——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分析[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8,39(12):104-119.
Tan J, Zhang J H. Does China’s ETS Force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Evidence from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J].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39(12):104-119.
[23] 孫振清,李歡歡,劉保留.碳交易政策下區域減排潛力研究——產業結構調整與技術創新雙重視角[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20,37(15):28-35.
Sun Z Q, Li H H, Liu B L. Research on reg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under carbon trading policy: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20,37(15):28-35.
[24] 任曉松,馬 茜,劉宇佳,等.碳交易政策對工業碳生產率的影響及傳導機制[J]. 中國環境科學, 2021,41(11):5427-5437.
Ren X S, Ma Q, Liu Y J, et al. The impact of carbon trading policy on industrial carbon productivity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41(11):5427-5437.
[25] 范 英,衣博文.能源轉型的規律、驅動機制與中國路徑[J]. 管理世界, 2021,37(8):95-105.
Fan Y, Yi B W. Evolution, Driving Mechanism, and Pathway of China’s Energy Transition [J]. Management World, 2021,37(8):49-55.
[26] Lanoie P, Patry M, Lajeunesse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8,30(2):121-128.
[27] 李 強,丁春林.環境規制、空間溢出與產業升級——來自長江經濟帶的例證 [J]. 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25(1):17-28.
Li Q, Ding C 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patial spillover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vidence from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25(1):17-28.
[28] 姜 楠.環保財政支出有助于實現經濟和環境雙贏嗎? [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8,(1):95-103.
Jiang N. Does Environmental Fiscal Expenditure Help Achieve a Win-Wi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18,(1):95-103.
[29] 田淑英,董 瑋,許文立.環保財政支出、政府環境偏好與政策效應——基于省際工業污染數據的實證分析 [J]. 經濟問題探索, 2016,(7):14-21.
Tian S Y, Dong W, Xu W L. Environmental Fiscal Expenditur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and Policy Effe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Industrial Pollution Data [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6,(7):14-21.
[30] 杜雯翠.環保投資、環境技術與環保產業發展——來自環保類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15(3):47-53.
Du W C.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Environmental Listed Companies [J].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15(3):47-53.
[31] 張 華,馮 烽.非正式環境規制能否降低碳排放?——來自環境信息公開的準自然實驗 [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20,41(8):62-80.
Zhang H, Feng F. Does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J].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0,41(8):62-80.
[32] 郭 進,徐盈之.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邏輯、路徑與效應 [J]. 資源科學, 2020,42(7):1372-1383.
Guo J, Xu Y Z. The logics, paths, and effec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J]. Resources Science, 2020,42(7):1372-1383.
[33] 盛光華,龔思羽,解 芳.中國消費者綠色購買意愿形成的理論依據與實證檢驗——基于生態價值觀、個人感知相關性的TPB拓展模型 [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9,59(1):140-151,222.
Sheng G H, Gong S Y, Xie F.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test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onsumers'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 TPB expansion model based on ecological values and personal perception correlation [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59(1):140-151,222.
[34] 付凌暉.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J]. 統計研究, 2010,27(8):79-81.
Fu L H.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dustry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10,27(8):79-81.
[35] 曾 剛,陸琳憶,何金廖.生態創新對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與工業綠色效率的影響[J]. 資源科學, 2021,43(1):94-103.
Zeng G, Lu L Y, He J L. Impact of ec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J]. Resources Science, 2021,43(1):94-103.
[36] Wheeler D, Pargal S. Inform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04(6):1314-1327.
[37] 秦炳濤,余潤穎,葛力銘.環境規制對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 [J]. 中國環境科學, 2021,41(7):3427-3440.
Qin B T, Yu R Y, Ge L M.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41(7):3427-3440.
[3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 [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Compendium of statistics data 1949~2008 [M]. 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0.
[39]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 [J]. 心理科學進展, 2014,22(5):731-745.
Wen Z L, Ye B J.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2(5):731-745.
[40] 易 蘭,李朝鵬,楊 歷,等.中國7大碳交易試點發育度對比研究 [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8,28(2):134-140.
Yi L, Li C P,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China’s 7pilot carbon markets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28(2):134-140.
[41] 包 群,彭水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基于面板數據的聯立方程估計 [J]. 世界經濟, 2006,(11):48-58.
Bao Q, Peng S J.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imultaneous Equation Estim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06,(11):48-58.
[42] 余 萍,劉紀顯.碳交易市場規模的綠色和經濟增長效應研究 [J]. 中國軟科學, 2020,(4):46-55.
Yu P, Liu J X.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arbon Trading Market Size 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J]. China Soft Science, 2020, (4):46-55.
The impact of carbon market on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energy mix and its action path.
LIU Ya-qin*, SUN Wei, ZHU Zhi-sh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2022,42(9):4369~4379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to construct the low-carbo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dex, and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and heterogeneity between carbon trading policy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using multi-period double difference and triple difference method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carbon trading policy on the low-carbo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by using multipl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rbon trading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ow-carbon level of reg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effect keep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four major effects” is obvious, and the effect from large to small i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effect, behavior-driven effect, ec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in regions with slower GDP growth has accelerated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impa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regions with faster GDP growth; carbon trading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astern region,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arbon trading policy;low-carbon transi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s model
X820.3
A
1000-6923(2022)09-4369-11
2022-01-1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210311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7YJCZH115)
*責任作者, 副教授, liuyaqin2003@126.com
柳亞琴(1981-),女,山西柳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能源經濟與能源政策研究.發表論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