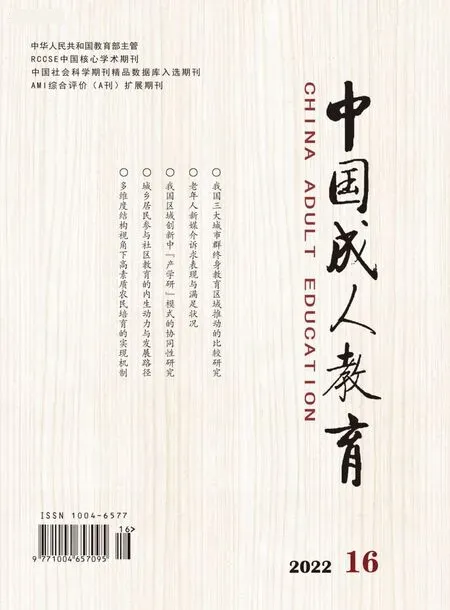我國區域創新中“產學研”模式的協同性研究
○劉 濤 崔怡心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創新驅動,推動產學研結合和技術成果轉化,強化對創新的激勵和創新成果的應用[1]。產學研協同發展的關鍵在于提高產學研耦合程度,加強合作主體之間的交流與互動[2]。通過深化產學研協同發展,加速創新體系內的資源流動、信息共享和知識擴散,克服單一主體獨立創新面臨的資金、技術、人才困境,充分發揮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的優勢和作用,帶動區域創新系統的演化升級,最終推動社會整體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然而,在產學研協同發展實踐中,由于企業、高校、研究機構三類創新主體間的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異[3-4],使得產學研協同發展的可持續性及規模受到制約,進而增大區域創新的成本及風險,影響區域創新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我國區域間的經濟條件、政策紅利、資源配置等方面各有差異,創新效率存在區域差異[5],從而使得區域間產學研協同創新發展不平衡[6]。因此,在區域創新背景下對產學研模式的協同性研究,可以發現區域產學研協同發展中的差異及不足。通過三類主體的互補協調并形成合力,更好地推動區域創新,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現有研究對產學研耦合協調的機理、協同作用及協調狀態已進行了較為詳盡的闡述,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敦實的理論基礎。但少有學者從阻礙度這一視角來具體辨析產學研協同發展過程中的阻礙因素,來明確其中的哪些因素阻礙了產學研的良性協調。因此本文在創新資源流通順差的基礎上厘清了產學研創新系統的耦合協調機理,構建了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三大子系統創新能力指標評價體系,以求為提升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的創新能力及協同發展水平提供一定的科學依據與經驗參考。
一、指標體系、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指標選取
在楊偉等[7]和劉偉等[8]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兼顧子系統間指標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從創新投入與產出等方面選取了15個代表產學研創新系統發展水平的一級指標構建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所列。

表1 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指標評價體系
(二)指標與耦合協調度測算
本文選用熵值法來計算產學研創新系統中的各項子指標的權重,具體測算步驟參考徐延利等[9]的做法,在確定各指標權重后,通過加權得到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的得分u1、u2、u3,根據耦合模型計算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三大創新子系統間的耦合度,其公式為:

其中,C代表三個子系統間的耦合度。此外,由于耦合度指標反映的主要是各子系統間的相似性,難以體現出三者之間協調發展程度[10],且耦合度指標在評價時容易出現序參量較小而耦合度較高的情況[11]。因此,為了更好地展現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本文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耦合協調度模型,從而更好地分析產學研三個子系統間的協同發展程度。計算如下:

D為產學研創新系統的耦合協調度,T則代表三個子系統的綜合發展度。其中a、b、c分別為產、學、研創新發展能力的待定系數,代表子系統對系統層的貢獻度,a+b+c=1。由于本文試圖探究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三個創新子系統之間的真實協同狀況,三者皆為產學研創新系統中重要的轉換節點,各自承擔著內部鏈接系統、外部資源交流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將a、b、c均設置為1/3。為了展現全國及各省、市、自治區的耦合協調狀況,參考王偉等的做法,將產學研創新系統的耦合協調類別劃分為低度耦合協調(0<D≤0.3)、中度耦合協調(0.3<D≤0.5)、高度耦合協調(0.5<D≤0.8)與極度耦合協調(0.8<D≤1)[12]。
此外,在產學研創新系統的評價過程中,不僅要對各子系統的創新水平進行測度,也需要辨析在產學研協同發展中的阻礙因素。因此本文借鑒范斐等[13]的方法建立阻礙評價模型,從而進一步確定影響產學研創新系統協同發展的因素。
(三)數據來源
由于港澳臺地區部分指標數據缺失,因此本文沒有將其加入測度范圍。本文將研究對象定為2009—2020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數據來源于EPS全球統計數據庫、《中國科技統計年鑒》、《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
二、實證測度
(一)產學研創新水平測度與分析
基于表1和圖1可以看出,2009—2011年產學研創新系統的耦合協調度低于3,處于低度耦合階段;從2014年開始,三個子系統之間開始進入中度耦合協調階段。這是由于樣本期初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創新發展水平處于一個較低的狀態,但隨著2010年中國大型企業開始將研發創新作為戰略發展目標,不斷擴充研發人員團隊、增加R&D項目申請以及加大經費投入,發展態勢與持續增長的高校創新水平保持相對一致,因此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能夠保持一個持續上升的態勢。但其中科研機構子系統的增幅較緩,存在方位模糊、定位不清的問題。

圖1 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變化趨勢
對企業來說,研發人員強度(0.253)與R&D經費支出(0.269)等創新投入能力對其長期發展水平貢獻最大,反映出了在現階段企業發展模式向“創新驅動”轉變的過程中加強企業創新活動中的人才儲備以及研發資金投入是提升企業創新發展水平的重要措施。通過計算各省、市、自治區2009—2020年企業創新發展水平評價指數可以看出,企業創新發展水平除2010年有小幅回落以外,在樣本期內基本處于穩定上升的態勢。此外,R&D項目申報等創新投入的快速增長也對企業創新能力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知識儲備,提高了企業研發活動的基礎實力,增加了企業的創新產出。
相比于企業的逐利性而言,高校與科研機構則是創新成果與創新人才的孵化基地。課題數(0.231)與論文發表數(0.272)對高校創新發展水平的影響最為顯著;研發人員數(0.250)與論文發表數(0.220)則是科研機構創新發展水平的主要影響因素。表明科研成果導向型的發展模式是實現高校與科研機構創新水平提升的關鍵一環。樣本期內高校發展水平從2009年的0.122增長到2020年的0.281,反映出了近年來高校通過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推進優質資源建設共享、提高人才培養標準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高校創新人才的補充以及創新實力的增強。相比而言,科研機構的創新發展水平較高校而言尚存在差距,科研機構的資金與政策扶持力度較低,人才儲備量相對匱乏,因此創新活動與創新能力稍顯不足。但總體上升的態勢反映出了近年來高校與科研機構創新環境的優化創新潛力的提升在我國區域創新系統中的貢獻度逐步增強。對比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創新發展水平后,可以看出高校在產學研創新系統中處于主導地位。這主要是在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高校的人才與智力優勢使得近年來教育服務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匹配度與貢獻率逐步提升,教育成果滿足國家與地方發展的戰略需求度、學科鏈與產業鏈對接程度逐年提高,故而成為區域產學研系統中的核心力量。
(二)影響因素分析
從圖2中可以看出,在樣本期內阻礙度排名第一的子系統序參量為高校創新發展水平,這表明高校創新活動是產學研協同發展的最大阻礙。可能的原因:相比于企業而言,高校的創新活動具有更強的社會性,其課題申報與成果產出更多地服務于區域性發展戰略與重點社會性問題,多為現實意義較強的實質性創新,但同時也會受到科研經費、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制約,由此帶來的創新激勵的欠缺會導致高校創新數量較低;相比科研機構而言,科研機構的創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專識性較強的基礎性研究,而高校創新活動為了迎合地方經濟的需要,更多地表現為通識性較強的應用性研究,不免會造成創新成果魚龍混雜、創新質量良莠不齊的現象。因此,高校創新活動在數量和質量上處于相對的劣勢地位。此外,經濟下行壓力下就業市場的日趨飽和與高校畢業生屢創新高間的矛盾、科技基礎與科技環境競爭等因素都會導致高校對產學研協同發展的阻礙程度較高。但隨著近年來國家“雙一流”高校建設方案落地、高校科研水平的日益提高,樣本期內高校創新活動的阻礙度不斷下降。

圖2 產業、高校、科研系統序參量的阻礙度變化
企業的阻礙度介于二者之間,其創新活動主要是以盈利為目的一種策略性創新,通過其創新活動的數量而非質量去迎合財稅扶持政策,以獲得更多的研發補貼與稅收優惠。由此帶來的創新成果多為研發周期較短、技術含量較低、對企業乃至區域綜合價值提升貢獻較小的非發明型創新專利。因此相比于科研機構,在企業逐利性的影響下,其創新活動對產學研創新系統協調發展的影響較大。而科研機構的政策紅利與目標導向較為單一,較多地從事航天、軍事等國家核心技術的研發活動,其創新產出雖“稀”但“貴”,因此其創新發展水平始終保持一個較低的比重,在產學研協同創新系統中的阻礙度較低。但從二者變動趨勢來看,企業創新活動“保量不保質”的現象與科研機構在產學研系統中的日益脫節等現象,都使得二者的阻礙度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
三、時空分異特征分析
(一)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研發能力演化
為了將各省份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創新發展水平可視化,本文選取2009年與2020年三個時間截面來展示各省份子系統的創新發展水平得分(圖3)。2009年企業創新發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江蘇、浙江、山東與上海,其他得分較高的省份也多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省份。經過十余年的發展,2020年企業創新發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江蘇、浙江、山東與北京。此外,安徽、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的企業創新發展水平也都達到了0.15以上,從中下游逐步躋身至中上游行列。而企業創新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多分布于西南、西北等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的地區。

圖3 中國產學研系統研發能力演化
2009年高校創新發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江蘇、上海、湖北、廣東,且得分超過0.2的省份多為“雙一流”高校與優質教育資源聚集的東部地區,相比而言,西部地區的得分較低。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省份為北京、江蘇、廣東、上海、浙江。青海、西藏等西部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區域得分不足0.1,兩極分化現象嚴重。
2009年科研機構創新發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上海、陜西、江蘇、四川。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依舊為這五個省份,只有內部排序發生了變化。由于科研機構的設立與高校等教育資源分布相關性較高,因此除教育資源優勢區外,其余地區科研機構創新發展水平的兩極分化現象更為嚴重。西部地區如青海、西藏等省份得分均不足0.01。
綜合來看,在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企業的創新發展水平增速較快,得分呈現出東、中、西由高至低的階梯型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分布相近。但隨著《中部經濟崛起計劃》的提出,東、中部地區的差距逐步縮短。高校創新發展水平的基數較高,且呈不斷發展的態勢,但由于教育資源分布等先天因素的存在,兩極分化程度較大。科研機構創新發展水平相較于企業與高校更低,發展滯緩,且區域間差異更加明顯。
(二)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演化分析
根據前文耦合協調度的測算模型,得到2009—2020年我國各省市及自治區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的測算結果。通過表2可以看出,樣本期內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總體呈波動上升的趨勢。這表明,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中,我國各省市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創新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不斷提高。但除了像北京、江蘇、廣東、上海、浙江、山東等經濟發達省份的耦合協調度處于較高水平外,其他省份耦合協調度基本都處于中低度耦合協調區間,且區域間差距較大。其中,北京的產學研創新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最高,且根據子系統得分來看屬于“高校——科研機構驅動型創新系統”。這是由于作為首都的北京匯聚了全國多數“雙一流”重點高校與科研機構,具有雄厚的國內外科研團隊與創新動力;中關村產業園區以及國家名企總部的存在也為一批批創新型企業的孵化與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營商環境,知識、人才、技術、資金能夠實現良好的溝通與融合,從而實現了產學研創新系統的良好耦合。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份是我國的傳統經濟強省,多位于東部及東南沿海地區,民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企業在產學研創新系統中占據較大比重,屬于“產業——高校驅動型創新系統”。排名次之的四川、湖北、陜西等省市則憑借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建立了多所重點高校,教育資源豐富,因此屬于“高校驅動型創新系統”。排名墊底的省份有西藏、寧夏、青海,耦合協調度在0.01至0.11之間,屬于低度耦合狀態。這三個省份的產業結構單一且多以第一產業為主,創新性企業孵化平臺較少,且少有重點高校與研究機構來培育研發人員,人才引進政策力度不足,因此產學研協同發展的狀況并不理想。

表2 2009—2016年各省市及自治區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
為了可視化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特征,通過圖4展示樣本期內各省市耦合協調度的階段劃分,可以明顯地看出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同樣呈現東部最強、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階梯型分布。縱向來看,處于低度耦合協調的地區數在不斷減少,中度、高度耦合協調的地區數逐步增加。橫向來看,屬于高度耦合協同的省市全部位于東部,到2017年,東部地區已無低度耦合協調地區,到2019年,已有一半的省市躍居高度耦合協調階段。中部地區在2011年實現了中度耦合協調地區“零”的突破,而隨著中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到2016年已有36.4%的省份達到了中度耦合協調。西部地區耦合協調度增長趨勢滯后于中部地區,且具有兩極分化趨勢。自2011年陜西與四川兩個地區達到中度耦合協調狀態后,隨后的7年時間其分布狀態保持不變,直到2018年重慶市成為第三個中度耦合協調地區。其余自然條件比較惡劣、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的省份耦合協調度增長緩慢,基本都處于低度耦合協調狀態。

圖4 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狀態
(三)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阻礙度演化分析
圖5展示了我國三大經濟區產學研協同發展的阻礙度變化。可以看出中部與西部地區的阻礙度分布及變動趨勢與全國平均水平及走勢相對一致,即高校子系統的阻礙度最高、企業次之、科研機構最低。這是由于中西部地區的教育資源與人才流動較東部地區而言還具有較大差距,且教育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因此高校的創新活動仍舊是中西部地區的主要阻礙因素。反觀東部地區,在近年來高校子系統的阻礙度在樣本期內有明顯的降低趨勢,而企業與科研機構子系統的阻礙度在逐步提高。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流入高校的教育投入與科研資金越來越多,且東部地區的高校數量更多、人才流動與學科交流更加頻繁,因此高校在產學研協同創新系統中的積極作用日趨增大。同樣的,東部地區民營經濟更為發達,而企業創新具有較強的逐利性,因此其創新行為中“策略性”創新占比較大,不利于產學研協同發展。而科研機構則較多地從事科技導向型創新和活動,研發投入以及創新成本較高,從而更容易在產學研創新系統中出現脫節,不利于產學研內部的協作聯動。

圖5 東、中、西部地區產學研系統序參量的阻礙度變化
本文在構建產學研三大子系統創新能力指標評價體系的基礎上,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與阻礙度模型對我國各省市及自治區產學研子系統的研發能力、系統耦合協調度及其中的阻礙因素進行了研究。整體而言,我國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的研發能力與協同狀態在穩步提升,但仍有較大發展空間。首先,重視阻礙度排名第一的企業部門的創新活動,其中應重點關注創新投入層面,如改革研發型人才培養模式以及加大研發項目的執行力度等;在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同時,利用知識與資金順差加強企業與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對接,提高企業“實質性”創新的自主性,將知識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其次,針對區域間階梯化、極差化的分布差異,要打破資源壁壘,根據各地區特有的優質資源發展區域間創新發展聯盟。此外,中西部地區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同時,應著重關注創新型企業的培育與扶持;東部地區則應重點關注科研機構的經費支持與政策保障,促進其研發能力與企業、高校間良性協調。最后,政府與市場監管部門要為產學研協同發展建立起適宜的發展秩序。政府部門應通過相關的法律法規與政策扶持保障高校、科研機構中科研人員的合法權益,并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市場監管部門則應注重創新型專利與產權的保護,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引導市場良性競爭,從而實現“知識—科學—技術—產業—市場”的路徑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