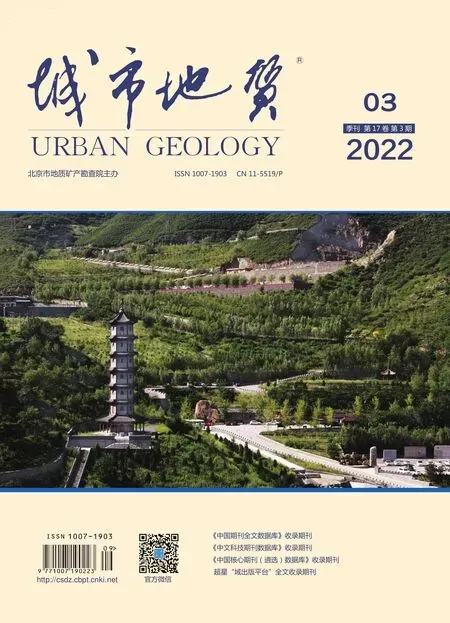數據的背后
——北京市鐵礦資源戰略儲備淺析
馬海全,鄭琴,龍承濤,葛長峰,孟冬青,潘雪婷
(北京市礦產地質研究所,北京 101500)
礦產資源戰略儲備,是戰略意義上的礦產資源儲備,通常稱為礦產地儲備(任忠寶等,2013),在北京就是上表礦區(即資源儲量經官方評審備案、登記在《北京市礦產資源儲量表》中的礦區)的儲備。戰略儲備,是礦產資源應急啟用的直接對象,其家底數據是基本國情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密切關系著國家的資源戰略安全,因此數據質量具有重要意義(賈文龍等,2008;余良暉,2016)。
2021年,根據自然資辦發〔2020〕36號文件要求,北京市開展了鐵礦資源國情調查(以下簡稱“國情調查”)工作。此項工作以單礦區為基礎,匯總了全市鐵礦累計查明資源儲量、累計消耗資源儲量、保有資源儲量及壓覆資源儲量的數量、質量、結構及空間分布等基礎數據;分析了各礦區資源儲量變化情況及變化原因,為更新北京市儲量庫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支撐。結果表明,全市累計查明鐵礦資源儲量逾10億t,保有9.46億t(北京市地質工程設計研究院,2021 a),資源儲量豐富。由于各礦山于2020年底前陸續關閉,保有量作為戰略儲備將呈現穩定狀態。
國情調查工作收集的數據質量存在一定的問題,但限于“我們不生產數據,我們只是數據的調查員”這一工作原則,并沒有據以分析評價。本次工作在進一步收集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對數據質量問題進行了歸納總結,分析了戰略儲備的可變因素,并對戰略儲備應急啟用主要方向進行了初步探討。
1 戰略儲備現狀——數據源分類解析
北京市鐵礦資源儲量匯總確定46個上表礦區,按礦床類型分有沉積變質型、沉積型、巖漿巖型和矽卡巖型,累計保有資源儲量9.93億t。其中,沉積變質型保有9.54億t,占比達96%。10年后至2020年底,礦山開采礦區新增資源量0.13億t,累計消耗0.6億t,全部為沉積變質型鐵礦。
按礦區的開發利用狀況,礦區可劃分為未利用礦區和已利用礦區。
1)未利用礦區是指未經任何形式開發利用、消耗量為0、保有量等于原始累計查明量的礦區。這樣的礦區共9個,保有資源儲量0.9億t。
2)已利用礦區是指存在消耗量,保有量一般小于累計查明量的礦區。這樣的礦區共有37個,按開發利用主體的區別,可進一步劃分為民采礦區和礦山開采礦區。其中:民采礦區是指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2010年以前)沒有正規采礦許可證但曾經集體開采或民采的礦區。這樣的礦區有18個,累計查明資源儲量2.94億t,保有2.84億t;礦山開采礦區是指擁有采礦證即合法采礦權而主營采礦活動的礦區。這樣的礦區共19個,其中大型2個,中型10個,小型7個,礦區累計查明資源儲量6.98億t,保有5.72億t。
3)戰略儲備。北京的礦山開采礦區,自2008年起陸續停采,至2020年已全部關閉。全市46個鐵礦區保有資源儲量全部轉為戰略資源儲備,數據定格在9.46億t:按資源量類型劃分,其中探明資源儲量0.24億t、控制資源儲量2.20億t、推斷資源儲量7.02億t。
2 戰略儲備的可變因素——數據源質量分析
戰略儲備數據來自官方,具有權威性和長期的穩定性,但鑒于歷史遺留因素,部分已知和未知數據未納入或難于納入官方統計,而部分數據有失實之嫌,數據質量有待提升——這就是戰略儲備數據的可變性。其可變因素包括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2.1 內在因素
最終會導致上表礦區資源儲量數據變化的因素是內在因素。它的形成與人的認識程度和工作任務的局限性不可分割,屬于資源稟賦自身的問題,可以分為3種類型。
1)資源儲量數據斷檔
北京市密云冶金礦山公司曾下轄5座礦山,21世紀以來,應開采需要各礦山在所屬主要礦區均開展了生產補充勘探工作,包括馮家峪、沙廠、霍各莊、高嶺東—放馬峪、東莊、桑園諸礦區。其中沙廠、東莊、霍各莊、高嶺東—放馬峪均未將變化的資源儲量納入官方統計數據,沙廠、東莊兩礦區尚明確了資源儲量變化情況——二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高嶺東—放馬峪鐵礦的生產補充勘探工作提交了儲量報告,變化情況也有據可循。而霍各莊的補充勘探工作、馮家峪在地下開展的第二次補充勘探工作沒有留下儲量數據。
2)資源量類型“拔高”
懷柔區老公營和雙文鋪鐵礦區曾經民采,分別保有一定的資源量(北京市地質工程設計研究院,2021 b;北京市地質工程設計研究院,2021 c)。按最初勘查報告(首鋼地質勘探公司地質研究所,1994;懷柔縣人民委員會地方工業局,1960),兩礦區資源儲量均屬推斷類型,相當于2020年儲量改革前的333類型。DD 2002-01《中國地質調查局工作標準》關于“固體礦產推斷的內蘊經濟資源量和經工程驗證的預測資源量估算技術要求”明確指出,333資源量是地質可靠程度為依據地表和深部工程見礦情況推斷的、可行性評價程度為概略研究、經濟意義為內蘊經濟的(即經濟意義介于經濟的-次邊際經濟范圍內的)資源量”。而兩礦區礦體除地表探槽外,深部均無鉆孔控制,資源量可靠程度低于推斷類型。按GB/T 17766—2020《固體礦產資源儲量分類》,兩礦區礦產資源可歸于“潛在礦產資源”,而“潛在礦產資源不以資源量表述”。
3)資源儲量沿革不清
密云區兵馬營鐵礦區開展過3次地質勘查工作:1960年詳查工作(北京市地質局密懷平勘探隊,1960),其界定了礦區范圍;1982年是在礦區范圍內,以查明礦區褶皺構造為首要目的的具有科研性質的勘查工作(北京市地質調查所,1982);而1994年則是在向斜轉折端為礦山提供首采區的詳查工作(北京市地質礦產局一〇一隊,1994)。
1982年在查明向斜構造的同時,利用含礦系數,“為較準確反映轉折端處礦體儲量,將其形態視為‘哈密瓜’的四分之一,采用橢球體的體積公式進行儲量計算”求得“II礦帶轉折端處儲量”,相對于1960年提交儲量,“D級”儲量顯著增加(北京市地質調查所,1982)。
1994年詳查工作指出,“80年代前施工的鉆孔,有的孔斜偏差過大,采取率偏低,從而影響了礦體連接對比,對礦體形狀有一定歪曲。在工作中,大部分鉆孔未予利用,只利用了少數質量較好的鉆孔資料,如CK3、CK15號鉆孔等(北京市地質礦產局一〇一隊,1994)”。
1994年的詳查工作,對1982年的勘查成果未予評述,對1960年探礦工程質量總體持否定態度。而受國情調查工作的局限,兵馬營鐵礦區舊有的儲量沿革沒有調整,戰略儲備維持不變,即“哈蜜瓜”里的儲量依然是主體,而其所對應礦體的形態和空間位置難以確定,實屬“潛在礦產資源”。
昌平區上莊釩鈦磁鐵礦區也存在資源儲量沿革問題,致使礦區保有量增大(北京市地質局102隊,1973;北京市地質調查研究院,2004;北京市地質調查研究院,2007;北京市地質工程設計研究院,2021 d)。
2.2 外在因素
從地表或淺部改變礦產資源儲量或賦存狀態的因素是外在因素。它的作用不會從根本上影響礦區累計查明資源儲量,是獨立于資源稟賦之外的因素,包括建設項目壓覆和礦山地質環境治理2種類型。
1)建設項目壓覆
建設項目是否壓覆礦產資源,本質是厘定建設項目與礦產資源的位置關系。壓覆的前提下,在建設項目施工時會消耗礦產資源儲量或改變礦產資源賦存狀態。比較典型的是道路工程,包括隧洞和埡口,建筑基坑也有可能。無論是已利用礦區和未利用礦區,建設項目壓覆礦產資源的情況都可能發生。
2)礦山地質環境治理
一般情況下,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僅發生在已利用礦區。多年來,在已利用礦區,采礦與治理形成了固定的因果關系。相對于建設項目壓覆,治理工程的實施對礦產資源的影響會更普遍、更深遠。這一點,地表開采尤其顯著。以民采礦區密云區大漕鐵礦區為例,在2009年開展礦產資源利用現狀調查時,大漕鐵礦還是千瘡百孔(圖1),歷經治理,現已面貌一新(圖2)。但在治理過程中,是否又消耗鐵礦,消耗了多少鐵礦,尚不明確,它的保有資源儲量,已經停留在2010年治理之前了。與大漕鐵礦相類似的還有達巖鐵礦、水峪鐵礦等民采礦區甚至礦山開采后主動關閉的頭道嶺鐵礦、白河澗鐵礦等12處鐵礦區(帶)(圖3)。近年來,密云冶金礦山公司先后被動關閉的礦區有8個,如果這8個鐵礦區的治理情況對礦產資源的影響一如既往地被忽視,那么礦產資源儲量數據的權威性將會受到更多的挑戰。

圖1 密云區大漕鐵礦區局部采坑(于2009年4月攝)Fig.1 Open pits in Dacao iron ore mine,Miyun County,2009

圖3 密云區鐵礦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分布圖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Miyun iron ore mines’recovered,in and for recovering
以上討論了數據源的變化因素,無論內在因素還是外在因素,它們的存在直接影響戰略儲備數據,包括已知數據和未知數據,致使戰略儲備存量變小。
3 戰略儲備應急啟用的限制條件與主要方向
3.1 限制條件
所謂戰略儲備,是為響應或滿足不時之需,礦產儲備能夠從多大程度上滿足應急啟用的要求,客觀上受到礦產資源稟賦自身和外部條件的限制。
1)內部條件——資源稟賦
北京市有鐵礦區46個,其中大型礦區2個,達到勘探程度;中型礦區20個,其中5個達到勘探程度,6個詳查,9個普查;小型礦區24個,達到勘探程度的礦區3個,詳查3個,普查18個。戰略儲備主要分布在大、中型礦區,其中大型礦區占7.85%,中型礦區占62.46%.按礦產資源類型劃分,探明資源量占2.50%,控制資源量23.28%,推斷資源量74.22%。
總體上,就資源儲量規模和控制程度而言,大中型礦區都要優于小型礦區,而開發利用主要集中在大中型礦區,正是資源稟賦選擇的結果。
除了上述統計數據,就單礦區而言,資源稟賦還包括礦體的富集程度、構造復雜程度、開采技術條件、礦石品位、可選性等(陳興龍等,2010;趙忠琦等,2019);就多礦區而言,礦區的密集程度所反映的成礦地質條件也是資源稟賦的表征之一。北京市沉積變質型鐵礦劃分為庫(密云水庫,下同)西北、庫東北和庫南3個礦集區(許海濤,2013),這3個礦集區匯集了北京所有的大中型(沉積變質型)鐵礦,反映了密云水庫(及周邊)成礦地質條件的優越。
2)外部條件——重要功能區與壓覆
國情調查成果表明,北京市46個鐵礦區中有42個存在已劃定的重要功能區,即它們的資源儲量分布范圍與重要功能區存在空間上的重疊關系。其中生態紅線范圍涉及礦區35個、城鎮建設邊界涉及礦區10個、永久基本農田涉及礦區26個(北京市地質工程設計研究院,2021 e)。在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階段,這些重要功能區是限制開采的條件,致使部分資源儲量成為禁采對象,如在空間上緊鄰密云水庫或與其存在重疊關系的礦區,包括密云區的前保嶺、董各莊—燕落、學各莊、王家會、太師莊、大漕6個鐵礦區。
北京市鐵礦區已批復壓覆礦區3個,其中建設項目壓覆范圍內的礦產資源是禁采對象。
北京市存在事實壓覆的礦區25個,事實壓覆主體主要為居民點、公路和水庫(北京市地質工程設計研究院,2021 f)。受工作任務所限,國情調查工作對事實壓覆進行了定性評價,定性壓覆的礦產資源是否禁采,需要經過進一步的調查評估才能確定。
3.2 主要方向
北京一旦啟用鐵礦資源戰略儲備,資源稟賦是先決條件,從礦區規模看,大中型礦區優于小型;從控制程度看,勘探、詳查優于普查。這兩個序列,鐵礦的開發利用歷史已經印證,因而密云區近年來按政策被動關閉的8個礦區是應急啟用的首選對象。此外,資源儲量規模和勘查程度相近的礦區,曾經民采的礦區優先考慮。應急啟用的主要方向即這兩類優選礦區,它們全部分布于庫西北、庫東北或庫南3個礦集區內。
應急狀態下,當優選礦區涉及重要功能區與壓覆兩種關系時,作為限制條件,生態紅線范圍將最先為開發利用讓路,其次是事實壓覆,再次是城鎮建設邊界。國情調查成果中,事實壓覆是不確定的結論,需要進一步調查評估,即篩查出確定壓覆的部分,方能得到可利用的戰略儲備。
4 結論
受城市功能定位的影響,北京鐵礦資源開發利用暫時告一段落,鐵礦資源全部轉為戰略儲備。戰略儲備豐富是數據的表象,數據的背后隱藏著可變因素,而應急啟用的限制條件進一步制約著戰略儲備的可利用性。總體看,在限制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戰略儲備的應急啟用,應著眼于3個礦集區,首選曾經礦山開采的被動關閉礦區,其次是曾經民采的達到勘探程度或詳查程度的中型礦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