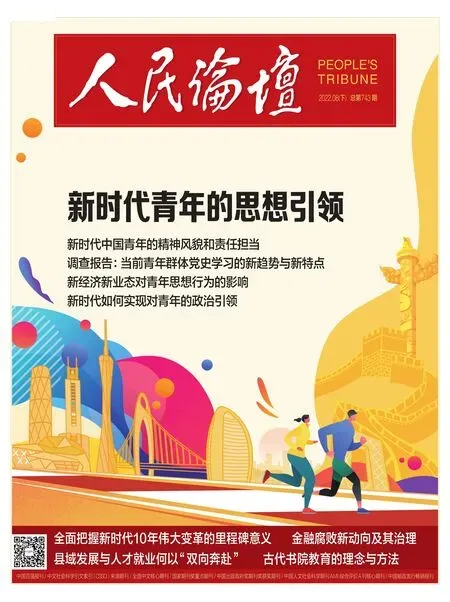新經濟新業態對青年思想行為的影響
趙聯飛
“新經濟”涉及一、二、三產業,并不僅僅指第三產業中的“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和業態,也包括工業制造中的智能制造、大規模的定制化生產等,還涉及到第一產業中有利于推進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股份合作制、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等情況。按照這一解釋,新經濟在當前更多的是籠統指代信息技術環境下涌現出的新的經濟形態。新經濟新業態的出現帶來了新就業。據統計,2019年4月以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了五批共74個新職業,涵蓋了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物聯網工程技術人員、區塊鏈工程技術人員、城市管理網格員、互聯網營銷師等多個類別。業界機構委托開展的研究則列出了更多的職業類別,例如,《2019—2020微信就業影響力報告》顯示,微信生態新職業不斷涌現,2019年微信生態相關職位同比增長156.6%,新媒體運營、社群運營、小游戲開發工程師、微信公眾號運營、小程序運營等職業崗位快速增長。2019年支付寶新職業報告數據顯示,支付寶成立15年來,在其平臺上總共誕生了超過40種新職業。此外,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21年底,快遞員和外賣騎手群體的總規模超過1000萬人。這些數據顯示了新職業群體規模的快速擴大。
從中國近30年來的發展歷程看,無論是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還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都與當代青年群體的成長經歷高度重合。2020年8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新職業——網約配送員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顯示,2020年1月20日至3月30日,美團平臺新注冊且有收入的新增網約配送員達到45.78萬人,20—30歲為疫情期間新增網約配送員的主要年齡段,占比為45.3%。美團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生活服務業新職業人群報告》數據顯示,在從事生活服務業的新職業人群中,92.13%的新職業人群年齡都在40歲以下。艾媒咨詢發布的《2020H1中國直播電商行業主播職業發展現狀及趨勢研究報告》顯示,20—30歲和30—40歲的網絡主播的比重分別為46%和35%。騰訊電競發布的《2019年度中國電競人才發展報告》顯示,20—25歲從業者所占比例為43%,26—30歲的比例為39%。新經濟、新業態的蓬勃發展對青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青年作為社會成員受到新經濟新業態的影響
第一,培育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經濟新業態的出現,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樣態,催生了全新的生活方式。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開始從早期國家倡導信息化轉向了由市場力量驅動的全面商業化,以移動支付、網購、團購、網上炒股、網上預訂、網約車為代表的互聯網應用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加便捷;以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網絡音樂、網絡視頻為代表的網絡休閑活動則極大地改變了人們業余時間的分配模式;以QQ、微信、微博為代表的社交軟件改變了人們社會交往的方式。由于手機上網極大地消除了受教育程度對個體上網能力的限制,上網人群出現低齡化和高齡化的趨勢,其受教育程度的平均水平也逐漸下降。《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3.0%。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7%,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9.75億,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9.04億,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8.42億,網上外賣用戶規模達5.44億。上述數據表明,互聯網在我國經過30余年的發展,已經全方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世界,并改變了經濟和社會的形態。同時,數據還顯示,我國未成年網民已達 1.83 億,互聯網普及率為 94.9%,遠高于成年群體互聯網普及率。這一數據反映了當代青年作為“網絡原住民”的現實,以至于出現“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無網”的說法。
第二,促進了新消費理念的形成。如果說網購、團購、網上炒股、網上預訂等網絡應用還只是傳統業務“搬”到互聯網上,那么,以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共享廚房為代表的共享經濟則在深層次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觀念。從共享經濟在現實中的表現來看,其根本特征是消費者暫時轉移對物品的使用權,并因此獲得收益。與此同時,暫時獲得使用權的消費者則為此付出相對較低的代價和成本。在這里,使用權被轉移的物品既包括像汽車、自行車、房屋這樣的實物,也包括游戲賬號等虛擬物品。共享經濟是在信息技術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新型經濟模式,一方面,它提高了已經生產出來的各類物品的使用效率,從總體上節省了資源,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另一方面,它革新了人們的消費理念,對消費的理解從“占有并使用”轉變為“不必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在共享經濟發展的同時,二手物品和閑置物品交易也開始流行,以二手書、二手玩具、二手電器、二手汽車等為代表的二手交易近年來迅速發展。相關的行業研究報告表明,中國二手閑置物品交易規模從2015年約3000億元快速提升至2020年破萬億元的市場規模,預計2025年將達到近3萬億元的市場規模。
第三,極大地豐富了流行文化。這一過程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觀察。一是網絡世界本身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策源地。在用戶創造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s,UGC)模式下,網絡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尤其是隨著商業機構以UGC模式介入網絡內容生產之后,眾多內容制作機構通過對大眾流行文化特征以及大眾心理的主動把握,制作了大量易于傳播的文化產品,促進了流行文化的發展。二是網絡環境加速了流行文化的傳播。新經濟新業態依賴于網絡信息技術,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現象級熱點,推動流行文化的形成。網絡傳播強化了流行文化所具有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點,往往是舊的熱點尚未完全消失,新的熱點已經開始出現。三是新經濟新業態催生了新的流行文化生產模式。推動個人IP形成而后進行流量變現成為新經濟模式下流行文化生產的重要機制。在這種機制的基礎上,形成了近年頗受人們關注的“網紅經濟”。
青年作為新職業從業者受到新經濟新業態的影響
第一,賦能青年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首先,一部分基于新經濟新業態產生的新職業對從業者的信息技術素養有較高的要求,例如,人工智能工程技術人員、物聯網工程技術人員、大數據工程技術人員、云計算工程技術人員、數字化管理師、建筑信息模型技術員等,從事這些職業需要掌握前沿信息技術,而青年相較于年長的群體,在這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其次,新經濟為青年就業創業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遇。例如,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B2B網站,以京東為代表的B2C網站,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平臺,以美團、大眾點評為代表的生活服務平臺,以知乎、豆瓣為代表的在線知識分享平臺,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的自媒體平臺,等等。這些平臺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和創業機會。最為典型的是,在平臺經濟發展初期出現了一批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草根”博主,他們利用互聯網平臺,改變了自身的經濟狀況。
最后,新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為青年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從2000年開始,以淘寶為代表的電商帶動網店快速發展,使得一些無法在傳統就業市場中獲得良好職位的青年人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在短視頻和直播興起以后,身處農村地區的青年人通過直播帶貨推銷家鄉的農產品,提高了自己的經濟收入,同時也為鄉村的產業興旺開辟了新的發展路徑。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案例是李子柒,她通過拍攝唯美的鄉村生活視頻贏得大量粉絲,并成功創辦了獨立品牌的商業實體。
第二,重塑了青年的職業觀和職業生涯軌跡。一是職業選擇的變化。伴隨新經濟新業態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職業顛覆了人們此前的認知,例如,電子競技成為正式體育競技項目,電子競技運營師與電子競技員被列為新職業。在電子競技員中,除了職業游戲選手,還出現了“游戲陪練師”“游戲代練師”等新職業,從事這些職業的青年在此前被人們認為是“不務正業”和玩物喪志。又如,不少具有高等學歷的青年加入了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職業群體,而在此前人們的刻板印象中,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員學歷普遍較低。調查數據表明,大專及以上學歷人才在這些職業群體中占比并不低,例如,《2019年生活服務業新職業人群報告》顯示,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從業者比例占到68%;《新職業——網約配送員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則表明,快遞人員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占到14%;《2020H1中國直播電商行業主播職業發展現狀及趨勢研究報告》則指出,主播中40%具有大專以上學歷。這表明人們在選擇職業時已經不同程度摒棄了此前的刻板印象,構建了新的職業身份認同。
二是供職模式出現了新動向。近年來,“斜杠青年”“兩棲青年”“多棲青年”大量出現。所謂“斜杠”“兩棲”“多棲”均是指人們同時從事兩項或者兩項以上的職業,這些職業所需要的工作技能乃至工作特點彼此差異可能較大,甚至角色橫跨了老板和員工,模糊了雇傭者和被雇傭者的身份。之所以出現這種模式,是因為有的人認為單一職業的收入不能滿足自身對收入的要求,有的人認為自己的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還有的人認為既有的職業并不是自己的興趣和愛好所在。
三是職業生涯的發展樣態呈現跨界特征。在新經濟新業態的影響下,許多個體改變了傳統的單一職業發展路徑,在“兩棲”和“多棲”的基礎上,一些青年的職業生涯呈現出多軌并進的特征。例如,一些文藝和體育明星在獲得一定的社會榮譽之后,走上直播帶貨的發展道路,商業研究者通常稱這種現象為“流量變現”。從深層次的角度分析,這種現象反映的是社會資源的交換和應用方式在新經濟模式下的更新和放大。回顧歷史,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就已經出現電影和體育明星代言廣告的情況。如果我們認為當時的這種明星廣告代言是較低層級上的跨界。那么,在新經濟模式下,職場人士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和資源,同時也充分利用互聯網環境下勞動自主性增強的特點,在多個領域進行發展,則代表了一種新的職業發展理念,這種跨界的實踐模糊了既有的職業界限,彰顯了勞動者作為主體的自由度。
第三,改變了傳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關系。從勞動過程來看,互聯網平臺在很多時候突破了傳統上對勞動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而使得勞動過程獲得相對的自主性。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勞動者被綁定于固定的勞動場所,尤其是在工業社會中,為了滿足工業生產的內在節奏,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也受到嚴格控制。而在互聯網平臺,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的支持下,勞動者的勞動場所大為拓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居家辦公的工作方式已經越來越常見,無論勞動者身在何處,都可以通過網絡來完成處理訂單、與客戶視頻會談、遠程簽訂協議等工作任務。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勞動過程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可能會進一步放松,從這一角度講,新經濟新業態使勞動者獲得了較高程度的勞動自主性。
從勞動關系來看,互聯網平臺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勞動關系,同時也給現行勞動法的實施帶來了挑戰。在傳統的勞動關系中,雇傭方和被雇方身份明確、權責清晰,而互聯網平臺在勞動關系中并不是明確的雇主身份,這為現行法律框架下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帶來了法律難題。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案例表現在網約車平臺和直播平臺中。由于網約車司機與網約車平臺之間簽訂的并非勞動合同,網約車平臺僅按照業務抽取訂單提成,因而在網約車司機出現疾病或在勞動過程中受到傷害時,其勞動權益無法得到全面保障。同樣地,在直播平臺中,如果主播及其輔助人員并不隸屬于某一個多頻道網絡(multi-channel network,MCN)機構,而是直接與平臺公司簽訂合作協議,那么,當他們遭受勞動傷害時也面臨類似網約車司機的情況。
新經濟新業態對青年的影響是深刻且全方位的
總體來看,新經濟新業態建立在信息技術的應用之上,并且始終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由此增強了從業者在其中面臨的社會風險和不確定性。新技術對舊技術的取代將使得原來的從業者不得不轉向全新的行業。新經濟新業態的這種內在特質使得從業者在客觀上需要終身學習以應對社會的快速變化。新經濟新業態強化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所言的“制度化的個體主義”。基于社交網絡軟件形成的個人社會網絡正在取代傳統上基于地緣、血緣和業緣而形成的社區,而互聯網平臺經濟在提供一定的勞動自主性的同時,也將個體與勞動社會組織進一步割裂,不僅在實質上與工業社會同樣加速個體化進程,更在形式上強化了這種“制度化的個體主義”。新經濟新業態造就的新的財富分配格局和發展空間對不同的青年群體有著不同的影響。由于“數字鴻溝”的出現,青年群體在信息技能方面存在差異,新經濟新業態在很多情況下放大了這種差異,并最終體現在不同青年的職業發展軌跡和人生軌跡中,由此可能出現新的社會不平等生成機制。也正因如此,在新經濟新業態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有效消除“數字鴻溝”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議題。
新經濟新業態對青年思想狀況和行為的影響很可能是一個雙向的作用機制。一方面,如前所述,新經濟新業態對青年的思想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同思想文化的變化是一個累積和連續的過程,那么,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的各類社會思潮,實際上對新經濟新業態的發展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在40余年的時間內,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社會領域的改革也大步前行。而西方各種思潮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大量涌入并廣泛傳播,比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消費主義、工具理性等社會思潮,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深刻影響。在新經濟新業態的高速發展中,可以觀察到上述社會思潮的影子。例如,從“斜杠青年”的實踐中可以看到個體主義和文化自由主義的影子;在“網紅經濟”以及流量快速變現的商業模式中,消費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影子時常出現。盡管這種影響是雙面的,是潛在的而不是顯性的、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在長時段歷史變遷過程中來考察新經濟新業態對青年思想觀念和行為的影響,將有助于人們進行更為透徹的分析并作出更為理性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