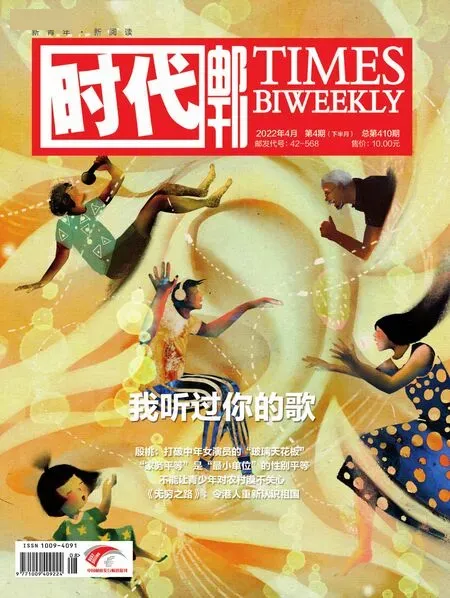流動的音符
文 任冠青
正如刺猬樂隊所唱的:“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拿音樂來說,每一代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歌,經典歌曲是個體成長和時代發展的記錄。它們刻畫著不同的青春面貌,而音樂也成為辨認彼此的一種符號。
有沒有那么一首歌……
哪首歌是你的青春“必聽曲目”?對于這個問題,各個世代的答案可能有著全然不同的“畫風”。有些人的“回憶殺”是一遍遍聽郭蘭英的“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那時候,新中國成立不久,百業待舉、欣欣向榮。這首《我的祖國》唱出了年輕人為開辟新天地,喚醒“沉睡的高山”、讓“河流改變模樣”的蓬勃朝氣。
八九十年代,華語樂壇群星閃耀,迎來流金歲月。有人在鄧麗君的溫柔甜美歌聲中迷醉,《月亮代表我的心》和《我只在乎你》成為許多人的情歌啟蒙。有人偏愛王菲的空靈之音,當燈光打開,瘦削的王菲出現在舞臺之上,一開口便能攝住所有目光,每一個詞句都直達靈魂深處。多年以后,《紅豆》中那句“等到風景都看透,也許你會陪我看細水長流”,《流年》里的“有生之年,狹路相逢,終不能幸免”仍會令人沉吟良久。
那時,不管是內地的劉歡、毛阿敏、田震,還是港臺的張國榮、“四大天王”、羅大佑、李宗盛、譚詠麟,都自成風格,盡情綻放,留下了一首首至今仍被傳唱的流行金曲。
對85后、90后來說,他們的“青春歌單”則是由陳奕迅、周杰倫、孫燕姿、林俊杰、SHE等明星偶像填滿的。這些偶像當時有多火?那些像周杰倫一樣愛摸鼻子、愛耍酷的寡言男生,總是不難成為校園的焦點;隨便哼一句“你是電,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話”,就能開啟一次“班級大合唱”;每逢畢業之際,樸樹如呢喃般演唱的“我們就這樣,各自奔天涯”便會飄蕩在人群中,訴說著彼此的不舍……
再以后,音樂的載體從磁帶、CD、MP3變遷為手機里的音樂App,95后、00后有機會接觸更加多元、小眾的音樂創作者,也展現出更加豐富的音樂旨趣。他們聽歌時更強調自我選擇的主體性,愿意去了解剛剛起步的先鋒歌手,也喜歡嘗試鮮有人走的音樂小徑。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夠再占據絕對的音樂“C位”,人們的聆聽喜好參差百態:有人喜歡民謠,有人熱愛搖滾,有人則沉浸在“抖音神曲”之中。五條人、毛不易、陳粒、康姆士……人們的選擇是如此之多,總有“一款”令我鐘意。
“有沒有那么一首歌,會讓你輕輕跟著和……”正如周華健所唱的,每個時代,都有那么幾首朗朗上口、讓人難以忘懷的曲調。因為太過耳熟能詳,它們早已成為時代的背景音,嵌入人們的記憶深處,激蕩起不盡的回憶。
一首歌,承載著什么
歌曲,顧名思義,是旋律與歌詞的結合。正因如此,優秀的作品往往有豐富的文學和藝術內涵,能夠為聽眾帶來愉悅和審美的雙重體驗。

歌曲的力量,首先體現在它能給人帶來感官上的美好享受。這背后,固然有著科學性的分析,比如好的音樂能刺激腦回路,釋放多巴胺等令人心情愉悅的物質。不過對普通聽眾而言,即便不懂其中的道理,類似的生理性感受也幾乎人人都有,并不高深玄妙。
就像我們看奧黛麗·赫本抱著一把吉他,在電影《蒂凡尼的早餐》中略帶憂愁地唱起《月亮河》,就是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縈繞于周身的浪漫感。聽到《十年》,就是會被戀人漸行漸遠、無奈錯過的酸澀打動。很多時候,我們被一首歌曲擊中,就是會如此“沒有理由”。
除了歌曲“本體”,“那一首歌”之所以意義非凡,是因為它承載著太多沉甸甸的回憶:或許是小時候共同抄寫歌詞的場景,或許是如紙頁般泛黃的童年記憶,又或許是與好友的分別……就像我的表弟,每次跟我見面,常會提到讓他懷念的少年時候的場景:那時,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都還有暑假,我們圍在一起,最喜歡聽的是周杰倫的《動感地帶》。而今,我們分隔各地,每每見面都有些匆匆,能夠湊在一起安靜聽個歌的時間更是少之又少。
傷逝、勇氣、愛情、勵志、期待……人類的情感世界浩如煙海,而好音樂的奇妙之處,便在于它們觸達精神世界的力度是如此精準,涵蓋的情感譜系又是如此之廣。
從創作、歌唱,到被傾聽,一首經典歌曲的生命,如同一個跨越千里的漂流瓶。寫作者將自己的情感、過往和感受沉淀、提純,經由歌者深情演繹,最終投入每個觀眾的心海,激起心底的層層漣漪。
初聞不識曲中意,再聽已是曲中人。很多時候,在不同人生階段聽同一首歌,往往會有不同的感悟。前段時間,我的多位好友點贊了劉若英在演唱會上與觀眾同唱《后來》的視頻。視頻中,劉若英臉上掛著笑容,眼角卻止不住地溢出淚水,直至哽咽。而那群伴隨這首歌共同成長的年輕人,則在現場與她一同流淚,一同感懷,形成一種彼此相通的情感共同體。也許,這便是這首歌的生命力所在:我把過往唱與你聽,而你又完全懂我在唱什么。
除了寄寓情感,歌以言志也是經久不衰的音樂傳統。其中,有黃霑作詞時一揮而就,直抒“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的矢志不渝;有“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三毛式流浪情懷;也有那位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音樂人鮑勃·迪倫,他筆下的那句“一只白鴿要飛過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彈要多少次掠過天空,才能被永遠禁止”,通過其“砂紙般”的嗓音深沉地詢問著世界,讓頭腦發熱的人們不得不跟著安靜下來,去反思戰爭給我們帶來的災難,去思考愛與和平的價值。
音樂連接你我
好聽的歌曲,總會有一種神奇的魔力:音樂一流淌出來,仿佛空氣都被加上了一層濾鏡,周遭的人、事都會變得更加可親、可愛。音樂作為一種世界通用的語言,可以跨越時空、種族、人群,讓聽歌的人彼此結識、了解。對每個人來說,秉持開放的態度,懂得以音樂為支點,打通自己與他人、與外界的聯結,便不難開辟出更加豐盈、自如的精神世界。
人是社會型動物,歌曲在人類社交中的助力作用不容小覷。很多時候,一首歌既可以幫我們找到擁有共同審美偏好的“同類”,也能夠成為現實社會交往中的“破冰利器”。
在網易云音樂上,有一種有趣的“景觀”:離開了網友們的精彩熱評,一首歌仿佛都不夠完整了。評論區里,人們交流著自己是從哪部電影尋過來的,聽到這首歌后內心是如何久久難以平復,有些甚至成為了現實中的好友。從卡拉OK到KTV,只要那些熟悉的旋律響起,最初略顯拘謹的人們也會放下靦腆與不安,與身邊的人一起不由自主哼唱起來。
這樣的景象,便揭示了歌曲的重要社交作用:它就像是一個個標簽,構建在日常生活之外的社群里;它也像是神奇的黏合劑,讓陌生人卸下心防,坦誠面對彼此。
以歌曲為媒介,我們還可以被它帶到千里之外,洞悉人間世相,開闊自身視野。比如,因它去了解一座陌生的城市,去體味一種新鮮的生活。
很多五條人的樂迷就坦言,如果不是因為聽他們的歌,大概永遠都不會知道廣東還有個叫做“海豐”的小城。那一句句讓人聽了“上頭”的當地方言,使人感受著一種被海風浸泡過的縣城美學和處世哲學。前段時間,《漠河舞廳》的大火,也讓不少年輕人為中老年人的凄美愛情所動容。兩代人之間,因著這首歌曲產生了深深的共情。
可見,音樂之大,足以裝得下整個世界的風土人情和豐沛情感。很多時候,學會走出自己的音樂“繭房”,去聆聽異質的、陌生群體的講述和歌唱,能夠極大地拉寬我們的生命廣度,讓我們以更加平和、包容的心態看待世間萬事萬物。
就更廣闊的層面而言,一首動人的歌曲,往往能成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消除隔閡、增進理解的契機,成為人們共克時艱、團結友愛的動力。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中重現的一個經典場景,就讓無數人動容:那是1985年,皇后樂隊在援助非洲慈善音樂會上壓軸表演,佛萊迪·摩克瑞一口氣演唱了《We will rock you》《We are the champions》等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臺下,萬人忘我合唱,為幫助非洲走出饑荒加油打氣。那一刻,音樂成為聯結整個人類的紐帶。
往事并不如風,歌曲是情懷的寄托。每一首被反復“單曲循環”的歌,背后都刻著聽眾的過往流年,載著這個世界的多重情感。去吧,去聽一聽彼此珍視的那首歌,便更知人間多么奇妙,世界有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