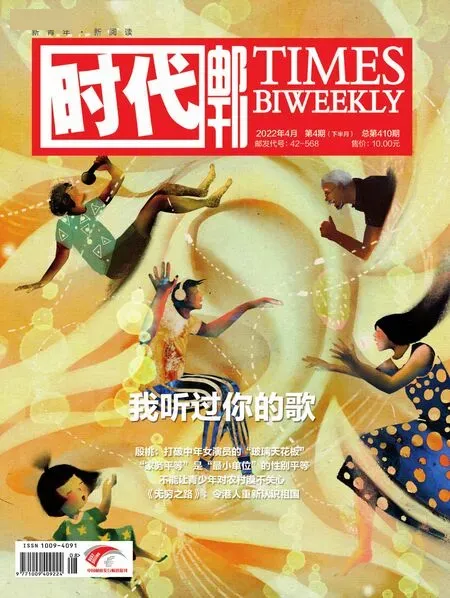互聯網上的求醫者
文 習思怡
無論是線上咨詢與預約,還是遠程隨訪、配送藥品,互聯網醫療配合線下診療,滿足患者多層次的就醫需求,讓患者獲得更接近全流程、全周期的閉環管理。此外,在互聯網醫療平臺,患者的自主選擇權更為凸顯,主動尋求優質醫療資源的路徑不斷縮短。

過去兩年,互聯網醫療在抗疫中發揮的作用有目共睹。國家相關支持政策相繼推出,希望依托“互聯網+”等新技術,擴大優質醫療資源延伸服務范圍,緩解人民群眾看病難問題。
“互聯網+醫療健康”對傳統醫院的線下診療模式形成了強有力的補充作用,正在成為中國醫療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重視“遺忘”
19歲時,“早發型阿爾茨海默病”這個名詞擺在了阿文面前。阿爾茨海默病(AD)在我國約有1000萬名患者,早發型AD僅占AD患者的3%~5%。
從外表來看,阿文和同年齡段的人無異,幾乎看不出他是“早發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
回溯阿文的幼年時期,就已經有注意力缺陷,有時情緒低落,有時興趣高昂的情況。進入青春期后,又因為多次出現昏迷而反復急診處理,最終確診了少見的“高胰島素血癥”,手術治療很成功,但沒多久發現自己的記憶力逐漸下降。阿文輾轉奔波于成都、廣州、武漢、上海、北京等地各大醫院。因為“早發型阿爾茨海默病”的病例十分罕見,各種檢驗檢查卻始終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
盡管優渥的家庭條件能夠支撐這段漫長的求醫路,但阿文疲于奔命。
“病情確實很復雜,所以在各家醫院看完之后,患者聽到的建議會有差異。”阿文祖母攜帶阿爾茨海默病突變基因,“研究表明,攜帶了突變基因的無癥狀阿爾茨海默病患者,隨著年齡的增長,必然會出現認知功能障礙、行為改變等癥狀。”
面診前,阿文通過某健康互聯網醫院多次咨詢與溝通,再預約特需門診,把已經做過的各項檢查結果進行梳理。
自從開始求醫,阿文有意識地進行了記錄,將自己的病情做全面收集、整理。盡管他多次提醒自己要細心,但依舊出現重要資料丟失、遺忘復查時間等情況。
確診后,北京某醫院神經病學中心徐俊教授開始對阿文的生活方式進行有效的干預和促認知藥物治療,以延緩疾病進展。
目前,除了一年一度的復查需要阿文從四川來到北京,互聯網醫療為定期隨訪交流提供了便利。
“近年來,對于有確切醫療需求的人,互聯網診療方式確實節省了他們的時間、金錢。同時也有助于找到專家進行健康管理。”徐俊說。
互聯網醫療的發展,使得罕見病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互聯網醫療平臺。
“罕見病患者人群少,就診更坎坷。較難找到正確的診療方式,因為部分地區的醫療資源和病例難以支撐醫生對罕見病的研究。”徐俊說,“互聯網平臺對疑難罕見危重癥的及時的干預和支持很重要,同時也可以實現對常見病的規范全程綜合管理。最終努力為患者或咨詢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務。”
“怕是個騙子”
和阿文一樣,劉雪也在互聯網醫療平臺看到了新的方向。
一年前,劉雪下臺階時跌倒,雙膝直接跪在磚上,“當時想著忍一忍也就過去了,沒去醫院。”2021年初,雙膝的疼痛再次加倍襲來,膝蓋上好像長期附著一層寒冰,劉雪無法長時間站立,甚至難以從客廳走到廁所。她只能辭職在家休養。
“當地醫院醫生的診斷是滑膜炎,讓我正常服藥、貼膏藥、加強鍛煉,但我膝蓋疼痛不斷加劇。”劉雪雙腿難以支撐長期外出求醫,她待在家里,開始尋找一切希望。
2009年,剛大學畢業的梁強突然膝蓋腫脹,他只能踏上求醫路。“我父母是農民,我自己沒法好好走路,還需要每周去醫院抽積液、打玻璃酸鈉……”待業在家的3年里,梁強兩次前往外地住院治療,花費的幾萬元已經成為家里沉重的負擔。
“人生軌跡都變了。”35歲的梁強在找到肖軍前已斷斷續續求醫12年,卻依舊對病癥沒有清晰的認識。轉折發生在2021年8月,偶然的機會,梁強成為肖軍的病人,他患上的未知疾病終于找到了名字——陳舊性的前交叉韌帶損傷。
肖軍是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關節科主任,梁強在他的科普視頻里看到了希望。11月,梁強完成手術,持續了12年的求醫路終于看到盡頭。
“在復查時,會通過某互聯網醫院聯系肖軍醫生,不用跑到廣州,會好起來的。”梁強說。
與梁強不同,劉雪仔細聽完肖軍的科普后,心中存疑,“怕是個騙子,之前上醫院都沒看好,上網上找個醫生能看好?”她持續關注肖軍,通過某互聯網醫院取得聯系后,一股腦將自己的片子、報告通過圖文的形式上傳至平臺。通過線上溝通,劉雪逐漸安心。線上的診療往往比線下耗時更久,能夠更全面地進行連續性的診療,詳細為患者講解病因與治療。
兩個月后,劉雪的癥狀有所緩解,聯系肖軍面診。通過進一步的治療肖軍為劉雪制定了手術方案并成功完成手術。數次求醫碰壁,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重燃了希望的燈。一年的時間便通過網絡渠道找到了良醫,經正確的診斷和治療,將在康復后回到受傷前的生活狀態。
互聯網醫療的發展,不僅為許許多多求醫多年未見成效的罕見病、疑難雜癥的患者拓寬了就醫路徑,也讓異地看病、隨時隨訪成為現實。
“做醫生的初心”
作為國內首批取得互聯網醫院牌照的平臺型互聯網醫院之一,某健康互聯網醫院入駐了許多如肖軍、徐俊一樣推進線上線下醫療一體化的醫生。截至2021年6月,該平臺入駐超過13萬名醫生,2021年上半年日均問診量超過16萬。他們利用互聯網醫院為更多患者提供幫助,同時也能接觸到大量患者案例以進一步提升自己的醫療水平。
5年前,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內鏡科主任倪曉光入駐該互聯網醫院,正是希望通過互聯網獲取到更多需要針對性治療的患者,解決更多的臨床問題。
倪曉光認為,互聯網醫療平臺能夠囊括各類病癥,病歷資料具備重要的臨床價值,在后續隨訪過程中,還能夠及時獲得診斷的更新與反饋,醫生在此過程中便能夠獲得成長,以此形成良性循環。在此基礎上,倪曉光融合線上線下診療過程中諸多患者疑問,將醫療術語轉化為人們能夠清晰聽懂的語言,分享了普適性的科普建議。倪曉光說:“解決患者的問題是我做醫生的初心。”
除此之外,互聯網醫療行業也涌現了越來越多的全職醫生,肖幸幸就是其中一員。
2020年初,在對平臺型互聯網醫院做足了解后,原北京某醫院呼吸科醫生肖幸幸毅然選擇成為了一名全職互聯網醫生。彼時,新冠疫情暴發初期,肖幸幸剛剛入職便投入到緊張的抗疫工作中。最忙時,她一天接診多達200多次。
在肖幸幸看來,疫情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互聯網醫療本真的樣子,同時也讓以“互聯網+醫療健康”得到了一次真正“試煉”。
事實上,無論是線上咨詢與預約,還是遠程隨訪、配送藥品等,互聯網醫療配合線下診療,滿足患者多層次的就醫需求,讓患者獲得更接近全流程、全周期的閉環管理。此外,在互聯網醫療平臺,患者的自主選擇權更為凸顯,主動尋求優質醫療資源的路徑不斷縮短。互聯網醫療正在突破傳統醫療的區域局限性,逐步緩解我國優質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
在徐俊看來,阿文遲早會像《百年孤獨》里描述的一樣,記憶會一片一片掉落,但并不意味著放棄治療,而應該更積極的落實健康生活方式管理聯合藥物治療。“醫生不僅要有同情心,更重要是共情,也要共理,共理比共情更難實現。”徐俊說,“正像我們國家的態度,人民對健康、對幸福生活向往和追求,是我們醫療應該努力去接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