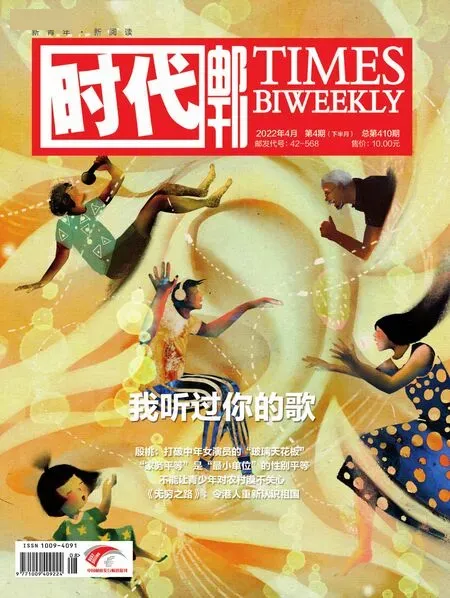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寒士之風
文 梁再冰

(節選自梁再冰口述,于葵執筆,龐凌波、潘奕整理的《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母親》,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21年10月)
1940年12月13日上午,我們從宜賓坐小木船(下水船)前往李莊。我們一家后來在李莊住了五年半,直到1946年夏天才離開這里。在木船搖到李莊時,我們五個小孩高興得同聲大喊:“李莊!李莊!”
李莊鎮在長江南岸,在物資匱乏的抗戰時期,這里是一個物產比較豐富、得天時地利的好地方。但是,李莊也是一個氣候比較陰冷潮濕的地方,對患肺病的人很不利。媽媽的身體也因無法適應這里的氣候而失去了健康。
我們到達李莊后,立即前往離李莊鎮約兩里路的上壩村月亮田,中國營造學社的“社址”就在這里。
1941年至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抗日戰局最艱難的時期,也是從我們一家人自離開北平以后最煎熬、最暗淡的時期。我的三叔梁思永到李莊后肺病也復發了,爹爹對兄弟和妻子的重病非常無助。他腰背痛的毛病雖然暫時沒有犯,但此時他的背已經駝得很厲害,體質也在明顯地下降,雖然只有40歲,可是精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家里的經濟狀況日漸走向谷底。我們住的兩間陋室低矮、陰暗、潮濕,竹篾抹泥為墻。爹爹和媽媽的臥室部分是磚墻,雖裝了白木地板,但仍頂不住川南的潮氣。梁柱都被煙火熏得漆黑,頂上有竹制席棚,蛇鼠常常出沒其間,木床上又常出現成群結隊的臭蟲。沒有自來水和電燈,夜間只能靠一兩盞菜油燈照明。
更使父親傷腦筋的是,營造學社的經費問題使得研究工作已經變得舉步維艱。爹爹不得不每年花費大量的時間到重慶去請求資助。那時候的交通非常不便,從李莊到重慶要坐船,跑一趟要好幾個月。因為學社是個民間學術團體,沒有正式的編制,向國家機關申請經費很是艱難。教育部補貼給的是鈔票,但那時候物價飛漲如脫韁之馬,通貨膨脹異常嚴重,若每月薪金到手后不立即去購買柴米油鹽,等過個三五天,鈔票就會化為廢紙一堆。
食品愈來愈貴,我們的飯食也就愈來愈差。媽媽吃得很少,身體日漸消瘦,整個人看上去憔悴不堪。肺病病人需要補充營養,但那時候根本買不到奶粉。為了變換伙食花樣,爹爹在工作之余開始學習蒸饅頭、煮飯、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醬等。家中實在無米下鍋時,爹爹就帶著我到宜賓鎮上委托商行去典賣衣物,我們把派克鋼筆、手表、媽媽的一些衣服等“貴重物品”都“吃”掉了。爹爹還常苦中作樂道,“我們今天把這只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清燉’如何?”
這一路西遷流亡中,我們的家庭生活遭遇巨變,在李莊,美麗的媽媽所有的好衣服幾乎都送進了當鋪;她一夜之間從京城的大小姐,變成家徒四壁、終日忙碌的煮飯婆……我們的生活日益清苦,每況愈下,媽媽調侃自己說:“我必須為思成和兩個孩子不斷地縫補那些幾乎補不了的小衣和襪子……這比寫整整一章關于遼、宋、清的建筑發展或者試圖描繪宋朝首都還要費勁得多。”她對我的學習成績還不錯挺高興,但是對我每天要走很長的泥路去上學又感到心疼,還總是擔心我中午上學會吃不飽。

梁再冰(左一)與父母合影
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籍貫廣東新會,畢生致力于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護,是建筑歷史學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師,被譽為中國近代建筑之父。
爹爹也曾這樣描述我們在李莊的日子:“很難向你描述我們現在的生活,或許很難想象:在煤油燈下,我們做著兒童的棉底鞋,點火做飯,買便宜的粗糧。我們回到從前,過著像父母十幾歲時一樣的生活,但卻從事著現代工作。”
正在這讓人倍感生活煎熬的時刻,從北方傳來了遲到兩年的消息。1939年,天津因為漲水成為一片澤國。營造學社六七年間在各地考察,走遍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浙江幾個省所搜集到大量的古建筑資料,包括拍攝的大量照片、繪制的圖紙等,在抗戰剛開始的時候,曾被爹爹和劉伯伯存放在天津麥加利銀行的地下保險庫中,他們只隨身帶走了少量關鍵的測繪筆記和資料。誰能料到天津發大水后,這批資料悉數被淹沒。這是父母和學社成員們多年心血的積累和結晶,父親和母親聽到這一消息后幾乎痛哭失聲。父親是從不輕易掉淚的人,我這輩子從未見他們哭得這樣慘痛過。
1942年春夏以后,父親和母親的精神開始稍有好轉。他們決定排除困難恢復《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的出版,將他們戰前的實地勘察成果和戰時的調查研究報告發表出來。那時,父親和莫宗江先生承擔了大量的繪圖工作。只要不發燒,身體勉強可以支撐時,母親也要大量讀書做筆記,協助父親做英文文字解說及圖文編撰等工作。
當時李莊既沒有印刷用紙,也沒有可以印刷的設備。爹爹他們只好自己刻蠟版石印,其中的圖紙和文字印刷,全依靠人工手描;裝訂也很困難,只能用最傳統的笨辦法,用一針一線縫起來,全家人都加入了這個“印刷作坊”,連外婆都出來幫忙了。
雖然李莊的印刷條件極其簡陋,最后大家還是齊心協力,完成了兩期《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全手工制作出版。1944年出版了第七卷第一期,1945年出版第七卷第二期,每期分別印刷了200冊,在戰火紛飛中寄往全國各地與讀者見面,使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建筑學者都知曉了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李莊那段與父母朝夕相伴的歲月里,雖然我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然而父親母親在事業堅守和面對困苦中始終有著共同的態度和選擇,他們表現出高度的一致。面對生活的突變和下沉,他們都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們依舊可以笑口常開,他們的拌嘴和吵架也少有因為缺吃少穿,倒是常常為工作爭得面紅耳赤,典當衣物他倆互相調侃,一副苦中作樂的模樣。我開始慢慢體會出爹爹和媽媽身上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寒士”之風,無論生活“淪落”到怎樣的底層困境,他們那股子“精神頭”始終傲然而立,從不曾消失丟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