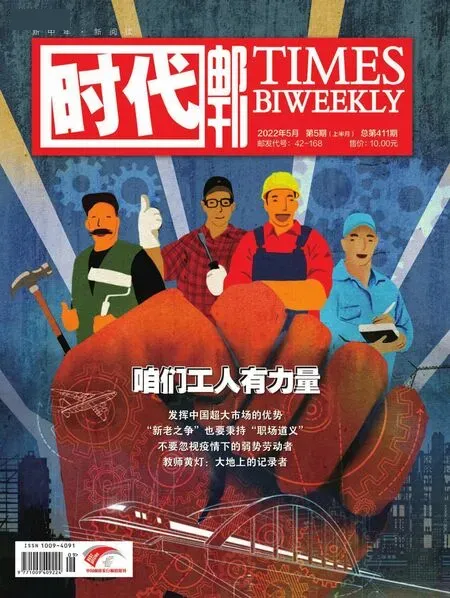走在研究“誤診”的坡道上
● 魏晞

1985年,在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醫務部工作的陳曉紅,畫“正”字統計經手的死亡報告單。現在,71歲的她只要用計算機“跑一下”,有關誤診病歷的數據就會出現在電子屏幕上。
究竟經手過多少份誤診病歷報告?她記不清具體的數字了:“大約30萬份吧。”
這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就像攀登一座醫學高山,分支眾多的專科是從正面拾級而上,而研究誤診是從背面翻越,同樣要經過陡坡和峭壁。如今,退休多年的陳曉紅還在向上爬。
不是制造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
許多雙眼睛關注著誤診研究:出版社時不時詢問陳曉紅的研究進度;程序員也加入研究,借助編程技術找到誤診疾病之間的相關性;科技公司找上門來,想收集她攢了30多年的誤診病歷數據。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陳曉紅和同伴完成第一版《誤診學》書稿時,卻被出版社拒絕:“醫生都要寫經驗,你這寫的是反面。”為了讓新書出版,她拜訪當時的醫學“大咖”,請他們幫忙寫序。
吳階平向她敞開了門。這位中國泌尿外科先驅者、診治過周恩來總理的醫生為了支持陳曉紅,挨個通知當時在北京能找到的醫學界院士參加新書出版的研討會。“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你們做了,我很激動。”“中國外科之父”裘法祖也給她打氣:“有人研究犯罪學,不是教人犯罪,是為了避免犯罪;同樣,研究誤診不是教人誤診,而是要減少、避免誤診。”
1995年,陳曉紅到《臨床誤診誤治》雜志當主編。那時醫療糾紛增多,承認誤診無異于“自找麻煩”。但一批老院士、老醫生,愿意說“刺耳”的話,把封筆之作留在了這本雜志上。
如今,計算機幫助陳曉紅找出了許多誤診規律。各級醫院的醫生都可能誤診:年輕醫生誤診,大多因為經驗不足,想不到是另一種病;老醫生誤診大多因為經驗太豐富,想當然。誤診不是A病被誤診為B病,而是A病可以被誤診為許多病,許多病可以被誤診為A病,不同問題互相交織。更麻煩的是,在今天,留給醫生診斷的時間變少了。醫生必須爭分奪秒與疾病競爭,果斷給出正確診斷。
扎進誤診研究幾十年,陳曉紅決定要做給臨床醫生提醒的人。“不讓診斷走彎路。”為了提高雜志稿件水平,上世紀90年代中期,陳曉紅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各個專科最資深的退休主任聘到編輯部,共同評審來自全國各地的投稿。
干了大半輩子臨床的老主任們對這個新任務充滿熱情。有人常常邊讀稿邊嘟囔:“我在臨床見過這個案例。”有人看到稿件寫得亂,忍不住上手逐句修改。還有人讀著讀著就拍桌而起:“這簡直是草菅人命!”有時遇到連他們都沒見過的案例,老主任們就一遍遍討論、翻書。編輯部的幾個大書架,很快就塞滿了最新的醫學書。
許多醫生說,誤診推動著醫生進一步認識人類的身體。其實,《臨床誤診誤治》的創刊人馮連元,最初也是為了汲取同行的誤診經驗而創辦雜志。當時,中國消化病學奠基人張孝騫很支持他,但也表示擔憂:“這個名字會不會惹事?”思前想后,馮連元決定:文章隱去患者、醫生名字,并適當修改一些細節,以免暴露患者個人信息。“辦這個雜志,是要解決問題,不是制造問題。”
誤診是系統性難題
現代醫學不斷取得進步,但誤診依然每天在臨床上發生。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醫生何權瀛認為,解決誤診是系統性工程。人類所掌握的醫學知識越來越多,醫學專科越分越細,許多醫生只專注研究一個專科中的一種疾病,當患者有多種疾病時,就容易漏診。
“就像用鉆頭打洞,越鉆越深,最后看不見洞旁邊的地方。”何權瀛研究睡眠呼吸暫停20多年,發現這個疾病可能引發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其他疾病。問診時,他喜歡給病人列明各種疾病,細細提問,尋找每種疾病間的關聯。但有的病人不愿回答過多問題:“你這個大夫這么煩人,給我開藥不就完了。”
醫患互相不信任,是導致誤診的原因之一。患者如今能從很多途徑獲取醫學知識,但何權瀛認為,公眾的衛生知識水平依然不夠。前幾年,《臨床誤診誤治》編輯部不時迎來“不速之客”——患者拿著一疊病歷,希望編輯們評評理:“你們判斷一下,我這是不是誤診了?”陳曉紅總結,這種態度緣于知識不對等。當病人躺在床上接受檢查時,他在仰視醫生;但當醫生看不懂疾病、下不了判斷的時候,他也在仰視神秘復雜的醫學宇宙。
誤診研究是醫學發展的同行者。醫療檢查技術的發展一度幫助醫生作出正確判斷,但陳曉紅發現,過度依賴檢查機器,成了新興的誤診原因。幾十年來,誤診的概念逐漸變廣,對醫生的要求更嚴格了。過去,醫生診斷錯了疾病才算誤診,如今即使診斷正確,但是治療用藥不恰當,或是初診時判斷錯誤,也算誤診。
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布數據,臨床醫學的平均誤診率為30%,其中80%的醫療失誤是思維和認識錯誤導致的。為了獲取經驗而辦刊的馮連元,如今已在臨床工作了近40年,攢足了經驗。但他發現,即使有了經驗,也還是可能誤診。
對于常見的疾病,醫生要根據對應的診療指南用藥、治療,但指南里的標準,并不能完全適用于每個病人。比如,按指南規定,煤氣中毒病人要輸液200毫克煙酸,但馮連元遇見過超出想象的情況:用2000毫克、指南所寫的10倍量的煙酸,才救回病人。
超越診療指南用藥,極其考驗醫生的勇氣。如今,為了避免過度醫療,系統能自動識別醫生的用藥量,一旦發現超出指南的規定,會對醫生罰款。而一旦發生醫療糾紛,將根據指南判定責任歸屬,醫生必須解釋清楚為什么不按指南的規定開藥。
馮連元總結,制定指南是大進步,但每個人適用的用藥量是不同的,要理解個體差異。“就像把100個螺絲釘安裝進孔里,某些螺絲釘就得墊張紙,才能精準安裝。”于是,退休多年的他還在研究誤診。他引用數學模型,彌補不精準的問題,找到墊螺絲釘的那張紙。
醫生們能夠自省、敢于發聲
孟慶義曾以主任醫師的身份,出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講臺上。坐在底下的從各地來進修的醫生,都是在當地醫院“跺個腳地都要抖三抖”的技術能手。他的第一課,不談那些高大上的疑難病,就講誤診,就從日常工作中那些“想偏了”的故事講起。
一個老年人晚上睡覺后,家人呼不應、推不醒,連夜送到急診。醫生判斷,處于昏迷狀態一定有重病,于是開了各項檢查,卻找不到病因。直到早上6點,老人突然醒來,一臉詫異:“我怎么在這里?”原來,他只是吃了兩片安定藥。
“醫生要不斷給自己提問題,為什么是這種表現?會不會誤診?”他形容,醫生的工作狀態是“如履薄冰”,必須強迫自己突破現有的臨床思維和認知。這門課程后來成了王牌課。
他常聽到病人抱怨:“這個病在縣醫院沒診斷出來,來了您這兒才知道是為什么。”孟慶義幫同行解釋:“縣醫院的醫生也不是水平差,你的疾病在早期沒有明顯表現。”他的正確診斷是在前人的診斷基礎上作出的,不能貶低前人的診斷。
醫學領域仍有許多謎題,等待解開。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每隔兩個月,就有一群醫生聚在一起,分享臨床上遇到的“謎題”。各家醫院的醫生輪番上臺,講述他們經手過的疑難病例。他們介紹自己的經驗時,也能夠接受同行的審視。這過程中也不乏有案例初診存在漏診、誤診,隨著患者病程進展,醫生才逐漸梳理出患者的主要疾病以及同時存在的其他疾患。
這樣的研討會至今已經辦了幾十屆,吸引了北京各大醫院的急診科醫生,如今還有專科醫生參與。他們定期坐在一起,沒有藩籬地討論彼此的誤診經歷,并在日后極力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敢于面對誤診、漏診的醫生不少,但敢于開口的醫生是少數。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急診危重癥中心主任米玉紅曾給《臨床誤診誤治》雜志投稿,寫她在急診接觸的一位右肺動脈缺如的病人,初診被誤診為肺栓塞的過程。推動她大膽公布案例的動力是,她對自己專業水平有自信,想借此機會提醒同行:“我研究肺栓塞17年,我知道大家共同的難點在哪。”
但對于更年輕的醫生來說,公開談論誤診需要極大的勇氣。大多醫生更愿意關起門來,在行業內小范圍地討論誤診。這種“避之不談”的氛圍,也影響了陳曉紅的研究。早年,在醫學期刊發論文,能幫助醫生評職稱,這一度讓陳曉紅不愁稿源。但最近幾年,基礎研究、課題研究更容易受到重視。《臨床誤診誤治》雜志里,真正與誤診有關的文章越來越少。
她鼓勵更多醫生敢說,勇敢真誠地貢獻臨床上的誤診經歷。只有這樣,才能廣泛地搜集到最新的誤診案例。陳曉紅依然走在這條少有人走的路上。她能看到前方最光亮的地方,是醫生接診時,隨時用上她攢了30多年的誤診病歷和總結出的規律。
即便到了現在,醫學界依然在“誤診有沒有學”方面有爭議。有的醫生堅持誤診無學,只有醫生零散的臨床經驗總結。但孟慶義卻認為,“誤診是高級學問”,它應該成為醫學研究那顆皇冠上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