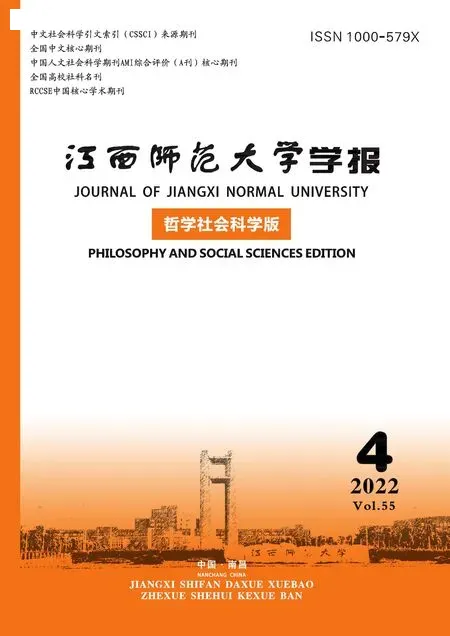晚清西學東漸的譯寫選擇及邏輯轉向解讀研究
何 娟, 余炫樸
(1.東華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西 南昌 300013;2.南昌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江西 南昌 300032)
“西學東漸”是歐風美雨狂潮下我國近代社會的文化發展主線。如何向西學習,局部開展還是全盤吸收?如何選擇譯介材料,偏兵工技術還是重制度變革?如何選擇譯書來源,翻“西書”還是譯“東書”?晚清社會朝野上下面對著種種迷茫與選擇,這是此前康乾盛世乃至漢唐繁榮鮮有遇到的,這也體現在社會轉型期的中西語言文化知識選擇、譯介知識的來源傾向、組織立會、設立學堂、開辦書局、創刊辦報等方面。有關清末民初或晚清翻譯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教士在華翻譯活動[1]、晚清文學翻譯、翻譯文學的文體演變、民族情結及目的與功能[2]、晚清法律翻譯和移植對語言、觀念、文學、社會的影響及知識范式轉化[3]、翻譯政策及西學翻譯的術語民族化策略[4]、晚清翻譯對國民“軍人意識”的培養[5]、該時期翻譯課程分類、翻譯教學實施和翻譯人才培養[6]、對林紓、嚴復、梁啟超等晚清主要譯者翻譯思想、翻譯方法及貢獻的研究[7]等。上述研究成果或聚焦于特定翻譯群體的翻譯活動,或囿于某一翻譯理論視角的文本分析、翻譯特點,或專注于某一主題的翻譯內容研究等,其研究內容、研究層次、研究視角、研究對象等不斷得到拓展,這對于本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將晚清時期的翻譯活動置于社會文化系統之中,在爬梳西書翻譯邏輯起點和知識選擇的基礎上,分析其多維轉向,探賾其深層的社會文化動因。
一、晚清譯寫主題的邏輯發展
19世紀末,面對外侮日亟、國勢日非的危局,晚清社會在空間自縛與迷茫彷徨中憂慮中國發展走向何方。作為儒學道統、禮制和知識的產兒,志士仁人憂國憂民、直面中國社會的縱深發展,他們在探尋西方文明興衰根源的過程中發現“泰西何以強?有學也,學術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國何以弱?失學也,學皆無用,雖有亦無也”[8](p411);在省察傳統政治知識危機中認識到“天地之間獨一無二的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9](p215);在探索與斗爭中認識到國家危機中的社會轉型如果要打破因循守舊、深閉固拒,就要不斷自我調整,轉變文化態度和思想意識。晚清士人的思想轉變和文化覺醒催生了西學翻譯,翻譯內容、價值定位、贊助人系統及翻譯行為主體及其角色與分工整體勾勒了晚清西書翻譯的概貌。
(一)以輿地學為起點的采西譯夷
為探求域外情勢,了解西方歷史和地理,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早期志士“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事,又購其新聞紙,具知西人極藐水師”[10](p537-543),編譯了系統介紹世界地理志的《地理大全》和《四洲志》,概述了西方歷史、地理、政治等內容的《海國圖志》,提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力主“悉夷情”“翻夷書”“立譯館”[11](p1124),這也是晚清中國一部比較完備的世界地理百科全書。左宗棠在甘肅重刻《海國圖志》序中評價道,“該書為抵御外侮、自強之道的奇書”[12](p472),并開宗明義表示其本人開展的洋務和船政是對林、魏思想的繼承和實踐。在19世紀40年代,徐繼畬編譯出版了敘述各國史地沿革及民主政體的《瀛環志略》,梁廷枏合編了歷述西方商貿及社會概況的《海國四說》等。此類匯譯編譯打破了天朝上邦的中心地理觀,是中國近代翻譯的初潮,也為后期西書翻譯奠定了基礎,代表了晚清西學東漸的邏輯起點。
(二)以科學技術為主的格致翻譯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中西兵力懸殊,“水師船遇西洋并無軍器之商船,尚抵擋不住,何況兵船。且軍器亦多廢鐵造成,年久并未修理整新”[11](p1987)。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朝廷重臣認識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先進主要在于其器物文明。為迎合晚清時局需求,清廷自上而下地開展了自強御侮、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發起了“以中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13](p179)的譯介活動。譯者主體多來自由傳教士設立的上海墨海書館、格致書院、益智書會和廣學會中的譯書機構,部分譯者來自于同文三館、江南制造總局等官辦譯書館。翻譯內容主要涵蓋法律、機械、軍事、數理、算學、電學等實用科技知識,以及麻痹國人精神的宗教文化信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泰西水法》等一大批譯自西方的著作為促進我國科技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據《西學書目表》統計,“江南制造局首以翻譯西書為第一要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同文館及西士之設教會于中國者,相繼譯錄至今二十余年可讀之書,略三百種”[14](p3-4)。南洋公學譯書院“初以練兵為急務,故兵學居多,理財商務學校次之”[15](p518)。在所有已翻的書籍中,“中國官局所譯者,兵政類為最多”[14](p8),大都屬于晚清政府的“緊要之書”[13](p207)。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在“西譯中述”的模式下聚焦于一些順應世事的應用科技類時務書,在緩解時局危機方面功不可沒。
(三)以社會科學為主的翻譯選擇
甲午戰敗,洋務自救失利。日本明治政府自上而下地開展了一系列改革和“維新”,“以徹底的西學打敗了中國不徹底的西學。這一事實非常雄辯地為西學致強的實效作了證明”[16](p284)。國人痛感國家民族危亡,幡然醒悟到所謂的“商戰”和“兵戰”不濟“學戰”,疾呼“言兵戰、言商戰,而不歸于學戰,是謂導水不自其本源,必終處于不勝之勢”[17](p436-437)。維新派人士紛紛直陳晚清政府危如累卵,變法圖強方能破局,重在改革腐朽的封建體制,如梁啟超在《論譯書》中談及翻譯時曾提出“擇當譯之本”,主張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次輔以藝學”[18](p132)。
如果說鴉片戰爭使國人醒悟到技藝乏力不如人,那么“中體西用”思想下的洋務敗北使知識分子認識到富國強兵不能乞靈于舊有的封建制度。“要強國富兵,首先要開啟民智,只有民眾擁有了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國家才能實現真正的強大。”[14](p1)甲午戰后的翻譯活動不再止于譯介“奇技淫巧”類書籍,還翻譯了一些有關社會制度、西方新思潮以及變法圖強的法政社科類書籍以及歷史、言情、哲理、心理等不同種類的翻譯小說。有學者曾統計,晚清翻譯小說出版量由1900年前后的個位數逐年走高,并于1907年達到年出版量208種[19](p4)。除譯介西書外,各學會紛起,報館云興。“光緒二十二年,《時務報》《昌言報》《實學報》《新學報》等先后重興。諸報皆以片民易俗,汲引新知為旨,故于摘譯西報外,并議政藝、史地、天算、格致諸學。”[20](p4)
二、晚清西書翻譯的多維轉向
晚清時期的翻譯活動將中西發展錯軌地連接起來,使此時的譯介活動有別于之前的佛經翻譯和科技翻譯。一系列亙古未有的翻譯活動相繼展開,與其相關的知識體系、來源文獻、譯者數量與角色等各翻譯要素發生了不同的轉向。
(一)晚清翻譯的知識體系轉向
通過分析文獻譜系我們發現,晚清翻譯活動中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文化觀念,即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經世致用”的觀念;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自強求富”的觀念;以及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變法圖強”的觀念。鴉片戰爭之后,以義理、考據和辭章之學為主的傳統知識體系和認知框架難以化解知識權力化社會中的政治窘境,也難以消解外侮內侵的危局,催生了以經世致用為經緯的格致之學及其譯介工作。“采西譯夷”擊潰了中國“天下”的文化體系,帶來了“世界”文化的潛流,民族存亡的政治問題上升至社會重心,開明志士的價值觀悄然變化,社會傳統的知識結構開始轉向,西方輿地、制器之器、外洋槍炮等西學知識逐漸被譯介并滲透至中國傳統知識體系。洋務派“中體西用”思想下的向西學習以鞏固舊有的封建制度為宗旨,在遵從“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基礎上主張譯介西方自然科學和兵器實用知識。根據《戊戌政變記》記載:“甲午以前,我國士大夫言西法者,以為西人之長,在乎船堅炮利,機器精奇。故學之者,不過槍炮鐵艦而已。”[21](p872)
甲午戰敗進一步拷問了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西書翻譯內容再次轉向,政治、法權以及與制度相關的社科翻譯在質與量上漸漸超過了自然科技類,清末民初發起的小說界革命也給翻譯小說帶來了極大的增長空間,出現了“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于汗萬牛、充萬棟”[22](p188)之勢。此外,隨著維新運動的推進,詩歌翻譯初現端倪,散文、戲劇等不同體裁的翻譯也嶄露頭角,譯介內容由單一取向漸趨多元。譯寫知識體系的轉向是推動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成為晚清翻譯轉向的一大特點。
(二)晚清翻譯的文獻來源轉向
對應于譯寫知識體系轉向,晚清譯寫在文獻來源方面也發生了轉向。鴉片戰爭前后的西學東漸專注于“西語”,即由英美傳教士為翻譯主體的英文轉向中文的譯寫。晚清創辦的翻譯人才培養機構也以英美學制為藍本。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文件中特明文規定,“嗣后英國文書俱用英文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此次定約漢英文字詳細校對無訛,亦照此例”[23]。在商務及其他書寫文件中也有類似表述,“各種表格全用英文,進出口貨物報關,用中國文字者概不受理”[24](p532)“通行文牘亦以英文為多”[25](p174)。隨著甲午戰爭、膠州灣事件的爆發,西方列強掀起的瓜分中國狂潮迫使國人亟須了解帝國主義。在后期的譯介活動中,國人對世界的關注以及選譯材料來源已經從個別國家轉向多個國家,出現了“彼美英德法澳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采外國名儒所撰述”[26](p37-38)的局面。
譯寫文獻來源還體現在其他傳播媒介。報刊作為一種大眾媒介,對社會時局變化的反應最迅速,對西方各國的語言文化傳播力度與之前各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其中,《譯書公會報》等報社在西報選譯專欄的基礎上開始陸續增設了不同語言的報刊選譯,如法報選譯、德報選譯、東報選譯、譯書選載等欄目[27](p321),編譯、選譯西方各國書籍成為解救民族危亡的常設途徑。甲午戰爭前,日本發起了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明治維新”,開始翻譯西方著作、移植西方現代文明,在歐化的道路上實現了資產階級改革。甲午戰爭后,日本征戰中國。在強鄰環視的形勢下,時人面臨繼續向西學,還是轉而向東學的抉擇。現實催人醒,朝野上下在民族意識逐漸自覺中一致認為要學西方,先學日本,且因文字親緣而比較省時省力,“日本與我同文也,其變法至今三十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咸譯矣……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28](p223)。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也曾指出“至各種西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29](p14),轉譯日文書籍成為獲取西方知識的捷徑。中國開始效法日本,掀起了轉譯日文書的浪潮,譯介東書躍居為翻譯活動的主流。“日本文譯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學校,幾使一時之學術,浸成風尚”[30](p95)。
甲午之后,“或由政府主持,或由民間提倡,競起譯印歐美日本各國的書籍,而其中尤以譯自日文者占最多數”[30](p99)。據《譯書經眼錄》統計,“光緒末季共譯書533種,其中譯自日語的書目有321種”[30](p100-101),比譯自英、德、法文的總和還要多。另據統計,1868年至1895年間,中譯日文書目共8本,包括應用科學、世界史地等類別,年均譯書量0.29本。但是從1896年至1911年,中譯日文書籍共計958本,涉獵10種類別,年均譯書量達63.86本,詳見表1。

表1 晚清中譯日文書統計表(1868-1911)[31](p109)
(三)譯者數量及譯者角色轉向
回首中國歷次翻譯高潮,無論是佛教文化初入中土、明末清初科技翻譯,還是晚清時期的“夷學”翻譯,各時期初始階段的翻譯活動基本都是通過中外翻譯行為主體合作完成的,衍生出“西譯中述”的翻譯模式,即西人執翻譯牛耳,國人負責記述并潤色,如鴉片戰爭前后的格物致知之學翻譯,同文館的公法翻譯,江南制造總局的制器之器翻譯,墨海書館、光學會等機構的宗教和科技翻譯等,各類主題翻譯大都呈現出以傳教士為翻譯主體,中國學者為翻譯輔助的模式。隨著社會文化環境變化,語言交際活動頻仍,熟練掌握外語者人數增多,社會場域內的中西翻譯行為主體漸趨平分秋色。其中,李善蘭、徐建寅、華蘅芳等成為主要的西學譯寫力量。甲午戰爭后,中國譯者數量劇增,譯者角色發生了主導與被動的逆轉,西方譯者逐漸缺席或失語,這種變化從當時的翻譯著作數量上可窺見一斑。據《譯書經眼錄》記載,甲午戰敗后,中國譯者約300人,他們均具有較系統的知識結構和較強的中外語言文化水平。較之于甲午戰爭之前,甲午戰爭后的翻譯規模和譯作數量大幅增長[30](p95)。
從總體來看,西學東漸以我國達官顯臣中的有識之士和西方傳教士為主體,譯者數量的變化和譯者角色的逆轉折射出該群體所處的社會文化境遇,即譯者是中西思想、文化交流與發展的建構存在,譯者角色既是一種具體的權力形式,也是社會對其認知的一種心理表征和態度,譯者行為的產物即譯作是國富民強的文化密碼。晚清譯者的數量變化及角色轉向彰顯了翻譯活動的跨民族、跨國界、跨文化的整體特點,也跳脫了由傳教士把控的誰主譯、如何譯的敘事窠臼。
三、晚清西書翻譯轉向的邏輯動因
在歷史情境和社會文化系統中,任何翻譯活動并非在“真空”中發生的,文本信息的譯寫不僅受特定的認知體驗以及文本背后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等內容的影響,還受特定歷史文化傳統或社會文化語境的影響[32]。晚清時期的西書翻譯被視作救亡和啟蒙的重要途徑,西學的引進為當時有識之士所重,并被上升到國家民族新生的高度,豐富和發展了中國語言文化。晚清翻譯過程潛含了明顯的社會文化態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等因素的過濾特征,也承載著政治規約下的社會功用取向。
(一)社會文化態度
晚清的西學東漸路線迂緩曲折。鴉片戰爭后的政治軍事失利折射出傳統知識的危機,也使統治階級、洋務派、頑固派、維新派等對西學持不同的文化態度,進而在翻譯這一語言轉換和文化交流的媒介中也有體現。主政者掌控話語權和知識的解釋權與支配權,他們在選擇知識的過程中將格致之學作為向西學習的核心內容,官紳及洋務人士在實用主義標準下主動向西方學習并譯介軍事武備和實用工藝類書籍,但所有的翻譯活動旨在迎合社會發展情勢,漠視了知識體系的銜接性和完整性。傳教士傅蘭雅曾坦言到,“本欲作大類編書,按西國門類分列”,完整地翻譯“更大更新”的西學知識,但最后只得“與華士擇合其所緊用者,不論其書與他書配否”[13](p207)。對于頑固派而言,夏夷思想和綱常名教占據主導,西人茹毛飲血的蠻夷形象植根于華土王者榮耀的內心深處,文化優越性的文化身份自居、知識權力化的社會背景或者說知識與權力的同構同形左右著西學書籍的譯介活動。以大學士倭仁為代表的士大夫仍以中國傳統倫理準則為圭臬,推崇八股辭賦,非議他者文化,反對異域新知對中國傳統知識的沖擊和解構,認為“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13](p206)。以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維新派對西書翻譯主張“中體西用”,堅持翻譯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對西方的學習由器物、實用層面轉向理論和制度層面。
從總體來看,晚清時期的西方堅船利炮擊潰了傳統社會對西方社會及其語言文化的整體認知,西學東漸的開展和深入是一場將中國社會發展寄托于異域他國新知的社會文化活動。不同行為主體的文化態度代表了特定的社會文化取向,進而對翻譯活動及其作用具有不同的文化認知。
(二)社會意識形態
翻譯是語言信息的傳輸活動,也是文化信息的交流活動,還是一個多元綜合且裹挾了政治、經濟、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實踐活動。“翻譯從來就是一種有目的的行為。在階級社會,當翻譯不可避免地同上層建筑發生關系之后,翻譯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會的精英階層在從事翻譯活動時,他們的目的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33]解構主義借用“權力話語”的理論闡釋了翻譯活動的意識形態影響因素,其中,權力話語操縱下的翻譯活動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目的。晚清翻譯活動不可避免地折射了意識形態的操控,并由此經歷了自發翻譯和自覺翻譯兩個階段。
早期文化自戀或文化自居實則具有強烈的文化排他性[34],翻譯活動主要傾向于自發譯寫,林則徐、魏源等開明人士組織贊助了零星的西書翻譯活動,他們是“促進或阻礙文化作品的閱讀、創作和改寫的力量”[35](p15),客觀上助推了西學東漸的開啟,也促進了社會發展的進程,但個體意識形態主導下的翻譯活動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和局限性,其影響力遠未觸及社會的深處。洋務運動時期,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以恭親王奕昕、朝廷官員文祥以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官員組建的政治共同體主張的“制器”“洋務”“新政”,成為當時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他們創設了官辦翻譯機構,放棄了傳統文化優越與自身價值至上的舊有觀念,開始全面接受域外文化,逐漸提升了翻譯活動的社會認同。滿足時局需要的“緊要”“新書”譯介使翻譯活動逐漸步入自覺階段,其組織性得到較大提升,但其系統性還略顯乏力。康有為托古改制、主張變法,在批判傳統制度文化的基礎上崇尚西方制度文化。維新派建設新制度和新體制的意識形態對晚清制度文化翻譯影響頗深。無論是自發翻譯還是自覺翻譯,晚清時期的西學東漸對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發展帶來了猛烈的沖擊,其中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對翻譯行為主體、翻譯選材、形式、規模、知識體系、譯書語言及其縱深發展都有極大的影響。
(三)社會功用取向
晚清的西書翻譯家大都肩負救國保種的時代責任,首先重視翻譯的社會功用,次而顧及其他需求。甲午之前的翻譯活動注重對西方國家報刊著作的摘、改、述和轉等多種“致用”性的翻譯形式,內容多側重西方政治、歷史、地理以及一般性的海防軍事知識介紹。從翻譯機構來看,當時成立的大都是編譯館(所),如1894年湖北譯書局的開辦拉開了西書編譯事業的帷幕,管學大臣張百熙在設置籌備所時附設編譯所,民國初期在教育部審定處基礎上改設了“國立編譯館”等。無論是鴉片戰爭前的輿地學譯介,還是“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洋務運動派組織的西書譯介,都采用編譯的形式,所譯書籍大多為滿足社會需要的時務書。不可否認的是,以編譯為主的譯寫形式因缺乏知識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未免會有遺漏西學精華之憾,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危如累卵的晚清時局。
此外,當時創辦的一批有影響力的報刊,或介紹異域文化,或譯介西方科技知識,或匯萃中外公法,或倡導思想啟蒙。這些西書報刊以編譯的形式從原文中選取部分內容,具有明確的文摘功能,不僅給晚清國人帶來了新知,也開拓了他們的文化視野,外國文學的選擇性借鑒或引進無疑也改革了中國文學,實現了文學的社會功用[36](pix)。在威脅與機會并存的晚清社會,以“編譯”“摘譯”“改譯”“述譯”和“轉譯”為主的譯寫形式及其輻射的翻譯自發向自覺階段的演變為中國文化發展帶來了后發外生型動力,西學譯介和西方文化的引進激發了中國文化的內生型動力,迎合了滿足時局發展的社會功能。
四、結語
翻譯史研究不僅要挖掘相關史料、探討譯寫特點,還要將翻譯活動放眼于特定的社會情境中描述其翻譯現象、分析其翻譯特點,并解釋翻譯的社會起因等問題[36](pix)。晚清西書翻譯以輿地翻譯為邏輯起點,經由科技翻譯、社會制度、西方思潮及變法圖強等內容的翻譯演變勾勒了他者文化與我族文化在交流交融中和社會時局需要的耦合軌跡。
翻譯活動的知識選擇變化旨在解構和重構“天下”文化體系以適應“世界”文化潮流的需要,其譯寫主題的邏輯發展以及譯寫知識體系、來源文獻的轉向整體反映了從知識不足、器物不足、制度不足到文化不足的文明認知過程,其譯者數量及角色的轉向體現了自發翻譯向自覺翻譯轉變。在橋接多元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翻譯催生了晚清社會的文化心態變化,夷夏觀念操控下的文化自戀在西學譯寫的沖擊下經歷了文化覺醒和文化自省。譯寫選擇及其邏輯轉向體現了特定歷史境遇下翻譯與社會文化系統的互動共生,其社會在場通常是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政治文化權力(political-cultural power)的反映,也是社會文化系統中社會意識形態、社會文化態度及社會功用取向等各文化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作用并非線性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具有立體交織的多重作用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