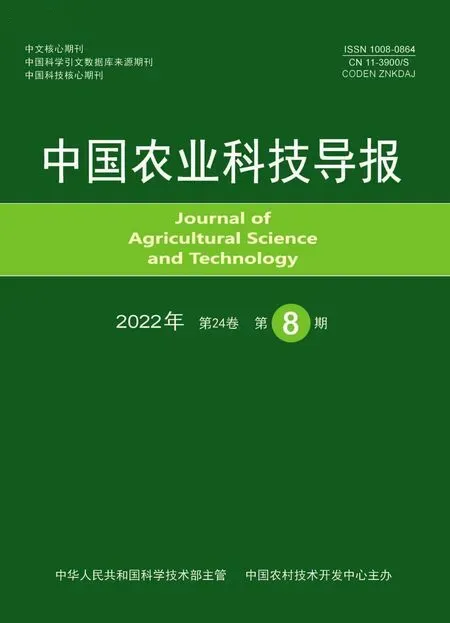機采棉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光合特性及干物質積累的影響
李玲, 董合林, 李鵬程*, 田立文, 李春梅, 馬云珍, 張娜, 王芳, 徐文修*
(1.新疆農業大學農學院, 烏魯木齊 830052;2.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 棉花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河南安陽 455000;3.新疆農業科學院經濟作物研究所, 烏魯木齊 830091)
新疆是我國主要商品棉生產基地, 2019年棉花種植面積達254.05萬hm2, 占全國棉花總種植面積的76%, 棉花總產500.2萬t, 占全國棉花總產量的85%[1]。隨著人工拾花成本的不斷增加, 新疆棉花機械采收發展迅速, 北疆主要產區棉花機械采收率已超過90%, 南疆機采棉發展相對較慢, 機械采收率在30%左右[2]。機采棉降低了棉花生產成本, 大大提高了棉農的經濟收益[3]。目前新疆機采棉的種植方式主要有一膜六行、一膜四行高密度種植方式[4], 近年來一膜三行76 cm等行距種植方式也得到小范圍的應用[5]。新疆棉花品種繁多, 株型結構多樣化, 在不同種植方式下, 受株行距配置的影響, 棉花生長發育及產量表現不同。但是, 在生產中棉農并未針對不同株型棉花品種而選擇適宜的種植方式, 使得棉花生長發育潛力未能充分發揮, 因此研究不同株型機采棉品種(品系)適宜的機采種植方式以提高產量就顯得尤為重要。
種植方式對作物生長發育影響很大, 在合理的種植方式下, 作物群體光合輻射分布合理、葉面積指數得到提高、光合性能增強, 干物質量增加進而獲得高產[6-9]。周永萍等[10]研究認為, 密度75 000株·hm-2條件下的(100+50)cm大小行種植和75 cm等行距種植方式可以提高單株鈴數、籽棉產量和總生物量, 是黃河流域棉花較為適宜的種植方式。近年來, 眾多學者對新疆地區棉花種植模式進行了研究比較, 有學者認為低密度76 cm等行距模式相對于(66+10)cm寬窄行模式更能提高株高、葉片數、葉面積指數、果枝數、單株結鈴數和產量[11-16], 但也有人認為(66+10)cm模式比76 cm等行距模式更能提高棉花葉面積指數和光能利用率, 從而實現高產[17]。有關不同類型棉花適宜種植方式的研究表明, 雜交棉在低密度76 cm等行距條件下能充分發揮雜種優勢, 產量較高[18], 而常規品種雖然在低密度等行距種植方式下具有較強的個體優勢, 但依舊需要高密度寬窄行模式來彌補群體的劣勢從而提高產量[18-19]。前人對不同株型棉花進行了種植方式的比較, 但因為種植密度、行距配置等不同, 結論不一致。阿不都卡地爾等[20]研究認為, 緊湊型和松散型棉花均在一膜四行(64+12)cm模式下具有較高的單株結鈴數、單鈴重和產量;但李健偉等[21]的研究結果則表明, 松散型品種和緊湊型品種分別在一膜三行、一膜六行種植方式下產量最優。目前與機采棉種植方式相關的研究多基于不同種植密度[22-23], 且以單一棉花品種為材料[11-14], 有關棉花株型與機采棉種植方式相適應的研究報道較少, 尤其缺乏機采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光合能力及干物質積累影響的研究。因此, 以新疆南疆為研究區域, 研究不同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光合特性、干物質積累特征及產量形成的影響規律, 為明確不同株型棉花適宜的機采種植方式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2019年、2020年的4—10月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阿拉爾市十團, 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阿拉爾試驗站進行不同棉花品種的機采種植方式的田間試驗。試驗地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 屬于暖溫帶大陸性氣候, 年均氣溫10.43℃, 年均日照2 556.3~2 991.8 h, 年均降水量40.1~82.5 mm, 年均蒸發量1 876.6~2 558.9 mm。試驗地土壤為沙壤土, pH 7.68, 有機質含量10.58 g·kg-1, 堿解氮含量84.87 mg·kg-1, 速效磷含量25.38 mg·kg-1, 速效鉀含量190.5 mg·kg-1。
1.2 試驗材料
供試材料選用2種株型差異較大的品種(系), 分別是中棉所96A(Zhongmiansuo 96A,簡稱ZMS96A, 植株稍松散呈筒形、Ⅱ式果枝)和B9(株型緊湊, 果枝較短), 由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提供。
1.3 試驗設計
采用雙因子裂區試驗, 主因子為品種, 副因子為種植方式, 在同一理論密度22.5萬株·hm-2下, 設3種種植方式(圖1):①一膜三行, 76 cm等行距, 株距6 cm(R3);②一膜四行, 單雙行, 平均行距57 cm, 株距8 cm(R4);③一膜六行, 寬窄行, 平均行距38 cm, 株距12 cm(R6)。各處理重復4次, 共24個小區。膜寬2.05 m, 2019年、2020年各小區面積分別為61.56 m2(6.84 m×9.00 m)、66.35 m2(6.84 m×9.70 m)。2019年播種和收獲日期分別為4月19日、10月2日, 2020年播種和收獲日期分別為4月21日、10月10日。每年全生育期灌水均為4 500 m3·hm-2, 灌溉方式為膜下滴灌。每年結合播前整地均基施尿素225 kg·hm-2, 磷酸二銨300 kg·hm-2。追肥隨水滴施, 2019年、2020年分別 追 施 尿 素150、255 kg·hm-2, 磷 酸 二 銨270、300 kg·hm-2, 磷酸二氫鉀112、165 kg·hm-2, 其余田間管理與當地棉田一致。

圖1 種植方式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nting mode
1.4 測定項目與方法
1.4.1 農藝性狀 于吐絮期(2019年9月15日, 2020年9月20日)在各處理選取具有代表性的10株棉花調查株高(子葉節至生長點的高度)、果枝始節位(棉花始果枝的著生節位)、果枝始節高度(子葉節至始果枝的高度)、主莖節數、果枝長度、果枝數, 并計算平均節間長。

1.4.2 葉面積及干物質2019年自棉花出苗后第25天開始, 每隔15 d取樣1次, 至吐絮期結束, 各小區選取具有代表性的3株棉花(為防止生育后期棉株葉片等脫落, 從鈴期開始用可透光網兜對棉株進行套袋供后期取樣), 重復3次, 取樣后立即裝入塑料袋帶回實驗室, 將地上部分植株按莖、葉、蕾花(鈴)等器官分開, 將葉片平鋪于白色平臺上, 旁邊放置標尺, 然后拍照, 利用Image Pro Plus軟件對得到的圖片進行分析計算單株葉面積[24], 并計算葉面積指數(leaf area index, LAI)。2020年因疫情原因, 干物質數據不全, 且未收集葉面積數據。

拍照后將植株樣放入105℃烘箱殺青30 min, 80℃烘至恒重, 冷卻后測定其干物質重。利用Logistic曲線對棉花干物質積累進行擬合[25]。

式中,Y為干物質積累量,K為理論最大積累量,t為生長天數,a、b為待定系數,e是自然常數(e=2.718 281 82)。將K、a、b代入公式(4)至公式(8), 求得相應特征參數:快速積累期起始時間(t1)、快速積累期終止時間(t2)、快速積累持續期(Δt)、最大積累速率出現時間(tm)、最大積累速率(Vm)。

1.4.3 凈光合速率 于現蕾期(2019年6月9日, 2020年6月1日)、盛蕾期(2019年6月27日, 2020年6月20日)、盛花期(2019年7月16日, 2020年7月7日)、盛鈴前期(2019年8月6日, 2020年7月25日)及盛鈴后期(2019年8月22日, 2020年因疫情原因數據未獲得), 選擇晴朗無風的天氣, 于當天11:00—13:30之間, 每個小區選取3株長勢一致的棉株, 重復3次, 在自然光源下利用CIRAS-2光合儀, 測定棉花功能葉(打頂前倒4葉, 打頂后倒3葉)的凈光合速率(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
1.4.4 產量 于棉花吐絮期(2019年9月15日, 2020年9月20日)調查收獲株數和總成鈴數, 并計算單株成鈴數。各個小區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植株, 分別取植株下部(1~3果枝)、中部(4~6果枝)、上部(7以上果枝)吐絮鈴各20個, 重復3次, 進行鈴重測定并計算衣分, 產量以實收計產。
1.5 數據處理
采用Excel 2010、Origin 8、SPSS 19.0進行數據統計及分析, 方差分析采用Duncan法。
2 結果與分析
2.1 機采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農藝性狀的影響
由表1可知, 種植方式對棉花株高、果枝始節高度、平均節間長、平均果枝長、果枝數均存在顯著或極顯著影響, 而果枝始節位主要由品種決定。相同種植方式下, 緊湊型B9的果枝始節高度、平均果枝長均小于松散型中棉所96A。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2年的株高、果枝始節高度、平均節間長、平均果枝長平均值分別比R4處理、R6處理的高出12.04%、13.97%, 5.01%、5.29%, 10.17%、8.33%, 7.89%、14.89%。B9在R3處理下2年的株高、果枝始節高度、平均節間長、平均果枝長平均值分別比R4處理、R6處理的高出1.63%、4.62%, 8.78%、17.78%, 1.20%、7.69%, 24.97%、21.14%。2年2品種(品系)的株高、果枝始節高度、平均節間長、平均果枝長均以平均行距最大的R3處理最高, 說明同一種植密度下, 隨著平均行距的增大, 植株生長旺盛。

表1 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植株形態指標的影響Table 1 Effects of planting patterns on morphological indexes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of cotton
2.2 機采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葉面積指數的影響
由圖2可知, 2個品種(系)棉花各處理的葉面積指數均隨生育進程推進呈先增再降的變化趨勢, 各處理LAI最大值出現時間均在苗后100~115 d, 中 棉 所96A各 處 理 的LAI峰 值 在5.08~5.25之 間, B9則在5.37~5.96之間, 至 苗 后130 d, 2個品種(系)LAI均表現為R3>R4>R6。進一步比較同一品種(系)不同種植方式可知, 在苗后55~130 d, 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的LAI基本上始終高于其他2種種植方式。B9在苗后55~100 d, R3處理、R6處理的LAI明顯高于R4處理;苗后115 d, B9在R4處理下的LAI略有上升趨勢。綜合來看, 松散型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 生育前期能保持較高的LAI, 生育后期LAI下降緩慢, 有利于增大光合作用面積, 從而利于光合產物的形成和積累;而緊湊型B9的LAI在苗后115 d之前以R6處理較高。

圖2 2019年不同株型棉花葉面積指數變化Fig.2 Changes of leaf area index of cotton with different plant types in 2019
2.3 機采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光合速率的影響
表2表明, 2年2種棉花各處理的凈光合速率(Pn)均隨著生育進程的推進呈現先升后降的變化趨勢,Pn峰值均出現在盛蕾期至盛花期。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的Pn在盛蕾期至盛鈴前期基本始終高于其他2種種植方式, 且R3處理2年的凈光合速率均值最大, 為33.21μmol·m-2·s-1, 分別比R4處理、R6處理的高出3.62%、1.93%。緊湊型棉花B9在現蕾期至盛鈴后期, R6處理的Pn基本始終高于其他2種種植方式, 其2年Pn均值為33.60μmol·m-2·s-1, 分別比R3處理、R4處理高出4.25 %、4.32 %。綜合來看, 進入生殖生長后, 松散型棉花中棉所96A和緊湊型棉花B9分別在R3、R6種植方式下有利于保持較高的光合能力, 進而增加光合物質積累量, 為提高產量打下基礎。

表2 2019—2020年不同株型棉花凈光合速率Table 2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of cotton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from 2019 to 2020(μmol·m-2·s-1)
2.4 機采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干物質積累特性的影響
2.4.1 單株干物質積累特性 由表3可知, 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的單株干物質快速積累期起止時間較早, 快速積累持續期比R4處理和R6處理少3 d左右, 最大積累速率出現時間比R4處理和R6處理提前9 d左右;各處理的最大積累速率均為1.51 g·株-1·d-1, 不存在差異。緊湊型棉花B9在R6處理下的干物質快速積累起止時間較其他種植方式有所提前, 最大積累速率出現時間提前4 d左右, 最大積累速率為1.65 g·株-1·d-1, 比R3處理、R4處理分別高出14.58%、8.55%。綜合來看, 在干物質快速積累速率起止時間和最大積累速率出現時間提前的基礎上, 增加干物質最大積累速率有利于增大單株干物質積累量。

表3 2019年不同株型棉花干物質積累特征值Table 3 Eigen values of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in different plant types of cotton in 2019
2.4.2 營養器官干物質積累 由表4可知, 對于中棉所96A而言, 其營養器官干物質最大積累量以R3處理最大, 為41.56 g·株-1, 比R6處理高出6.81 %;且R3處理的快速積累結束時間最早, 積累持續期最短, 但最大積累速率最大, 為1.09 g·株-1·d-1, 比其他2種種植方式分別提高了31.33%、43.42%。緊湊型棉花B9在R6處理下, 營養器官干物質積累最大值最高, 為40.18 g·株-1, 快速積累持續期最短, 但最大積累速率最大, 為1.21 g·株-1·d-1, 比R3、R4處理分別高出6.14%、27.37%。研究表明, 松散型中棉所96A和緊湊型B9分別在R3處理、R6處理下營養器官干物質最大積累速率提高, 并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最大的營養器官干物質積累量, 為提早進入生殖生長、增加生殖器官干物質積累量奠定了基礎。

表4 2019年不同株型棉花營養器官干物質積累特征值Table 4 Eigen values of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in vegetative organs of cotton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in 2019
2.4.3 生殖器官干物質積累 由表5可知, 與其他2種種植方式相比, 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的生殖器官干物質快速積累起始期提前, 快速積累結束時間推遲4~5 d, 快速積累持續期延長了5 d左右, 生殖器官干物質最大積累量最高, 達到62.31 g·株-1。由此可知, R3種植方式有利于松散型中棉所96A提早進入生殖生長, 并延長快速積累持續期進而增加棉花生殖器官干物質的積累量。B9在R6處理下的生殖器官干物質最大積累量為62.77 g·株-1, 較其他2種種植方式分別提高了8.52%、4.23%。與R3處理、R4處理相比, B9在R6處理下的快速積累起始期提前2 d左右, 快速積累持續期延長2 d左右。B9雖然在R4處理下具有較高的最大干物質積累速率, 但其快速積累持續期短, 干物質積累量不如R6處理。因此, R6種植方式更有利于緊湊型棉花B9生殖器官干物質快速積累期的延長, 增加干物質量。

表5 2019年不同株型棉花生殖器官干物質積累特征值Table 5 Eigen values of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in genital organs of cotton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in 2019
2.5 機采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產量及產量構成因素的影響
2年數據(表6)顯示, 品種(系)、種植方式及兩者互作對棉花產量均有極顯著效應, 其中單株鈴數是差異形成的主要因素。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的單株鈴數最高, 并與R4處理、R6處理呈顯著性差異, 其籽棉產量顯著高于R6處理, 與R4處理、R6處理相比分別增產4.76%、6.73%。B9在R6處理下的單株鈴數最高, 籽棉產量也以R6處理最高, 且與R3處理、R4處理差異顯著, 2年籽棉產量與R3處理、R4處理相比分別提高了9.00%、12.16%。

表6 不同株型棉花產量及產量構成因素Table 6 The yield and yield components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of cotton
3 討論
種植方式對不同株型棉花植株形態的影響不同。本研究結果表明, 同一密度下, 種植方式對棉花株高、果枝始節高度、節間長度、果枝長度均有一定程度影響, 而果枝始節位受種植方式影響不大, 主要由品種(系)決定, 這與李建偉等[26]研究結果相同。楊培等[27]研究了等密度下機采棉不同種植模式, 發現種植密度相同時, 棉花株高、果枝始節高度均隨著行距的增大而增加。本研究也證明了這一結果, 2個品種(系)的株高、果枝始節高度、平均節間長、平均果枝長均以行距最大的R3處理最高。行距大, 行間通風好, 光線充足, 而且植株間養分競爭也較小, 有利于棉花植株的生長。
葉片是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場所, 適當的葉面積指數可以增加葉片對光能的吸收利用[28]。本研究中, 2種棉花LAI峰值不同, 中棉所96A的LAI峰值范圍在5.08~5.25, B9的LAI峰值較高, 在5.37~5.96之間。本試驗中的最大LAI比以往研究的棉田最大LAI范圍4.8~5.4[29]高, 可能是由于本試驗采用的掃描圖像處理法更精確。葉片光合能力是決定產量的重要因素, 棉花在盛蕾期至盛花期具有較高的單葉凈光合速率[30]。本研究結果表明, 各處理棉花功能葉Pn在盛蕾期至盛花期達到最大值, 松散型中棉所96A和緊湊型B9分別在R3處理和R6處理下保持較高的Pn, 可能是由于作物株型差異影響了群體光截獲能力和光在冠層中的分布, 從而影響作物光能利用率[31]。松散型中棉所96A在R6處理下由于行距減小, 果枝、葉枝相互遮蔽嚴重, 進而增加了植株間對光的競爭, 降低了光能利用率;而B9由于本身株型緊湊, 在R3處理、R4處理下, 行距較大, 行間漏光嚴重, 對光資源造成浪費, 在行距減小, 株距增大的R6處理下, 冠層光合有效輻射分布更均勻, 從而提高了光合速率。
在農業生產中, 調整種植方式是改善群體光溫環境進而影響作物生長發育、光合物質生產并最終決定產量的重要手段[32-33]。徐新霞等[32]研究結果表明, 一膜六行(66+10)cm種植方式下的棉花比一膜六行(72+4)cm種植方式的更早進入生殖生長并延長生殖器官快速積累期進而增加干物質積累量。阿不都卡地爾等[20]研究認為, 與高密度一膜六行相比, 松散型棉花和緊湊型棉花均在低密度一膜四行種植方式下生物量累積特征值較協調, 各器官分配比例較合理。本研究結果表明, 松散型中棉所96A和緊湊型棉花B9分別在R3和R6處理下具有最高的營養器官、生殖器官干物質積累量, 這是因為中棉所96A的R3處理比B9的R6處理的營養器官干物質積累起始時間提前, 最大積累速率最高, 干物質量在短時間內積累到最大值, 為提早進入生殖生長并延長生殖器官快速積累持續期從而增加鈴重奠定了基礎。李健偉等[21]研究表明, 同一密度條件下, 株型松散型新陸中54號在一膜三行下單株結鈴數和單鈴重表現較好, 增產顯著, 更適合一膜三行種植方式, 而緊湊型新陸中75號不適合一膜三行種植模式, 這與本研究結果類似。本研究結果表明, 松散型中棉所96A在R3處理下具有較高的單株鈴數和籽棉產量, 緊湊型B9則在R6處理下單株鈴數最高, 相較于其他2種種植方式增產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