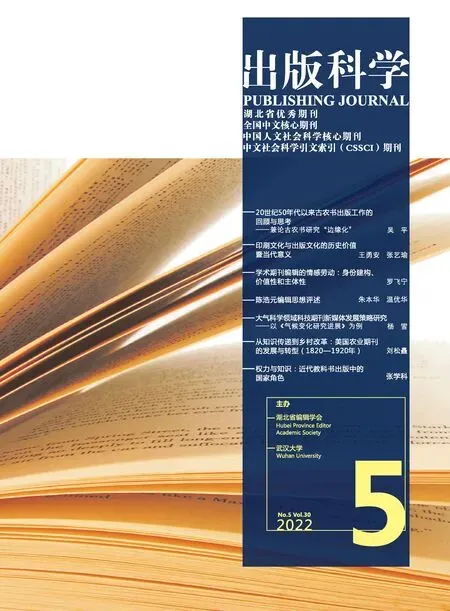20世紀50年代以來古農書出版工作的回顧與思考
—兼論古農書研究“邊緣化”
吳 平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武漢,430072)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古農書是中國傳統農業精髓的重要載體,是古籍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黨和國家對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也是對古農書工作的意見。因此,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古農書在新時代應當加強而非削弱,應當深入而非停滯,應當活化利用而非僅僅藏之館閣。只有充分繼承、吸收中國古代農業科學實踐經驗,發揚古代農業科學家探索精神,多渠道搜集、豐富古農書文獻,多方法匯編整理已有典籍,多視角揭示、建立中國古農書知識體系,方可“深入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加強古籍搶救保護、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進古籍事業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
古農書是農業古籍的俗稱,即指1912年以前(不含1912年)論述農業生產以及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古代文獻。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我國古農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聚焦于古代農業文獻的輯佚校注、書目編制、分析評價、作者作品等取得了豐碩成果,在農業文化遺產總結、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從本世紀開始,伴隨著農史研究的‘社會經濟史’轉向,古農書研究逐漸邊緣化:一方面,它們不再作為‘農業文化遺產’概念的核心,另一方面,它們也不再是農史學者主要依靠的史料”。這里所說的“邊緣化”應是一個相對概念。雖然研究領域的轉向與邊緣化并非因果關系,但該觀點在古農書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無論古農書搜集整理還是編撰出版,近年來研究隊伍年齡偏大,重大研究成果不多,出版數量減少,研究者在非史學非考古、似冷門非絕學的情境中感受到邊緣化的壓力。且社會發展越快,科學技術越先進,信息網絡越發達,這種感受越強烈。古農書出版情況是“邊緣化”論點的重要佐證。但學界、農史研究領域缺乏古農書出版的準確數據。為此,本文擬準確統計、回顧總結20世紀50年代以來古農書的出版情況,縱向對比,橫向分析,厘清“邊緣化”一說之緣由,揭示其背后的真實含義。其最終目的是倡導加大古農書搜集整理力度,出版更多的古農書研究成果,扼制邊緣化。更希望從古農書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中,增強全民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成為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1 新中國成立為古農書出版提供了有利環境
古農書研究邊緣化、日漸式微是相對于過去得到的重視、取得的成就而言的。新中國成立為古農書出版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環境。
1.1 國家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視也就是對古農書出版的重視
古農書是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古籍出版工作包括古農書的出版工作。自新中國成立,古農書出版與古籍出版管理緊密相連。古籍出版的繁榮與衰弱都會對古農書出版產生影響。古農書的出版與先后調整、更名的“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以及各機構制訂的出版規劃等密切相關。有了機構、有了規劃,才有落實規劃的出版單位。黨和政府對古籍工作的重視,直接影響了國家出版規劃、中華書局、各科技出版社或農業出版社的出書計劃,在上述組織、機構、出版單位的重視下,才有了古農書出版系列成果。從另一方面說,設置了管理部門,制訂了五年或八年規劃,依靠一批作者、團隊和出版機構,古農書的出版順理成章。
1958年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北京成立,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明確古籍整理出版的六個重點任務:整理和出版中國古代名著基本讀物;出版重要古籍的集解;整理和出版總集或叢書;出版古籍的今譯本;重印、影印古籍;整理和出版閱讀和研究古籍的工具書。同年4月,文化部調整中華書局等出版社的業務分工,決定中華書局為主要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其出版方針和計劃受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指導,同時,明確其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事機構。從1959年至1961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出版了多部古農書孤本或珍本,如《天工開物》(崇禎十年本)、《便民圖纂》(萬歷本)、《救荒本草》(嘉靖四年本)以及《授衣廣訓》(嘉慶原刻本)等等。1959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提出了“中國古農書叢刊選題計劃(草案)”,征求意見的同時落實出版計劃。《汜勝之書輯釋》《汜勝之書今釋》《農政全書校勘》《齊民要術》《農桑經校注》《種藝必用》《四民月令校注》《陳旉農書校注》等多部古農書校注著作問世。就在古籍整理、農業文化遺產總結得到最佳發展的時機,“文化大革命”按下了“暫停鍵”,這一切都停頓了下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再次出現是21年后。1960年,“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調整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經中宣部批準后下發各地。1981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通知》。1982年3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召開,隨后,農業部討論制定了農業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3年,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成立。1993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更名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隨之,《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出臺。1999年,世紀之交前夕,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顧問改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顧問。這是新聞出版總署根據國務院機構設置的通知和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的規定做出的調整。自此,“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代表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管理的最高部門行使制定、組織實施古籍出版規劃,資助項目審定、資助金額分配及其他重大事項等。從新中國成立到2000年以前,古籍整理出版機構做過三次調整,其“前綴”從“國務院”到“國家”再到“全國”,似乎只是主體、領導體制上做了一些改變,但反映出國家對古籍整理出版領域工作反復思考的過程和結果。正因如此,2000年以前的古農書整理出版工作成效明顯。
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進一步加強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利用現代印刷技術,推進古籍影印出版工作”,這是進入新世紀后,國家啟動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對古籍再生性保護提出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全國古籍,包括古農書的搶救整理與影印出版進入新階段。
1.2 黨和政府對農業文化遺產的珍視也就是對古農書整理的重視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醫、古籍、農業遺產的整理與利用,古農書研究也得到極大的推動。1954年10月,中央文化委員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出版中醫中藥書籍,包括整理、編輯和翻印古典的和近代的醫書”;與此同時,第二次全國農林教育會議召開,農業部楊顯東副部長、高教部楊秀峰部長作了重要講話,參會代表認為,這是“黨號召我們農學界整理祖國農業遺產”,很快啟動、實施了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業遺產整理工作。第二年4月,農業部又組織召開了“整理農業遺產座談會”,強調農業科學、總結農業遺產工作的重要性,聽取了農業文化遺產研究方面的意見和搜集、整理、出版有關古代農業文獻史料方面的建議,擬定了有關農業古籍校釋出版的計劃,要求“注意搜集古農書及相關地方碑志等文字記載”,且對“流傳在各地農民群眾中的農諺”,“體現祖國極為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的重要資料,亟應有組織有系統地進行搜集整理”。會議將積極整理出版重要古農書列為農史領域的重要任務。中宣部、農業部、中央農村工作部、高教部、科學院、農業院校、財經出版社均有代表參會。
農業部對整理農業遺產工作的高度重視,代表黨和政府的殷切希望。“在黨的指示與鼓勵下”,原南京農學院1953年開始籌備的農業遺產研究室迅速成立。也正是從1953年起,原西北農學院、北京農學院、華南農學院、浙江農學院等相繼成立了一批研究機構,在其后多年中,對農業歷史遺產、古農學、農史、古籍文獻的研究與整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夏緯瑛先生響應黨和政府“重視祖國農學遺產”的號召,與石聲漢一起點校《授時能考》,整理出版了《〈管子〉地員篇校釋》《〈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周禮〉書中農業條文解釋》《〈夏小正〉經文校釋》等先秦諸子書中的農學篇。畜牧學家謝成俠在校勘《元亨療馬集》時寫道:“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祖國文化遺產頗為珍視……本著采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方法,繼承其中可貴的內容,改進其中可議的部分,深信這對我國畜牧獸醫科學創造性的發展不難獲致”。謝先生的真切感受當然不僅代表他個人,也代表畜牧獸醫學界,代表全體農業科學工作者。在黨和政府的感召下,古農書研究者信心倍增,研究機構快速成立,研究成果迅速產生。
1.3 東南西北古農書研究中心成為古農書出版資源匯聚的中心
為響應黨和政府號召,各農業院校迅速成立了一批有影響的機構,如農業遺產研究室、農史研究室、古農學研究室、古代農業文獻特藏室等。各研究機構里都有一批熱愛農學農史的專家學者,他們古文字功底扎實,古農學知識深厚,熟悉現代農業生產實踐,無論是校釋評注,還是選編整理,力求忠實原本,精準釋義,啟發當代。古農書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形成了學術探索的氛圍和一批有影響的專著,成就了萬國鼎、梁家勉、石聲漢、王毓瑚、夏緯瑛、胡道靜、陳恒力、李長年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古代農業文獻研究專家,他們為古農書出版做出了卓越貢獻,其作品流傳至今,成為后人學習古代農業文獻的經典。有了農業文獻研究的專家與成果,20世紀80年代初,《農史研究》(華南農業大學,1980年)、《中國農史》(南京農業大學,1981年)、《農業考古》(江西社會科學院,1981年)等一批農史研究刊物應運而生,既有利于學術爭鳴,又匯聚了各類成果信息,也成為古農書研究者交流共享的園地。圍繞農業院校、出版社、古農學研究機構以及特定讀者需求形成的農業遺產、農業文獻搜集、整理與研究的氛圍也就是古農書出版資源匯聚的氛圍。因為熱愛與持之以恒的努力,全國范圍內逐漸形成東南西北四大農史研究中心。它們既是古農書研究的重鎮,也是古農書校釋整理的作者專家隊伍聚集地。以點帶面,推動了全國的古農書出版工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東,以南京為中心,以中國農科院、南京農業大學(原金陵大學、南京農學院)為主體,以金善寶、萬國鼎、惠富平等專家為代表。1955年,在南京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系農史資料史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經幾代人的不懈努力,2001年,整合多方資源成立了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從研究室到研究院,名稱變了,研究內容沒變;規模變了,功能沒變。現擁有明嘉靖刻本《齊民要術》、平露堂刻本《農政全書》等珍本古農書;整理出版了《中國農業史資料續編》《方志農史資料》《中國農學遺產選集》等重要文獻,先后完成了《汜勝之書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四時纂要校釋》《補農書校釋》《農桑經校注》《陳旉農書校注》《農政全書校勘》等一批經典古農書的校釋校注工作,成為古農書研究一方重鎮。
南,以華南農業大學(原華南農學院)為主體,以梁家勉先生為代表。在其擔任華南農學院圖書館館長之時,創建了中國古代農業文獻特藏室(1955年),征集、保存了一大批古農書珍貴典籍。1978年,在古代農業文獻特藏室的基礎上成立了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該研究室擁有《一切經音義》《聚芳帶圖》《毛詩名物圖說》等日本古珍本。梁家勉先生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農史研究的新水平。該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以其強大的實力成為南方古農書研究中心。
西,以西北農業大學(原西北農學院)為中心,以辛樹幟、石聲漢、夏緯瑛等為代表,將初始的古農學研究小組(1952年)發展為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1956年),再改建為中國農業歷史文化研究所(1999年),2010年成為以古農書收藏為特色的中國農業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該中心擁有280多種古農書,校注出版了《氾勝之書》《四民月令》《齊民要術》《農桑輯要》《授時通考》等經典農業文獻,以《中國農業遺產要略》《中國古代農書評價》《中國農書概說》等為標志性學術成果,坐穩西北古農學研究重鎮。
北,以中國農業大學(原北京農學院、北京農業大學)為主體,在王毓瑚先生的帶領下,依托農業史研究室(1978年),形成《中國農學書錄》這一標志性成果。且在古農書的整理校注,特別是版本溯源、物種考證上做了大量工作,留下寶貴遺產,為后續研究指明了方向與路徑。從1959年9月落成的全國農業展覽館到1986年竣工的中國農業博物館,及其編纂出版的《北京農業大學圖書館藏中國古農書目錄》等,證明該研究機構、展陳場所在北方及全國不可撼動的古農書研究國家中心的地位。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有東南西北為代表的一批古農書研究中心,形成“東萬(國鼎)、西石(聲漢)、南梁(家勉)、北王(毓瑚)”為代表的一批熱愛農學、鉆研農史、甘于奉獻的專家隊伍,搜集、積累、利用各具特色的藏書體系,數十年如一日地開展古農書研究校勘活動,支撐起了中國古農書出版一片天地,帶領并推動了全國的古農書研究出版工作。
2 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末古農書出版概況
正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視,古農書研究者深受鼓舞,自覺使命光榮,責任重大,因而發奮努力,整理農史,校釋農書,東西南北齊上陣,古代農業文獻研究一片蓬勃發展之勢。此時沒有“邊緣化”一說。
匯集多方資料統計,1950—1959年,共出版古農書60種,見表1。

表1 1950—1959年古農書出版種數統計
新中國成立,古農書搜集整理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受到高度關注,特別是1956—1959四年出版古農書51種,形成古農書出版的小高潮。其中,1956年古農書出版23種,五大農書無一缺席,清代農書相較其他朝代出版得更多一點,如汪日楨輯錄湖州地區蠶桑生產資料的《湖蠶述》、陳淏子專書花卉植物的《花鏡》、月令體農書《農候雜占》、楊鞏編纂的《農學合編》、陳開沚的《禆農最要》等。從成書方式來說,有影印、校釋、點句、校勘等;所涉出版社中,科學出版社1種,文學古籍刊行社1種,農業出版社4種,其余17種均為中華書局(如表2)所出,表明中華書局在落實文化部指示、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領導下執行出版規劃的良好狀況。

表2 1956年古農書出版統計
這是古農書出版繁榮極具代表性的一年。1957—1959年雖然出版數量上沒有超過1956年,但也分別有8種、8種、12種。反映出第二次全國農林教育會議和農業部整理農業遺產座談會的成效。20世紀60年代的前四年,古農書出版雖未大幅增長,但總體趨穩。分別為9種、2種、8種和11種,見表3。隨后,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革”掉了古農書出版的“命”:1964—1966年三年僅出5種,1967—1969年1本都沒有出。出版厄運延續至20世紀70年代。20世紀70年代的前五年依然1本都未出。從1967年到1977年,十年僅出版了4種。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各行各業迎來發展的最佳機遇,古農書出版的恢復期也正式到來。1979年出版了5種,為20世紀70年代古農書出版劃了句號,也為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出版小高潮奠定了基礎。

表3 1960—1969年、1970—1979年古農書出版統計
1980—1989年共出版古農書63種。對比20世紀70年代9種,應該是飛躍發展的階段了。無論研究者還是旁觀者都會對其未來產生更高的期望。然而,20世紀90年代的十年卻只出版了33種(如圖1),僅是20世紀80年代的52%。這種落差委實有點大。這一事實讓古農書研究者深為嘆息,邊緣化由此產生,失落感與焦慮感交織,不平衡心態一覽無余。

圖1 1950—1999年古農書出版種量曲線圖
1996—2000年是國家“九五”規劃,也是20世紀最后一個五年規劃。世紀之交本是一個總結過去、憧憬未來的重要時刻,但這五年古農書的出版情況卻有點令人沮喪,見表4。

表4 “九五”(1996—2000年)古農書出版統計
“九五”規劃時期古農書出版沒有增量反而下降,與全國 “圖書總印數由‘八五’末的63.22億冊增加到73.16億冊”“總印張數由316.78億印張增加到391.36億印張”“出版實力顯著增強”的成就很不相稱。分析其原因,惠富平認為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學科建設拓展,“農史學科研究層面進一步拓寬”,研究重點發生轉移,延伸到了“農業科技史、近代農業史、傳統農業文化、區域農業史、農業災害史”等領域,而作為學科基礎的農業科技史、農業歷史文獻學研究步伐平緩,有關刊物上發表的農書研究論文相應減少。
20世紀90年代,學科意識崛起,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復興,跨學科研究方法在農史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農史自身研究橫向拓展面加大,呈現出以下特征:(1)農業科技史研究成果豐碩。1989年農業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成為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研究的標志性成果。(2)農史學科意識增強。20世紀90年代,學科意識突顯,農史學科建設也提到了議事日程,《論農史學科主體意識和體制化建設》《農史學科發展方向芻議》《〈農史學科發展方向芻議〉一文的思考》相繼發表引導了研究方向。(3)農史研究方法受到關注。(4)地方以及少數民族農史研究有了較大進展。如西北、東北、太湖等地區的農史研究,云南山地民族農耕的產生與發展等。(5)中國小麥、稻作起源問題形成討論熱點。(6)傳統農具、機械農具、配套農具的制造、使用、促進生產方面的作用得到深入研究,《中國農具史綱與圖譜》出版。(7)農田水利史研究受到重視。(8)畜牧獸醫史研究持續不斷。(9)農業災害史研究得到加強。(10)歷史農業地理研究也得以開展。(11)農作物品種的引入與傳播等專項研究取得新進展。
這一系列關于農史展開的專題研究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學術文化熱、20世紀90年傳統文化復興、技術經濟喚醒對農史研究的影響,在學術史回歸、思想史趨熱的學術研究大潮推動下,農史研究也發生了一系列改變。有的是深思熟慮后學術方向的選擇,有的是就事論事中學術轉向的突破,也有的是缺乏思想自覺的學術本能響應。雖然出發點不一,但在專題研究上取得多元進展,突破了過去就農書說農書,從文字訓詁到文本校釋、單一直線的研究框架,呈現出重農業經濟史、農業技術史、農業社會史、農業文化史的傾向,研究視角多樣,研究內容增多,研究水平提高,立體地呈現出農史與農學、史學、文獻學、經濟學等學科的關聯、屬性與地位。
這一過程,于農史宏觀研究而言是拓展,是進步,于微觀、單一的古農書研究卻并不樂觀。相比過去研究力量分散,重視程度下降,研究論文不多,研究成果減少,呈現出學術思想的引領性、學術研究的指導性、出版規劃的統籌性等方面的不足。葛氏撰文認為古農書的校釋、研究活動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平緩低迷、與日遞減,陷入低潮。20世紀90年代,關于農史文獻及農學家的研究論文占年全部論文的16.4%,而2000年之后,古農書研究僅占約6—7%左右。研究成果少,必然出版數量少,雙雙下滑,邊緣化的事實與感覺成正比。
3 從“十五”到“十三五”古農書出版概況
20世紀末古農書出版下降的趨勢,直接影響到了“十五”(2001—2005年)。在這期間,研究農史的專家有的轉向農業文化的研究,有的轉向農村社會發展研究,愿意從事古農書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少,校釋人員、研究隊伍青黃不接;相關論著難以發表或出版。研究轉向對于個人而言無可厚非,但于古農書出版事業卻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十五”期間古農書出版23種,雖然是“九五”11種的倍增,但仍未走出低迷之勢。直至“十一五”(2006—2010年)下滑態勢方有較大改觀。
2008年9月,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工委”)成立。或許是古籍出版日漸式微帶來的壓力,中國出版協會加強了對古籍出版工作的領導,在其下屬二級組織成立了古工委。“十一五”期間古農書出版57種,年均11.4種,年出版量超過“九五”的總和。這與古籍出版管理工作力量增強有直接關系。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也是出版業由出版大國向出版強國邁進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古農書出版數量增長不多。僅比“十一五”多出2種。而這個五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降為《“十二五”時期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規劃》的子規劃,也多少令人沮喪,雖然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在2013年對《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進行了適當調整,但古農書出版量與“十一五”保持平衡,為59種。
總結21世紀以來古農書出版的情況,“十三五”成效最高,共95種,見圖2。

圖2 從“十五“到”十三五“古農書出版情況
總體來看,進入21世紀后的20年里古農書出版呈上升趨勢,令人欣慰,似乎與“邊緣化”之說不相稱。但僅僅自己與自己縱向對比是不夠的。同樣是古籍,比較一下中醫藥古籍出版的情況也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中醫藥古籍與古農書有著許多相同點。中醫藥古籍在繼承與發揚中醫藥傳統、指導臨床醫學實踐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故而,新中國成立后對中醫藥古籍出版工作高度重視,各地出版機構在校勘注釋、重印影印中醫藥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與古農書出版一樣定期制訂出版規劃。如,1982年,衛生部中醫司在北京召開了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工作座談會,制訂了中醫藥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年),計劃整理出版中醫藥古籍686種。(2)與古農書一樣以校點本、評注本,釋義本、白話解本等作為古代醫學文獻整理出版的重要載體。(3)與古農書一樣重視經典古代醫書的整理出版。“日本漢方醫古籍、朝鮮金禮蒙等人編輯的近一千萬字的《醫方類聚》等書,也整理后排印出版”。(4)與古農書一樣重視整理出版質量。以校勘為重點、以善本為對象;校而不漏、勘而有據;以搶救性、保護性出版的方式使大量鮮為人知的善本、瀕臨失傳的孤本以及系列古籍中醫藥叢書等得以傳世。(5)出版數量遠超古農書。1949年至1988年,中醫藥古籍出版1022種。同期古農書出版為163種。再如,195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出版的中醫藥古籍581種,同年,古農書出版23種。“十三五”期間,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完成了“中醫藥古籍保護與利用能力建設”項目,整理出版了406種重要中醫藥古籍。同期古農書出版95種。
出版數字雖然不能說明所有的問題,但多與少的比較十分直觀、清晰。固然有祖國傳統醫學遺留更為豐富的文化遺產的緣由,但古農書出版數量上的弱勢十分明顯,不由得讓人感嘆“邊緣化”。
總之,截至2022年7月,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古農書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古農書出版452種,保護、弘揚了祖國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在農業生態、水土保持、動植物養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當然,分析已出版的古代農業文獻,也存在規劃性不足導致出版品種重復;校釋水平不一導致高質量注釋作品不多;缺乏監管導致《茶經》出版泛濫;作者隊伍后繼乏人導致出版資源嚴重不足等問題。“邊緣化”一說來自出版上游,影響的是出版鏈條上的所有環節;看似一種感覺,實為一種現象,透過現象揭示的是它內在本質:對傳統文化的態度、重視的程度、投入的力度與作用發揮的有效度。它看似一種說法,也是一種壓力。
4 乘《意見》東風,挑戰邊緣化,用現代出版接續古農書生命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對被置于“邊緣化”的古農書研究與出版,無疑是一針強心劑。
《意見》的針對性與指導性十分明確。它既強調現實古籍工作體系有待完善,也對古籍工作的質量、水平提出了高要求,滿懷對古籍資源轉化利用、古籍數字化、古籍保障工作的殷切希望,提出古籍工作的體制機制應該更加完善,“標準規范體系基本健全,工作水平有效提升,古籍保護傳承、開發利用成效顯著,人才隊伍發展壯大”等多方面要求,努力實現“古籍工作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更加凸顯、作用更加突出,古籍事業繁榮發展”的前景目標,像總書記所期望的那樣,“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意見》的出臺是古農書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開展與推進的大好機遇,深刻領會《意見》精神,匯聚合力,結合實際,將傳承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的文化事業進行下去,在建設文化強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體現古籍工作者、出版者的責任、使命與擔當。
首先,多渠道搜集古農書現存情況,科學地制訂古農書出版選題規劃,讓古農書出版成為激勵古代農業文獻研究者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的力量。搜集古農書是為了更全面地清點、掌握老祖宗留下來的農業文獻信息,整理并出版是為了更好地為當代農業、農村、農民服務。處理好這種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系,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體現文化軟實力的力量。
其次,在組稿階段加大投入,讓古農書研究者潛心、安心打造精品力作。經典來自于時間投入與經費保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3年公布的‘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目錄’,在91部入選圖書中,有超過20部的出版時間在10年以上,有9部圖書的出版時間跨度在30年以上,最長的近50年”。古農書出版也是前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古籍整理項目,這是對古籍出版者眼界與實力的考驗。
最后,用影印或數字出版等不同出版方式,活化古農書。影印、修復古籍是保護古農書最好的方式,從古農書的版框界行、紙墨書法、耕織圖、校注圈點中感悟超越時空的不朽力量,它是對老祖宗的尊重,對傳統文化的敬畏。數字出版是為其賦能、活化利用的最佳選擇。如果說影印出版更多的是“感悟”的話,數字出版則直接“超越”。在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仿真、大數據等技術應用下,充分挖掘古農書影像數字資源,編制出版古代農業文獻可視化地圖,將古農書中凝聚的農業文化景觀、農業科技發展、農業技術傳播,外來農業物產與生態、農政、時空等環境有機結合,數字化搶救、復原瀕危古農書,挖掘古農書時代價值,接續其生命活力。
如此推進,無論古農書研究者還是出版者,都不能落伍,不能旁觀,即使“邊緣”也應回歸中心。因為系統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古農書也就是弘揚中華傳統,有利于堅定文化自信,同樣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著自身的精神與物質力量。
注 釋
[1]葛小寒.文獻、史料與知識:古農書研究的范式及其轉向[J].中國農史,2019(2):12
[2]文中數據來源于課題組成員孫明慧博士生的統計工作基礎,特別致謝。
[3]具體規劃包括:《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草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1991年—1995年—2000年)》、《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1996年—200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點規劃》、《國家古籍整理“十一五”(2006—2010年)重點規劃》、《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等。
[4]1954年10月26日 中央文化委員會在《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中醫古籍影印出版70年.https://www.zhzyw.com/zycs/mh/19122016895C96I83F79KGGE.html [2022-06-04]
[5]曾京京.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成立紀實[J].古今農業,2020(1):80
[6]農業部1955年農宣字第226號.轉引自:古今農業,2020(1):81
[7]萬國鼎.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Z].轉引自:古今農業,2020(1):82
[8]夏緯瑛.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后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6:119
[9](明)喻本元,(明)喻本亨撰,金重冶,謝成俠等校勘.元亨療馬集(附牛駝經)·序[M].中華書局,1957:2
[10]資料來源:《中國農學史·附錄》《古籍整理圖書目錄》(1949—1991)《古籍目錄》《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等7種圖書;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數據庫http://www.nlc.cn、中華古籍網http:www.guji.cn中國農科院科技文獻平臺http:www.nais.net.cn等;以中國農業出版社、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中華書局等為代表的主要出版農業古籍的出版社官方網站等。
[11]大寨大隊理論組.北京大學生物系等注釋組.齊民要術選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
[12](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M].天津農林局三結合理論研究小組譯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
[13](元)婁元禮原著.田家五行[M].江蘇省建湖縣《田家五行》選釋小組選釋.北京:中華書局,1976
[14]廣西農學院法家著作注釋組.齊民要術選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77
[15]吳尚之.我國圖書出版業“九五”發展綜述[J].中國圖書評論,2001(2):4
[16]惠富平.二十世紀中國農書研究綜述[J].中國農史,2003(1)117
[17]張波,樊志民.論農史學科主體意識和體制化建設[J].農業考古,1990(2):144-152
[18]卜風賢.農史學科發展方向芻議[J].農業考古,1998(3):132-134
[19]荊峰.《農史學科發展方向芻議》一文的思考[J].農業考古,1999(1):97-98
[20]周昕.中國農具史綱與圖譜[M].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1998
[21]葛小寒.文獻、史料與知識:古農書研究的范式及其轉向[J].中國農史,2019(2):14
[22][23][24]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建國40周年中醫藥科技成就[M].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704,703-707,703
[25]陳仁壽.讓中醫藥古籍“活起來”整理出版工作怎么做[N].中國中醫藥報,2022-06-08
[26]2000—2020年7月,多家出版社出版《茶經》,共99種。
[27]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OL].[2022-05-20].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1%E5%85%AB%E5%B1%8A%E4%B8%AD%E5%A4%AE%E6%94%BF%E6%B2%BB%E5%B1%80%E7%AC%AC%E5%8D%81%E4%BA%8C%E6%AC%A1%E9%9B%86%E4%BD%93%E5%AD%A6%E4%B9%A0/56666211?fr=aladdin
[28]姜小青.對制訂和實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長期規劃的幾點認識[OL].[2022-07-29].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7148894201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