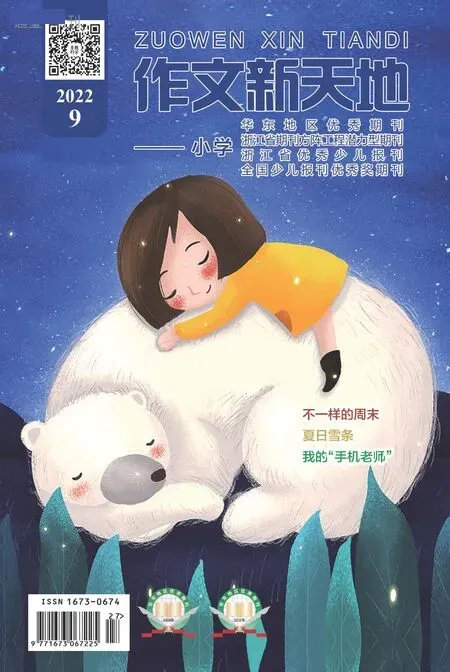夏日雪條
鄞 珊

下午最先穿越耳朵的是“雪條”的叫賣聲,在記憶的編碼上,它是干巴巴的童年里不可或缺的一點(diǎn)滋潤(rùn)的雪花,味蕾上那點(diǎn)冰冷的甜味慢慢氤氳擴(kuò)散,童年在一根雪條的點(diǎn)綴下,又蘇醒過來。
午飯的炊煙停息,太陽(yáng)炙熱的壓迫下,鎮(zhèn)上的居民沉沉地在屋里睡去。百貨店陳姨的瞌睡就袒露在低矮的柜臺(tái)后面,那不叫瞌睡,她純粹是午睡,除了沒有一張床,下面擺滿百貨的玻璃柜臺(tái)足夠她趴在上面美美地睡上兩個(gè)鐘頭,沒人打擾她。除了樹上的蟬、街上的母雞讓人知道還是活的,這樣的夏日,它可以讓所有的生物活動(dòng)暫停兩個(gè)鐘頭。若有路人,會(huì)誤會(huì)街上是否還有人。只是連半個(gè)路人也不可能有,除了中午的“雪條”聲殺進(jìn)來。
“雪——條——”
賣雪條的男孩子聲音極具磁性,從丹田發(fā)出的氣息穿過喉嚨,再拐個(gè)彎從鼻腔緩緩而出,“雪”字從鼻腔摜出時(shí)高音直抵槐樹頂端,馬上蓋過滿樹的蟬聲,“條”字則放低了八度,像個(gè)尾音,像女人拖長(zhǎng)的魚尾裙擺,猶如潮劇的青衣出場(chǎng),必定繞過長(zhǎng)長(zhǎng)的半個(gè)劇場(chǎng)。
“雪條——”這一叫,孩子先從睡夢(mèng)中追尋著他從遠(yuǎn)而近的聲響漸次醒來。聲音的分貝一致時(shí),賣雪條的男孩想是蹲在某個(gè)陰涼的地方——大榕樹下、屋檐底下,進(jìn)行守株待兔,希望能從某個(gè)門里跑出一兩個(gè)孩子。聲音許久停歇,定是有買賣進(jìn)行著,男孩子才會(huì)停下叫賣聲,進(jìn)行手中的活計(jì)。賣雪條的男孩子有著矮墩的個(gè)頭,戴著一頂寬檐草帽,跟連環(huán)圖里面上山下鄉(xiāng)的草帽一模一樣。實(shí)際上那個(gè)時(shí)代根本沒得選擇,就是這種草帽,大人、小孩都是一樣的款式,那戴在頭上的部分又特別淺,風(fēng)一吹,帽檐像帆,馬上帶動(dòng)帽子飛離頭部,所以帽子下面會(huì)系上一根白色帶子,可恨的是這帶子也沒法子打結(jié),它已經(jīng)給你連接好了,不管你的脖子長(zhǎng)短。所以每次戴這種帽子,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編織帽子的草刺還經(jīng)常會(huì)鉤住頭發(fā),弄不明白雪條弟為啥能戴得這么怡然自得。雪條弟——我們是這樣叫他的,這個(gè)名字感覺不是那么好聽,可是他做這買賣就得承受這個(gè)稱號(hào),好像是天經(jīng)地義的。
雪條弟把帽檐戴得低低的,像電影里面的交通員。他提著保溫壺走路的時(shí)候,只能看到他的半張臉。他的皮膚黝黑發(fā)紅,這大熱天,街上就他一個(gè)人,走在白晃晃的陽(yáng)光下,只有帽子頂著陽(yáng)光。偶爾他會(huì)沖撞了歇息的雞群,飛起的翅膀聲和雞叫的聲音混淆一陣子,又恢復(fù)平靜。孩子們已經(jīng)習(xí)慣“雪條——”的叫賣聲,這聲音跟蟬聲一樣漸成天籟。他叫得那么遙遠(yuǎn),離嘴巴還有好長(zhǎng)的距離。
這樣的叫賣聲跟大人無關(guān),一兩分錢的是孩子自己口袋里的事情,每個(gè)人從很小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懂得算計(jì)自己的積蓄,哪怕這積蓄是極少的幾分錢。這雪條是夏日的,夏日的雪條又甜又冰涼,沒有嘗過的只有在旁邊看著人家盡情享受,想象著那種美好的涼意。冰、雪,來自北方的想象就在這一根插著小木棍的冰棒里,一整根就三分錢。雪條像個(gè)不規(guī)則的長(zhǎng)方形,下面接近木棒的部分粗壯厚重。沒有哪個(gè)孩子能在一個(gè)中午一下子把三分錢給花出去,所以雪條弟提著的保溫壺還帶著一把小刀、一塊木板。雪條就放在木板上,你指看哪個(gè)部分。一分錢的是雪條的頂端。二分錢的可以選擇:是上面有綠豆的三分之二部分,還是下面那很大塊的部分,這一部分沉甸甸的,夠慢慢舔上大半天,但沒綠豆或者紅豆的參與,多少有些遺憾。美味的豐富與享受時(shí)間的長(zhǎng)短在一根冰棍里成了對(duì)立的矛盾。
叫賣聲來到家門口,看到門虛掩著,雪條弟朝里面多叫了兩聲:“雪條——”
沒有哪家會(huì)覺得他騷擾,本來鎮(zhèn)上走街串巷賣東西就是這個(gè)樣子的。躺在草席上的大人動(dòng)了動(dòng)身子,又轉(zhuǎn)過去。小孩已經(jīng)在他的第一聲叫賣中開始思慮,直到他到達(dá)自家門口,這抉擇終于分明起來。有站起來的,已經(jīng)去找自己的零花錢,搖搖四方木桌上的陶公雞或是陶胖豬,能從它身上的縫隙里倒出一兩個(gè)子兒,一分錢被從滿滿的陶豬里面搖出來顯得底氣十足。大人也不阻止,任由他去,畢竟自己的零花錢,沒有哪個(gè)小孩會(huì)舍得每天都出手的。
在竹簾里面把他叫住:“雪條——”
這一聲跟他的叫賣聲有天壤之別,雪條弟的叫賣聲是戲曲的,拖長(zhǎng)著音,抑揚(yáng)頓挫;孩子的“雪條——”是生活的口語(yǔ),沒有聲調(diào),但雪條弟耳朵能伸進(jìn)屋里,聽到屋里的喊話,他在門外馬上回應(yīng)了。
“哎——”他等待著人家叫他進(jìn)屋去或是他們出來買。
“進(jìn)來——”一聽得這話,他隨即推開半掩的門,發(fā)出厚重的“吱呀”聲。他的前腳已經(jīng)邁了進(jìn)來,手掀開陳舊的熟褐色竹簾,前半個(gè)身子探了進(jìn)來。我們是喜極了,幾個(gè)孩子圍了上來,雪條弟蹲了下去,把柳條編的籃子放下,保溫壺就掛在里面,掀開大大的壺蓋,壺蓋下還墊著好大的一塊布。蓋子還沒打開就能看到這塊發(fā)黑的布邊被壓在外面,一直弄不明白為什么要把冰棍包得這么嚴(yán)密。“怕化了。”雪條弟這么說。可是,夏天穿棉襖不是更熱了嗎?我們更不明白,雪條弟這下也說不出個(gè)子丑寅卯。“怕化了。”他還是如是說。
他很笨,像他的塊頭,除了“雪條——”這聲,好像沒聽他說過其他別的話。他的家就在伯公巷子的旗桿埕里。他賣雪條,賣完雪條有空也去上學(xué),不知道他上的是幾年級(jí),他好像也不在乎他上哪個(gè)年級(jí)。但他的雪條切得那叫準(zhǔn)確,一分錢、兩分錢,沒人算得過他。吃了綠豆的那部分,你會(huì)后悔少舔了好多冰塊;吃了冰塊的那部分,你會(huì)為綠豆的缺席而遺憾好長(zhǎng)時(shí)間,直到你下次重新再買綠豆的那部分。
雪條弟任由我們選擇。我們會(huì)在這根雪條面前指手畫腳,在他手上的小刀切下去之前,這種選擇是交給我們的。切好了我們要的那部分,他用兜里的竹簽——他在家里一根根地削好了,一插,一根冰棍可以分成三份,賣三分的錢。每人各得其所,拿著自己的那部分,慢慢地舔,冰涼的感覺從口里融化,沁入心里,甜美,還有時(shí)尚的感覺一起彌漫開來。想想古人是沒有這種東西的,它從哪里來我們不知道,但想到我們現(xiàn)在擁有這種食物,我們便無比自豪起來。
以前每吃一種東西,我都會(huì)無比幸福地問外婆:“你們小時(shí)候吃過嗎?”外婆不語(yǔ),我們便對(duì)她的小時(shí)候藐視起來。這時(shí)又把這個(gè)問題例行拋給外婆,卻好像擰開了外婆一直關(guān)著的蓋子,她一臉不屑:“我哪樣沒吃過?鹵鵝、燜雞、豆豉排骨……”
外婆一下子列舉了一大堆食物名稱,我聽都沒聽過,但沖那些個(gè)名字,我多少知道是什么東西,用什么方法烹調(diào)而成,我目瞪口呆。
幸虧,現(xiàn)在有雪條,我們上過學(xué)的都知道它另外的名字叫冰棍,這是我們那個(gè)匱乏得只剩下陽(yáng)光的下午突兀出來的驕傲和自豪。
“雪條——”
那樣的聲音一直穿街而過,穿過我的整個(gè)童年,那個(gè)賣雪條的男孩子一直長(zhǎng)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