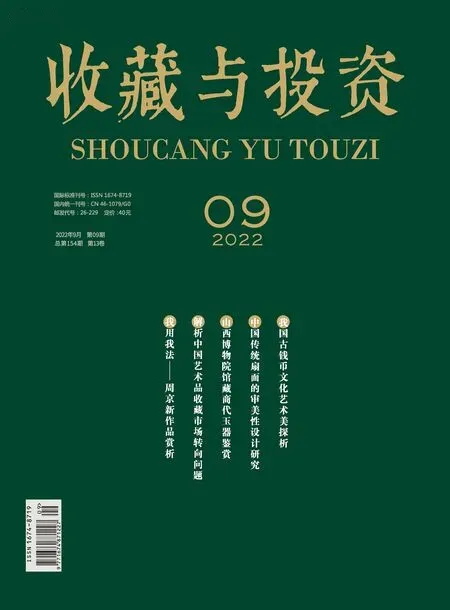丹青繪春秋妙筆頌吉祥
——國畫寫意花鳥作品賞析
郭愛霞(山西省長治市潞城區文物博物館,山西 長治 046000)
花鳥畫在我國國畫中占比非常之高,作為國畫的重要表現形式,創作花鳥畫要求畫家具備極高的筆墨素養。寫意花鳥是花鳥畫創作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對于寫意花鳥畫作品的賞析具有較大的意義。從另一個視角上解讀,可以認為寫意花鳥畫展現了古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自我理解。古人根據筆墨結構,形成屬于自己獨特的寫意花鳥畫繪畫風格,寫意花鳥畫中蘊含豐富的意蘊,可以展現古人崇高的藝術素養與文化情趣。
一、寫意花鳥畫的起源與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匠人已經將裝飾意義和寫實手法進行有機融合,在一定基礎上奠定了我國寫意花鳥畫的藝術基礎。出土的漢畫像磚展現了大量的花鳥意象,這些意象活靈活現,展現了我國花鳥的藝術美感。在秦漢之前,花鳥畫一直在不斷完善,人們很早就學會了利用花鳥裝飾屋子、制作標志等。進入隋唐時期,畫家逐步利用淺淡的筆觸和鮮艷的色彩繪制花鳥,形成了當時花鳥畫的創作特點。五代十國時期,徐熙和黃荃的出現,將花鳥畫的創作推向了一個小高峰,徐熙所用色彩比較淡雅,注重墨色的勾勒。黃荃的畫則給人以華麗之感,注重色彩的運用,他們推動了花鳥畫的改革。明代后期,花鳥畫整體呈現出水墨大寫意之風,這一時期的花鳥畫十分注重筆墨的著色,對于形似要求不高,重點在于筆墨發揮和展現獨樹一幟的風格。我國的寫意花鳥畫可以直接表達古人的心情,也承載了表情達意的作用。
二、國畫寫意花鳥畫作品賞析
(一)關注神似,隨心所欲抒發情感
中國畫更加關注神韻,寫意是畫家利用繪畫表達自我情感的形式,以繪畫為載體,抒發自己的情感。寫意中國畫都展現在手繪作品中,無論是簡單的筆墨寫意,還是淡雅有層次的筆墨寫意,都有各自的風格。中國畫寫意形式更加注重隨心,對于技巧性的繪畫技巧卻關注不多。用自由的筆觸舞動出自由的靈魂,而不是拘泥于形式,故步自封。中國畫自從元代開始,畫家對于自我心性的追求更加明顯,從大山大水到幾筆線條勾勒,一片葉子、一叢枯木,都包含了畫家的情感。在畫家眼中,山川草木不僅是眼前的自然景色,更多的是他們自由的精神世界。寫意花鳥畫中往往寄托著作者獨特的情感,類似于詩歌“賦比興”手段,托物言志,寄情于景。在繪畫立意上,往往是為了展現自我情感,并不是為了單純描畫花鳥而繪制花鳥,不是單純照抄自然,而是善于抓住花鳥與人們生活遭遇以及思想情感中的某些聯系,并進一步加以強化。不僅注重真實,要求展現花鳥的客觀造型,還會注重花鳥所表現的情感,強調其“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的移情作用,主張通過寫意花鳥畫的創作與欣賞影響人們的情感與精神生活,升華人們內在的精神追求。在造型上,更關注形似卻不拘泥于原有形狀,偏好利用現實對象實現作者的情感表達。構圖突出主體,善于裁剪,講究布局中的虛實對比與顧盼呼應,因此古人的寫意花鳥畫作品將詩歌的意境描寫到了極致,在寫意花鳥畫作品中留下詩歌的位置,輔之以印章,成為一種以畫為主的綜合性藝術形式。在繪畫技法上,花鳥畫由于對象是花鳥,因此相對于山水更為具體,相對于人物而言更加靈動豐富,因此其工筆色彩往往帶有裝飾的意識。寫意花鳥畫則更加注重筆墨的凝練性,更加有其程序性和不可模仿復制性。
北宋僧人惠崇代表作《秋浦雙鴛》充滿了詩情畫意,整體作品注重主體與環境搭配,作品中的鴛鴦墨色濃郁,創作者對樹枝的墨色進行了淡化處理,也就是將鴛鴦周圍的環境進行了“虛化”處理。這幅《秋浦雙鴛》描繪的是初秋時分的景色,畫面中繪制了河岸,閑情野趣溢出畫面,一對鴛鴦來到河岸邊,停下來,梳理自己的羽毛,氣氛安靜祥和。畫家用枯萎的荷葉和蘆葦點明了秋季的到來,淡雅的顏色為這幅畫增添了幾分秋意。鴛鴦的羽毛受到畫家格外關注,用細細的筆觸精心描繪,將羽毛的蓬松展露無遺。其用筆墨簡單勾勒的蘆葦和草葉的輪廓,與沒骨法細膩點綴的荷葉形成了勁拔的對比。整幅畫虛實結合,畫風清新,帶有幾分詩意。
項圣謨的《大樹風號圖》中的主題是大樹和老人,荊棘中雜草叢生,畫家用濃重的筆墨刻畫大樹,繪畫中的大樹參天而立,主干粗壯,有著剛強不屈之氣勢,枝條繁密,雖然樹葉已經脫落,卻依然彰顯出非凡氣勢,整幅畫構圖別致,在視覺上給人營造出一種蒼勁又不失獨立的穩定感。
唐寅是一位放蕩不羈的曠世才子,在琴棋書畫上有著很深的造詣,尤其是在山水畫上。才思敏捷、自由飄逸的思維方式,構成了唐寅灑脫的筆法墨法以及獨特的風格。《秋菊圖》中畫家自題:“彭澤先生懶折腰,葛巾歸去意蕭蕭,東籬多少南山影,挹取荷花入酒瓢。唐寅。”
(二)線條展形,墨色傳達情意
中國畫主要是利用線條的形式展現外形,作為寫意花鳥畫的基礎,線條有著獨特的魅力。寫意花鳥畫中給人的感覺是立體化的,主要是因為畫家賦予了花鳥生命力,在繪畫過程中傾注了心血。線條靈活多樣,粗細長短不一,在靈動中賦予每個作品生命力,呈現畫家情感。畫家用筆的力度以及情緒都會對線條的呈現有微妙的影響,不同線條展現了畫家不一樣的情緒,呈現了屬于畫家自己的繪畫風格。繪畫作品中線條的概念與自然形態是不同的,是超越自然形態的“人為”“文化”形象,需要經過概括、歸納、簡化、夸張等藝術化處理,才能完成形象的“藝術升華”,賦予其特定形式的意味,承載一定精神意志,并不是單純照搬照抄,一味描摹自然現象。

《秋浦雙鴛》27.4 cm×26.4 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銀杏翠鳥圖》27 cm×25.7 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馬世昌用斗方格局繪制了《銀杏翠鳥圖》,圖中一對叉尾太陽鳥,駐足于銀杏樹的樹梢,姿態一俯一仰,形成回旋律動曲線,銀杏果實與枝葉,則以石綠搭配汁綠填染,益發襯托出翎毛鮮艷華麗的身形。葉片的鉤筋與轉折,用筆極見細膩生動,反映了宋代畫家審慎觀物的創作態度。
張中的《枯荷?鶒圖》中,以墨為主,鴛鴦略加顏色點染,鮮妍可愛,頗具淡雅之趣。枯荷斷莖,畫有倒影,為古畫中少見。

《花卉圖冊》32.5 cm×57.3 cm 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
《斗雞圖》筆墨濃厚,樸茂多姿,端莊工麗,是文徵明的經意之作。在這幅作品中,他精心安排了竹子、菊花和石頭與兩只生機勃發的斗雞,兩只斗雞是畫中最為精彩之物,一大一小,劍拔弩張,似乎正要進行一場生死搏斗。圖中的斗雞造型準確生動,濃淡相間的墨色塑造出斗雞的整體形態。描邊點線結合,用筆虛實結合,構圖空靈瀟灑。這幅圖除了展現畫家的繪畫功底之外,更呈現了畫家的精神及其在遭遇種種挫折和困難時不甘示弱、奮起前行的勇氣與壯志。文徵明在描繪日常生活中常見事物時,往往會將自己的人生態度與繪畫境界融入其中。從美學意義上而言,文徵明這樣的審美趣味,恰好是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
(三)外師造化,內悟于心
每一幅寫意花鳥畫作品不同,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因為不同作家對于自己喜歡的花鳥有著屬于自己的解讀,形成了獨特的自然藝術感,如同鄭板橋所說,天然的竹子在他的眼中是竹子,眼中的竹子并不是胸前的竹子。鑒賞古人的花鳥寫意畫,則從古人的情感視角出發,理解他們的個性品質,自然就理解寫意花鳥畫背后的深刻內涵,這也恰恰是古人不同個性和不同藝術品位的追求。點線面、黑白灰、重復變異、聚散疏密、虛實濃淡、干濕枯潤、分割比例、統一變化都是在藝術實踐過程中抽象、提純、概括出來的形式要素和表現方式,都承載著一定的文化精神和觀念。
陳淳是文徵明的得意弟子,也是推動大寫意花鳥畫走向高峰的重要人物。陳淳在晚年期間,意識到“以貌似之”會導致“類狗之誚”,由此他拋棄了外在形似的束縛,更加追求內在的含義表現,尤其是“數年來所作,皆游戲水墨,不復以設色為事”,將狀寫自然造化上升到描寫物象之精神以及書法自我的精神高度。
《明畫錄》中介紹陳淳:“一花半葉,淡墨欹毫,疏斜歷亂之致,咄咄逼真。”在五十歲之后,陳淳已經能夠完全貫徹其“漫興墨戲”的創作理念,水墨大寫意藝術逐漸成熟。仔細觀察《花卉圖冊》中的荔枝形象,你會發現荔枝的形象并不是完全杜撰的,反而是符合其正常形象的。可以確定的是,在沒有對景寫生的情況下,陳淳依然可以描繪物象的基本狀態和內在意蘊,并表達繪畫作品的獨特內涵。筆者也深刻了解到在陳淳的寫生觀中,他并不是單純追求花卉的形象神似,而是重在表現物象的神韻,從而刻畫出自己的精神世界。花鳥畫創作不能局限在狀物之形,而是要表現物象的自然和神韻,既不要拘泥于傳統固有的創作模式,也不能全然依賴對景寫生,以致寫生與創作完全割離。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寫意花鳥畫作品的鑒賞可以讓人們深入了解畫家的內心世界,并獲得心靈啟迪。研究寫意花鳥畫作品,必然離不開對寫意花鳥畫的內涵以及意蘊的解讀,寫意花鳥畫作品各有千秋,而且每件作品所傳遞的情感與意蘊大不相同。由此可見,寫意花鳥畫作品鑒賞存在很大研究空間,需要進一步分析寫意花鳥畫作品本身,把握意象,解讀情感,為推動我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