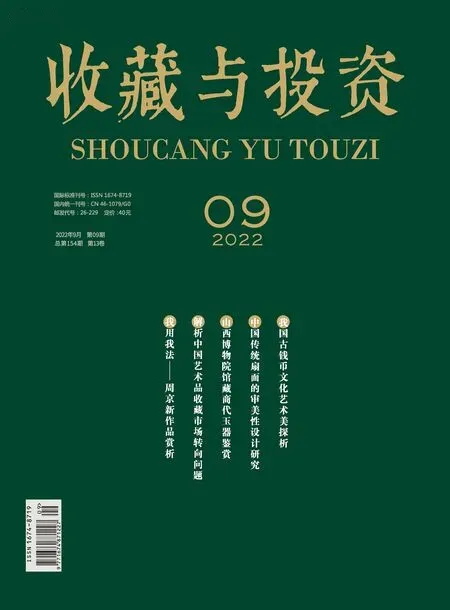理想與現實的糾葛
——戴進《三顧茅廬圖》賞析
龔雨萌(西安美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一、戴進的生平經歷及其藝術特點
戴進,字文進,號靜庵,玉泉山人,錢塘(今杭州)人。生逢號稱“仁宣之治”的明朝振興時期,卻意外地遭到挫折打擊,致使一生坎坷不平。他是明代畫壇屈指可數的全才畫家,人物、山水、花鳥無一不精,最擅長的就是在山水實景中描繪略有情節的人物活動,既有氣勢,又有情趣。
其代表作有《洞天問道圖》《關山行旅圖》《溪堂詩思圖》《風雨歸舟圖》等,繪畫風格可以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的作品多學南宋院體,筆墨工謹,中期作品學宋元諸家,風格多變。晚期作品融合了宋代院體、元代文人雅逸于一爐。因此,戴進被喻為“院體中第一手”“行家第一人”。這得益于戴進出生在一個錢塘民間藝人家中,父親戴景祥很擅長畫畫。據說戴進年輕時曾做過鑄造金銀器的工匠。匠人出身,決定了其文化程度受到一定的局限,但是熟諳金銀器紋樣裝飾為他的繪畫造型打下了基礎。杭州很多寺廟的佛教壁畫都出自戴進的手筆,畫得多,自然在紙絹上上手就快。作為一個職業畫家,這些經歷也讓戴進能夠掌握多方面的繪畫內容,手中的筆法墨法更加靈活多變,有些表現歷史人物故事,有些是宗教佛像,有些描繪四時風景,有些則反映文人士宦間交游酬唱的生活情況。因此《明畫錄》卷二中有記載:“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圭,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兼利家者也,神像人物雜畫無不佳。”
《三顧茅廬圖》,絹本青綠設色,縱172.2厘米,橫107厘米,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畫面右側中間落有“靜庵”二字題款,下面鈐有“靜庵”的朱印。此畫在中國美術史中作者暫歸于戴進,畫面中并沒有明確的紀年信息。徐邦達在《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中將其歸為款署尚待考,所以并沒有十足的把握認為這是戴進的作品。但是從其畫面中的筆墨信息來看,與戴進的風格較為接近。單國強認為戴進入宮時間不長,作品藝術表現力一般,此畫也可能為戴進傳派所作。

圖3 明 戴進《三顧茅廬圖》
筆者將戴進其他繪畫作品中的“靜庵”落款與《三顧茅廬圖》中的“靜庵”落款進行對比,認為其在筆法上的書寫相似無異,并且在畫面構圖、墨法上也類似,為同一個人所作。同時結合戴進的生平經歷,筆者認為戴進是具備作此畫的動機的,并且是借此題材來表達內心的苦悶之情。
二、畫面故事探究
這幅畫是以三國時期劉備攜關羽、張飛兄弟二人前往諸葛草廬,請諸葛亮出山輔佐為題材繪制的一幅山水畫。畫面以山石樹木占據主要部分,遠處山巒起伏,近處松樹參天而人物茅屋則為畫中點景。人物的刻畫細膩工整,線條平穩流暢,人物與人物之間透露出平和靜謐的氣息。雖然劉、關、張三人形象略帶文人化氣息,但是就細節特征來說還是有細微辨識度的,劉備站在前面雙手抱拳,身體前傾,略帶謙恭的姿勢,在向童仆詢問著主人是否在家。關羽、張飛二人則緊隨其后,身體后仰,略帶傲慢地交談著什么,似乎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視線順著茅草屋上移,則可以看見端坐在茅屋中的諸葛亮(圖1),其神態顯示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樣子。茅屋的帳幔以青綠加淡墨設色使其與周圍的山石、竹木區分開來。宣德一朝,由于皇權更替,宣德皇帝在繼位之時,他的叔叔朱高煦謀反,雖被鎮壓,但對于忠臣良將的渴求成為當時繪畫創作的主要題材。戴進通過對五個人物位置的排布,引導觀者視線轉移,間接透露了故事的情節。

圖1 茅屋中的諸葛亮
其次,縱觀整個畫面,仰山之彌高,氣勢巍峨,山道巒霧彌漫,瀑布飛流而下,房舍茅屋淹沒于叢林,置身于靜地,雖是描繪的歷史故事,依托的卻是明代文人追求的生活空間以及明代繪畫的風格特征,能夠使人產生一定的共鳴,如臨其境,馳騁想象,在獨步寧靜中虛擬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理想精神家園,人為造境,境隨情生,將主題一步步地詩意化。
三、畫面人物、山石、樹木分析
戴進的山水早年主要是學習李唐、馬遠、夏圭二人的風格特征。這幅《三顧茅廬圖》就是戴進在進入宮廷畫院之前所畫的,在皴法上帶有很明顯的馬、夏風格,并且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很像馬遠《踏歌圖》之中的斧劈皴山石,高大的懸崖峭壁通過干脆利落的毛筆側鋒多筆斜下地展示出來(圖2),占據了畫面的大部分面積,然后留出了右上角的空白,而不是用墨色占滿整個畫面。山頭以細小的雨點皴加以皴點,大概是參照了五代時期山頭的皴點風格,但是就皴點的大小來看,比五代至唐宋時期的大許多,其實這也是由五代至明代筆墨的一個發展趨勢,筆觸越來越大,細節化的內容逐漸減少。

圖2 山石局部
松枝也是明代繪畫的主要題材,例如畫面中上部的樹形,是在中間畫一根樹干,枝葉向兩邊平行而短促地排列。這種畫法比宋元時期簡略,這也是筆墨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塊或者粗糙的一種表現。安插在中間的松樹枝丫橫斜,松針墨色黑潤,成為視覺焦點,縱向的枝干隨著整體山石的走向,上下橫向接近平行的枝丫同時又與畫面下方的山坡平行,接連了左上方遠處的山石,與縱向的枝干于無形中交叉,稍微打破了畫面的總體走勢,給畫面帶來了一定的變化。
此外,畫面的變化還體現在畫面左側的竹林。孔明茅屋前的竹子以較實的墨色表現,屋后的竹子是以淡墨表現,再向上逐漸過渡成留白。用西方的繪畫理論來說就是有著黑白灰的關系變化,而用中國傳統的繪畫思想來說,則為虛實相生。重墨為實,淡墨為虛;近竹為實,遠竹為虛,前后的空間關系變化,使畫面既有豐富層次又極富韻味。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提道:“中國畫家并不是不曉得透視的看法,而是他的‘藝術意志’不愿在畫面上表現透視看法,只攝取一個角度,而采取了‘以大觀小’的看法,從全面的節奏來決定各部分,組織各部分……全幅畫面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是大自然的全面節奏與和諧……”“‘虛’與‘實’的辯證統一,才能完成藝術的表現,形成藝術的美。”也許戴進在作畫的時候并不是完全照著自然的實景描繪的,而是一個學習前人如馬遠的過程,用筆墨去表現山水,將相同的筆墨元素重新進行組合。所以合理且恰當的虛實關系能夠使得畫面的對比更加有張力,在保持畫面平衡的同時產生一定的視覺沖擊力,使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人物的表現體現了戴進獨特的個人風格,人物的衣紋出現很多節點,戴進在起筆拉出衣紋線條時,習慣將筆頓一下,像蠶頭一樣,再提筆,所以收尾的地方很尖,像鼠尾一樣。戴進在人物畫上先是遠師吳道子、李龍眠,獨創了蠶頭鼠尾描,行筆頓挫,筆法豪放。《三顧茅廬圖》雖然主打山水,以人物點景,但在細微之處卻也能見筆法。
人物相對于景物的比例,既不像巨嶂式山水畫那么小而不醒目,也不像描繪敘事性或軼聞中的人物山水畫,而是以人物為視線的焦點。戴進畫里的人物尺寸夠大并且數目也多,使得景物生動起來,但尚不足以主宰整個畫面;這種比例與元畫較為接近,不像宋代畫風。
四、理想的模式與現實的困境
筆者在此作一種推測,即《三顧茅廬圖》帶有戴進個人的政治訴求,渴望當朝明君能夠認可自己,重新受到重用。戴進進入畫院后,成為畫院畫家斗爭的犧牲品,特別是謝環。在一次御覽中,攤開春景與夏景的部分,謝環稱其畫作“非臣可及”,言下頗為贊賞。但是,當看到戴進的秋景時,卻面有怒色。皇帝詢問原因,他答道畫中漁人“似有不遜之意”。謝環認為漁人所穿的紅袍乃是士大夫的服裝,并非一般漁人所能穿著。文人著官服而行漁隱生涯的形象經常出現于元畫中,暗示高人隱士棄絕公眾生活,以及恥于仕元的態度。也許謝環認為這畫中帶有這種反政府的含義。當看到冬景一圖時,他更加認定戴進對朝廷有所不滿,他宣稱畫面中的“七賢過關”乃是“亂世事也”—七位賢者不滿腐敗無道的朝政而離開了國家,因此這幅畫可以勉強附會成是對皇上以及朝廷的侮辱。宣德皇帝同意了這個看法并且斥退畫作,導致戴進至少在這段時間內失去了進入畫院任職的機會。
李明、袁雯曾經對三顧草廬這個題材進行了探討,認為該題材是明代中期尤為盛行的題材,其文本來源與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之間的關聯性不大。這種圖式在元代就已經形成,創作者應該是有幸經歷了弘治中興,受到孝宗朝禮待正直賢能之士的影響。然而對于歷史故事畫來說,明朝宣德年間就已經非常流行,尤其是三國題材。例如明宣宗就繪有《武侯高臥圖》,宣德年間的畫院畫家商喜繪有《關羽擒將圖》,景泰至弘治年間供職畫院的倪端繪有《聘龐圖》,等等。戴進在畫院供職的時間是宣德至正統年間,長達十余年,但并未被授予一官半職。明代畫院從永樂年間初建到嘉靖前期,宮廷畫家群體以軍將或者民間畫家為主。尤其是軍戶出身的職業畫家在嘉靖以前的畫院中有較大的勢力,畫院中品級較高的大多是軍戶出身。戴進或許會因此而憤憤不平,一方面順應明代宮廷流行歷史故事畫的潮流,另一方面通過這幅畫來自喻諸葛孔明。諸葛孔明在三國時期也是文臣而非武將,戴進希望有賢君能夠邀請自己再入畫院,以此幅畫表達自己的懷才不遇。此畫的價值并不完全取決于他是否合乎帝王所要求的繪畫技術與規范,更多在于戴進在繪制的過程中是否抒發以及緩解了內心的苦悶和焦躁。雖然現實中他依然身處困境,不過三顧茅廬的題材卻給了戴進理想模式下的安慰。
戴進的繪畫雖然靈活多變,但風格特征卻有一個大體的走向,在師承宋元諸多名家的基礎上,主流風格為“院體”,所以戴進成為浙派的開創者。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提及“元季四大,浙人居其三,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明代后期流行宗派之說,董其昌和莫是龍提出了“南北宗論”的觀點,他們崇南貶北,把南宗奉為正統,為吳門畫派樹立旗幟,貶斥所謂的“行家畫”,即北宗。也就是說,戴進雖是一個職業畫家,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但是不久后吳門畫派的興起,使得文人畫在明代中后期搶占了新高峰,以院體畫為代表的浙派后期追隨者多流于形式,筆墨粗劣,格調不高,導致其日漸衰落。戴進再一次陷入了現實的困境。
五、小結
戴進雖然在宮廷內被排擠,但也擋不住他在民間的名聲大噪,對繪畫孜孜不倦的追求讓他在繪畫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三顧茅廬圖》是他繪畫某一個階段的體現,學習前人筆墨的痕跡較為明顯。不過行筆構圖嫻熟并且能跳脫出來,將筆墨的虛實、構圖的均衡運用得當也實為不易。所以對于傳統繪畫來說,這既是對程式化的遵從,又是對程式化的突破,只有融入自己的情感,才能做到突破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