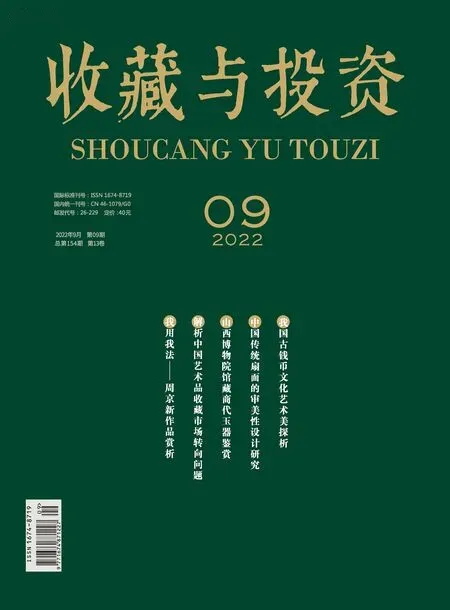云岡石窟洞窟形制特征研究
常夢婷,武 敏(中北大學 藝術學院,山西 太原 030051)
云岡石窟洞窟的形制演變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北魏時期的建造水平、佛教宣揚程度以及社會文化水平,因此,研究云岡石窟洞窟形制的變化,能夠進一步說明當時北魏佛教傳播對云岡石窟藝術特色形成的影響,也可以為石窟建筑特征的成因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礎。
一、云岡石窟洞窟分類
(一)中心塔柱式
中心塔柱式窟起源于印度支提窟,支提是梵文caitya的音譯,就是“塔”的意思,支提窟就是在洞窟的中央設置佛塔,所以又稱作“塔廟窟”。中心塔柱式窟成型于4~5世紀中期新疆所開鑿的龜茲石窟,然而此項技術在隋唐之后逐步消失。北魏石窟的一類主要窟型即為中心塔柱式窟,并由支提窟形制轉變為穹頂,用于荷重支撐。云岡石窟共有8座中心塔柱窟,分別是第1、2、6、11、5-28、13-13、39、4窟,如圖1所示,其塔柱樣式為中國式木塔的再現。中心塔柱式窟在平面方形洞窟中間開鑿塔柱、方柱,主要形式為重層式仿木構,在洞窟四面開龕造像,在塔柱四周開鑿禮拜道,穹頂采取平頂形式。中心的塔柱除具備塔象征外,還使穹頂及地面直接銜接,實現了洞窟牢固度的提升,因此被稱為塔柱。

圖1 云岡石窟第39窟
(二)大佛窟
大佛窟還被稱為大像窟,其特點是窟內大部分空間均為造像且主體高大,為展開禮拜及禪觀等宗教活動的場所。如圖2所示,云岡大佛窟即早期的曇曜五窟—第16—20窟,是北魏時期平城地區開鑿石窟的新樣式。此類石窟特點主要為大佛造像沒有直接暴露在外側,而是借助洞窟內本身的空間壁面完成大像的開鑿。此種洞窟多為禮拜場所,此類洞窟所設計的佛像前空間面積窄小,匠人借助此種設計方式,使得人們仰視佛像,充分彰顯佛像的偉大、莊嚴,使得佛教的感染力更強。此類型的洞窟以馬蹄形作為洞窟平面,窟頂呈現穹隆狀,壁面由下向上逐漸收縮,以此自然銜接窟頂、壁面。立足建筑結構視角,此種方式,可實現穹頂荷重的支撐。除早期洞窟外,中期階段的第5、第15窟也屬于大佛窟,其中第5窟在大佛窟基礎上,將佛像前的面積適當擴展,并在北壁下方位置鑿出禮拜道,更便于禮佛參拜。

圖2 云岡石窟第17窟
(三)佛殿窟
佛殿窟所承載的宗教功能為禮拜及講經,起源于中國早期的佛殿式寺院建筑,進入北魏晚期后得以不斷完善、健全。佛殿窟是云岡石窟中期階段的主要洞窟形制,即第7-10窟與第12窟。如圖3所示,其主要特征為:以南北方向作為縱軸線左右對稱,平面造型為方形或者是近似方形。洞窟均鑿出前室及后室,將洞窟前室作為洞窟外部空間及洞窟空間的過渡階段。此種建筑結構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普通民眾從實際生活進入理想世界。佛殿為供奉佛像所設置的場所,因此云岡佛殿窟中所體現的平面方形、重層布局的壁面設計原則,均為北魏建筑匠師對寺廟佛殿的模仿。

圖3 云岡石窟第12窟
(四)四壁三龕
四壁三龕式窟即為在石窟左、右、正壁分別鑿出一龕,此類洞窟多以小型洞窟為主,最早出現于云岡石窟的晚期階段。四壁三龕式洞窟盛行于北齊時期,但在之后的發展中逐漸消失。云岡晚期階段的洞窟所呈現的新樣式至少有70座,主要分布在云岡西部第11—13窟,第2—5窟等,方形平面為主要特征,在正壁、左壁及右壁各鑿出一龕,并在每一個龕內開鑿佛像,窟頂為平綦式。此類窟型的其他代表包括龍門石窟的魏字洞、藥方洞等。
二、云岡石窟洞窟形制變化
云岡石窟在鮮卑族傳統的影響下,由早期印度風格的圓形草廬式頂向具備“居山洞”“鑿石室”等風格的穹窗頂轉變,將洞窟拱門改造為馬蹄狀,改造結束后,洞窟拱門類似于鮮卑族傳統氈房的四頂。中期石窟較早期石窟而言,前者重視石窟內部空間的改造,將巨大的佛像作為大像窟的視覺中心,利用洞窟本身的空間鑿出大像,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大像免受風吹雨淋。所以,大像窟更類似于在山體中為大佛所鑿的大龕,但由于其體量過于龐大,因此修建為窟形。云岡中期的洞窟沒有延用前期明窗加拱門的設計,而是多見雙窟形式。雙窟形式的洞窟中有一個聯系兩個洞窟的前庭,雙窟前壁的兩側多設有立柱。前室、后室為洞窟內部主要構造,在建設后室時,多建設塔柱,穹頂為方形,部分洞窟的后室還設置了隧道式的禮拜道。有學者分析云岡二期石窟所出現的雙窟形制可能與北魏獻文、孝文時期與皇帝并稱為“二圣”的馮后相關。孝文帝將都城遷至洛陽后,民眾代替皇家成為建設云岡石窟的主要力量。分析晚期云岡石窟洞窟形制發現,建設規模越發狹窄且統一規劃不足,這一時期的洞窟不再有明窗的設計,只有方形的窟門。
三、云岡石窟洞窟形制演變的影響因素
(一)開鑿佛窟的功利化意圖
人們在佛教本土化發展過程中,與苦修佛教的初心逐漸偏離,除曇曜五窟具備象征北魏開國五位皇帝的意義以外,其余石窟造像多將祈求佛祖庇佑作為主要目的,由此也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封建皇權思想。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要在中國的土地上得到良好的傳播和發展,皇權確實可以為其提供一定的保障。佛教高僧倡導佛即為天子的理論也是為佛教的發展尋求一種政治保護的體現,同時佛教在中國本土的傳播和發展也為弘揚皇權、鞏固皇權政治發揮著重要作用。北魏時期中國本土佛教此種政治投靠行為除反映在佛教造像層面外,還體現在石窟建筑形態方面,如呈現前朝未曾出現的沙門禮拜皇帝。據《魏書·釋老志》記載:“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征赴京師……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逐常致拜。謂人曰:‘能雞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正是此種政治投靠,為佛教在北魏繁榮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印度的佛教理念中禮佛是苦修,在非常寧靜的環境下才能靜心禮佛。開鑿石窟的本意也是為給僧人提供禪修的場所。云岡石窟的選址靠近交通要道,雕鑿時間歷經數十年,且環境嘈雜,難以靜心修禪。由此可見,云岡石窟早期開鑿目的側重于世俗性。據銘記可知,云岡石窟部分石窟建設的主要目的是方便佛教信眾祈福及禮拜,同時也作為死者的瘞窟,并非均為僧興立,因此并不具備禪修功能。且早期石窟多為皇家主持開鑿,因此以禮拜祈福、彰顯功德、歌頌君王、宣傳教化作為主要功能。
北魏遷都洛陽后,講經風氣開始盛行,士大夫階層針對佛教的深入研究、信奉及熱衷,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佛教經典的傳譯。從某種程度而言,云岡石窟窟形的變化過程也是佛教世俗化的直接體現,由前期宣揚皇權威嚴,逐漸發展為后期普通大眾階層祈福、禮拜的場所,這些因素均對石窟的建造形態和功能產生了直接影響。
(二)洞窟實際作用的影響
北魏時期佛教盛行,禮佛的人數大量增加,因此,佛教洞窟也不再是印度佛教中僧人苦修的場所,而逐步發展為禮儀場所。為擴大場所容量,就必須擴大空間。北魏遷都洛陽前后的佛教倡導觀像禪定的宗教活動,引導普通民眾掙脫現實斗爭。觀像禪定必須要有佛像佛寺,造像修寺在北魏晚期盛行于洛陽,洛陽城所修建的佛寺數量遠超平城。云岡石窟在修建晚期時,由于喪失國家力量的支撐,規模縮減,但數量與日俱增。在此階段修建石窟者多為崇福者,目的也是祈求成佛、消除災禍、許愿還報、祈求富貴平安。佛教世俗化的進程在這一時期也逐漸加快了。
(三)雕鑿技術水平的提高
北魏社會在開鑿云岡石窟前,經歷了一場大范圍的移民活動,涉及的人口有百萬之多,其中就不乏名匠和僧人。一些小規模的佛像、石窟在曇曜五窟開工之前就已開鑿。依據佛教石窟的開鑿經驗,人們在設計云岡石窟時,沒有充分考慮開鑿石壁的石質成分問題,整個洞窟的設計可能存在漏洞,加上開鑿洞窟本身就對山體自身的結構平衡會造成一定的破壞,導致在修建過程中發生洞窟坍塌的情況。尤其是早期的洞窟,前壁較為脆弱,而早期洞窟又是開鑿明窗加門的設計,更增加了坍塌發生的概率。所以,建設云岡石窟的過程中,除必須保留象征皇家意義的部分外,在不斷發展過程中,人們開始重視洞窟的堅固性。
早期專門為僧團提供服務的石窟在不斷發展中逐漸變為單一石窟,但內部空間日漸擴展,與早期開鑿的石窟功能不同,并未對于儲藏、住宿及修禪等多方面功能展開綜合考慮,而是將上述功能單獨分離至山頂寺院。北魏時期孝文帝下令遷都洛陽,據《魏書·釋老志》記載:“景明初(500—503年),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網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505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二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請新山太高,費功難就,奉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由此可見,當時開鑿的技術水平有限,人們對石質山崖的開鑿還沒有足夠清楚的認知,仍處于不斷摸索中。就地質層面而言,云岡石窟砂巖地質較為疏松,這也是最初選址在此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對洞窟的堅固性提出了挑戰。因此,云岡石窟在發展過程中,后期為了增強洞窟的堅固性,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增加了洞窟前壁的厚度,明窗尺寸縮小,出現中心塔柱式設計等。
(四)拓跋鮮卑族生活特點的影響
鮮卑族聚集于北方廣闊的草原之上,受游牧民族生活特點的影響,其居住環境也存在一定特殊性。游牧民族的基本居住空間為氈帳,此種居住空間可適應游牧民族常年遷徙及逐水草而生的特點。此種易于移動、拆遷的圓形穹廬,頂部為穹隆狀,前方開門,在適當位置開設明窗。曇曜五窟窟頂呈穹隆狀,壁面、穹頂銜接位置無明顯轉折痕跡,以球狀圓形窟頂為整體形狀,類似于鮮卑族傳統氈帳頂。由此可見,曇曜五窟的建造模仿了鮮卑族居住的氈帳形態。
四、結語
綜上所述,云岡石窟洞窟形式以一定的印度佛教傳統思想為基礎,但更多融合了鮮卑族的民族文化和中國特色建筑風格。在建設過程中,諸多因素均會對云岡石窟形制的演變產生影響。佛教石窟在本土化的進程中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建筑特色,這也是在宗教意義上,中國的佛教石窟不同于印度佛教石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