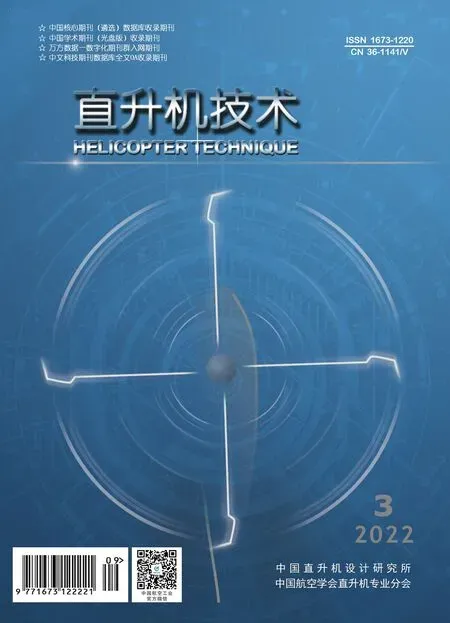全機風洞試驗在傾轉旋翼機發展中的作用
仲唯貴,黃建萍,張義濤
(1.中國直升機設計研究所,江西 景德鎮 333001;2.陸軍裝備部駐景德鎮地區航空軍事代表室,江西 景德鎮 333001)
0 引言
傾轉旋翼機是一種結合了直升機和定翼機特點的旋翼飛行器,既具有普通直升機垂直起降和空中懸停的能力,又具有定翼機的高速巡航飛行能力。傾轉旋翼機因其速度快、航程遠的構型特點,成為直升機高速化發展的重要方向。國外傾轉旋翼機發展經歷了XV-3和XV-15兩型驗證機的研發、試驗和試飛,完成了飛行原理、飛行性能和任務能力的驗證。在傾轉旋翼技術經過必要驗證并趨于成熟后,于1983年4月開始V-22傾轉旋翼機的裝備研發。目前V-22傾轉旋翼機已裝備超過400架,累計飛行時間超過60萬小時。歐洲正在進行民用傾轉旋翼機AW609的適航取證工作,并開展下一代傾轉旋翼機的研發工作。
傾轉旋翼機的構型特點帶來復雜的氣動和動力學問題,設計過程中需要通過風洞試驗進行研究和解決。因此,在傾轉旋翼機發展的不同階段,風洞試驗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特別是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在提前暴露設計問題、事故定位、完善設計、氣動特性研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系統構成復雜、測試參數眾多,要完成具有良好效果的風洞試驗,試驗難度大、風險高、周期長。本文對各型傾轉旋翼機開展的全機風洞試驗進行了總結,并分析了全機風洞試驗在技術發展中的作用,為傾轉旋翼機技術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1 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方法
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有兩種實現方法,即采用真實試飛樣機的風洞試驗和縮比試驗臺風洞試驗。
1.1 試飛樣機風洞試驗
采用真實試飛樣機的風洞試驗以發動機為動力驅動,通過在機體結構上設計支撐和連接點進行風洞安裝。試驗系統大部分采用機上系統,通過臺架天平能夠測量整機六力素;機上載荷和振動通過加裝應變片和振動傳感器測量;試驗控制通過機上飛控系統控制。以真實試飛樣機開展風洞試驗不需要重新研制試驗模型,對試驗臺和試驗測試系統的需求也有所降低。試驗不需要縮比,因此試驗能夠反映與真實飛行環境相近的氣動和動力學特性、載荷和振動水平等;同時,由于采用機上原有系統,能夠在試驗中反映機上系統工作的可靠性和協調。但是,能否開展真實樣機風洞試驗會受到已有風洞尺寸的限制,需要具有大型風洞試驗系統;同時采用發動機為動力和機上系統使試驗更為復雜,造成試驗風險增加。XV-3和XV-15兩型傾轉旋翼機的技術驗證機開展了試飛樣機的風洞試驗研究(見圖1)。

圖1 試飛樣機風洞試驗示意圖
1.2 縮比試驗臺風洞試驗
縮比試驗臺風洞試驗以電機為動力驅動,研制專用或通用風洞試驗臺和測試系統。由于需要進行縮比試驗,根據試驗目的考慮相似性準則,對試驗模型和試驗控制系統進行專門研制。相比于真實樣機風洞試驗,不受機身機構和改裝限制,因此能夠測量的參數可以更多,可以在機身、旋翼、機翼、尾面和舵面等部位安裝天平進行氣動力的準確測量,同時可以在機身、機翼、尾面等氣動部件布置壓力傳感器進行壓力分布測量。相比于真實樣機機上復雜的系統和設備,縮比試驗臺風洞試驗可以簡化系統,試驗難度會降低,試驗風險相對真實樣機也會變小。但是,試驗模型縮比后與真實樣機會存在差異,在相似準則條件的約束下,要開展滿足多種相似條件的氣彈耦合穩定性試驗或響應試驗難度較大。V-22傾轉旋翼機研制過程中開展了縮比全機風洞試驗(見圖2)。

圖2 縮比試驗臺風洞試驗示意圖
2 國外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
2.1 XV-3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
XV-3傾轉旋翼機項目始于1953年10月,共開展了四個階段的全機風洞試驗,均在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的40×80英尺風洞中完成(見圖3)。

圖3 XV-3全機風洞試驗
首次全機風洞試驗在1957年9月開展,針對試飛中出現的問題,將驗證機的三片槳葉鉸接式旋翼改為了兩片槳葉的擺振剛硬旋翼,通過風洞試驗研究改進旋翼后的性能和動力學特性。風洞試驗表明更換旋翼后消除了旋翼不穩定性問題,之后轉入飛行驗證。第二次全機風洞試驗研究短艙振動問題原因和改進設計效果,改進設計包括縮小旋翼直徑、增大機翼剛度以及提升旋翼操縱剛度。風洞試驗驗證了改進設計可實現動力學的穩定性目標,之后順利完成了傾轉過渡試飛。1962年6月,在軍方對XV-3完成了正式飛行評估后,開展了第三輪風洞試驗,研究定翼機模式高速飛行穩定性的提升方法。在增加了短艙和機翼剛度后,飛行速度提升到287 km/h才出現氣彈不穩定現象,但是最大飛行速度仍然與直升機相當。在XV-3驗證項目完成后,為進一步掌握傾轉旋翼機的動力學特性,啟動了第四次全機風洞試驗,試驗內容包括高速飛行狀態穩定性提升方案研究和理論分析方法的有效性驗證。在1968年11月進行最大風速約370 km/h的試驗時,由于翼尖勞損導致兩副旋翼松脫而使XV-3試驗機毀壞,但試驗內容和目標均已達成。
XV-3傾轉旋翼機四個階段的全機風洞試驗,前兩次是為解決試飛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保證試飛順利推進而開展,后兩次是為了研究傾轉旋翼機特性,提升性能潛力而開展。
2.2 XV-15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
XV-15傾轉旋翼機研制項目啟動于1973年9月,是滿足軍用或商用驗證需求的最小尺寸的概念驗證機。在項目策劃初期即制定了全機風洞試驗研究計劃,在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的40×80英尺風洞中進行,因此全機尺寸能夠滿足在40×80英尺風洞中完成氣動、載荷和系統性能的試驗要求(見圖4)。

圖4 XV-15全機風洞試驗
在XV-15研制階段設計了在風洞試驗時進行無人控制的工作方式,預留了風洞支架的安裝位置和遙測設備的安裝接口。風洞試驗時通過機外油源直接連接發動機供油,不通過機上油箱,在進入風洞前排干了機上油箱并填充了氮氣。為了保證風洞試驗的安全,利用地面系留試驗對風洞試驗的操縱人員進行了訓練;將飛行模擬數學模型更改為表征風洞試驗的數學模型,模擬遙控狀態的風洞試驗以評估應急處置程序的合理性;識別出在直升機模式高速飛行時雙發同時失效是唯一會產生危險情況的故障,制定了避免出現破壞性載荷的應急程序,要求在雙發失效的5秒內減少短艙攻角。共進行了54個小時的風洞試驗,完成了不同的短艙角和風速的試驗,測量參數包括通過風洞天平系統測量靜態氣動力和力矩,通過機上系統測量結構載荷和飛參,在控制室實時監控溫度、壓力和靜動態載荷參數等。
風洞試驗過程中機上部件和系統表現良好,出現的一些小問題包括:短艙下限動失效、機頭空速管振動、發動機滑油滲漏等。試驗中發現的最大問題是直升機模式前飛和部分過渡狀態下尾面的載荷過大。XV-15風洞試驗的時間安排在完成首飛之后、擴展飛行包線之前,通過試驗檢驗整機和系統,并且獲得準確的氣動特性數據,避免試飛風險。
2.3 V-22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
V-22傾轉旋翼機在1983年4月開始設計,在1984年至1988年的研制期間,采用縮比模型試驗的方式,開展了7輪的半模和全模的全機風洞試驗研究。試驗主要在波音的垂直起降飛機風洞和NASA的跨音速動力學風洞完成(見圖5)。

圖5 0.2縮比V-22模型在波音垂直起降試驗風洞的試驗
開展的試驗包括直升機模式、過渡狀態和定翼機模式的氣彈穩定性、旋翼載荷、機體振動等內容。為了基于縮比模型試驗獲得氣彈穩定性、載荷等試驗目的,試驗模型需要保證動力學和馬赫數的相似,因此在試驗模型研制上開展了大量工作。前期獲得的試驗結果用于評估設計結果和指導設計改進;后期試驗通過試驗數據驗證了與全尺寸設計相似條件下,在設計速度內特有回轉顫振不穩定問題具有足夠的飛行安全邊界。
2000年11月,在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的40×80英尺風洞中,開展了0.25縮比的全模V-22傾轉旋翼機風洞試驗研究。研制了傾轉旋翼機專用試驗臺,用于獲得傾轉旋翼機的噪聲數據,旋翼和整機性能,槳葉結構載荷,流場數據,機翼壓力等數據(見圖6)。試驗臺通過兩臺電機驅動,采用特殊設計的等速萬向鉸槳轂,實現動力學和運動學與V-22相似;槳葉采用基于柔性梁的雙路載荷傳遞構型,槳葉1階彈性模態(揮舞、擺振和扭轉)與V-22的頻率相似。試驗臺的測試系統包括兩側旋翼天平、機身天平、旋翼槳葉壓力傳感器、機翼壓力分布測量系統等,并進行流場和聲場測量。在獲得研究數據的同時,研制的試驗臺能夠成為傾轉旋翼機氣動機理研究的專用工具。

圖6 0.25縮比V-22模型在NASA 40×80英尺風洞的試驗
2.4 歐洲下一代傾轉旋翼機計劃(ERICA)全機風洞試驗
在歐盟第六框架下的創新競爭高效傾轉旋翼機集成計劃項目(NICETRIP)中,研制了旋翼機提升創新概念(ERICA)傾轉旋翼機的1:5縮比模型,分別在DNW-LLF風洞和ONERA-S1風洞中開展低速和高速的風洞試驗研究(見圖7)。

圖7 ERICA縮比試驗模型在DNW-LLF風洞試驗
縮比試驗模型為全機試驗模型。模型旋翼由布置在機身的兩臺空氣馬達經過中間減速器和旋翼減速器進行驅動。模型旋翼構型在全尺寸的萬向鉸旋翼構型基礎上進行了簡化設計,采用了無鉸式的槳轂構型,通過自動傾斜器進行總距和周期操縱。試驗模型的短艙和機翼外段可實現分別傾轉運動。試驗模型操縱量有16個,包括旋翼總距和周期操縱6個、外端機翼傾轉2個、短艙傾轉2個、襟翼2個、副翼2個、升降舵1個、方向舵1個,試驗時將重心處的全機六力素配平到零。測試系統包括:通過旋翼天平測量旋翼六力素和扭矩;通過機身天平測量整機六力素;通過尾面天平測量尾面六力素;通過一分量天平測量襟副翼、升級舵和方向舵的力矩;通過應變傳感器測量旋翼槳轂彎矩、槳葉載荷、作動器載荷;通過壓力傳感器測量模型機身和機翼表面的靜動態壓力等。每個試驗狀態測量的參數超過800個。
ERICA縮比試驗模型在風洞中完成了直升機模式、過渡飛行模式和定翼機模式的試驗,超過400個飛行狀態試驗點,并進行了過渡走廊的邊界研究。通過試驗積累了豐富的試驗數據,可用于傾轉旋翼載荷預估方法驗證、全機氣動特性驗證、旋翼動力學研究、機翼動態載荷預估方法驗證、飛行力學建模的數據支撐等。
3 傾轉旋翼機全機風洞試驗的作用
3.1 氣彈穩定性研究
傾轉旋翼機的旋翼、短艙和機翼構成氣彈耦合系統。對于定翼機模式的高速飛行狀態,傾轉旋翼機設計中必須要重點考慮旋翼、短艙和機翼的氣彈耦合不穩定問題,特別是回轉顫振不穩定問題。回轉模態不穩定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旋翼的力和力矩與柔性機翼/短艙結構的耦合。由于大尺寸旋翼的槳葉彈性運動和萬向鉸運動的動態激勵作用,傾轉旋翼機回轉顫振不穩定問題相較螺旋槳飛機更為嚴重,對傾轉旋翼機的旋翼和機翼設計產生極大的影響,并最終影響傾轉旋翼機的飛行速度、航程和商載。由于回轉顫振不穩定性的災難性特性,在設計時傾向于采用更大的回轉顫振安全性邊界。保守設計的原因之一是對回轉顫振問題預測的精確度不夠。
傾轉旋翼機的回轉顫振不穩定性問題在XV-3的全機風洞試驗中發現并通過風洞試驗研究了解決措施。在XV-15、V-22等傾轉旋翼機的研制中,通過全尺寸或縮比試驗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重點研究和驗證。因此,基于包括旋翼、短艙和機翼的傾轉旋翼機試驗模型,開展高速飛行狀態的回轉顫振穩定性試驗,能夠測量固定面的顫振速度特性、抖振載荷等,并且優化氣彈不穩定速度,可以獲得較準確的穩定性邊界結果,并可對提供穩定邊界的技術手段進行研究。
3.2 全機氣動特性研究
傾轉旋翼機存在直升機模式、過渡模式以及定翼機模式三種飛行模式,不同飛行模式下旋翼、機翼、機身等氣動部件工作的氣動環境不同,并且存在氣動部件之間的相互氣動干擾作用,對飛行性能、品質和載荷產生極大的影響。在直升機和過渡飛行模式下,存在旋翼下洗流場對機翼和機身、旋翼下洗流場對尾面的氣動干擾作用。特別是懸停狀態,由旋翼下洗流場與機翼相互作用產生的特殊的“噴泉效應”問題,生成機理復雜,產生的機翼向下載荷會降低起飛重量,從而嚴重影響飛行性能。
為了分析傾轉旋翼機的飛行性能、品質和載荷,建立準確的分析模型,除了需要旋翼、機翼、機身、尾面等孤立部件的模型或氣動特性,還需要旋翼、機翼、機身相互氣動干擾狀態的氣動特性。目前,通過理論分析和數值計算進行準確的預估還存在難度。因此,通過開展模型的全機風洞試驗,獲得包括旋翼、機翼、機身等部件的氣動特性以及全機氣動干擾特性,可為建模提供數據,并為氣動設計提供有效的指導。
3.3 載荷和振動研究
傾轉旋翼機載荷和振動都存在特殊性。傾轉旋翼機采用萬向鉸構型的旋翼系統,存在與直升機相同的槳葉、槳轂以及操縱載荷預估問題,旋翼系統各部件載荷表現為高頻的動態交變載荷,且由于旋翼槳葉的擺振剛硬特性,會帶來較大的槳葉動態載荷和較高的槳轂振動水平。傾轉旋翼機由于存在直升機、過渡和定翼機三種飛行模式,其振動源既包括了旋翼系統、傳動系統、發動機等動部件振動,也包括了機翼、尾面的振動,同時也包括了由于旋翼尾流對機翼、尾面的氣動干擾影響產生的額外振動。因此,直升機和定翼機的振動問題在傾轉旋翼機上都會存在,并且過渡飛行狀態是振動水平最高的狀態。
傾轉旋翼機旋翼動部件載荷特性以及引起的復雜振動問題,是傾轉旋翼機風洞試驗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通過傾轉旋翼機的全機風洞試驗,可以獲得較全面的旋翼槳葉、槳轂、操縱、機翼、舵面等全機部件的載荷特性,并能夠根據動載荷的水平、載荷傳遞等研究不同部件的振動特性。獲得的試驗數據可用于傾轉旋翼機全機載荷分析方法的驗證,以及振動抑制方法的研究。
3.4 全機氣動噪聲研究
傾轉旋翼機的噪聲源包括了旋翼槳葉的靜態、周期和隨機載荷,以及高槳尖馬赫數下的流場空間壓縮效應和非線性氣動特性。傾轉旋翼機顯著的構型特征影響了其噪聲特性,不同飛行模態下的旋翼和尾跡與常規直升機和定翼機都不同,同時存在短艙傾轉自由度,會改變旋翼的氣動特性,從而改變噪聲特性。
與直升機相比,傾轉旋翼機噪聲特性存在較多的不同。傾轉旋翼機具有更高的槳盤載荷和極大的槳葉扭轉角,帶來旋翼尾跡和槳葉載荷的變化,產生旋翼噪聲特性的不同;傾轉旋翼機雙旋翼產生噪聲,噪聲信號的相位產生變化,并且旋翼和短艙方位相對觀測點可變;傾轉旋翼機旋翼/機翼的氣動干擾帶來較大的流場變化,特別是懸停狀態特有的“噴泉效應”,產生較大噪聲水平;定翼機模式下,旋翼槳尖與機身近距離通過,噪聲傳播特性對機身影響較大,并且槳尖渦與機身作用產生新的噪聲。
通過孤立的傾轉旋翼風洞試驗可以研究部分傾轉旋翼機噪聲特性,但是雙旋翼、旋翼/機翼氣動干擾、旋翼/機身干擾等帶來的噪聲特性改變需要通過全機風洞試驗進行研究。通過傾轉旋翼機的全機風洞試驗,獲得較全面的噪聲試驗數據,可為理論分析方法驗證、聲源特性研究和降噪設計提供數據支持。
4 結束語
傾轉旋翼機經歷技術驗證機的研發、裝備的研發到大規劃裝備及戰場應用,已證明了其獨特的飛行性能優勢。在傾轉旋翼機發展的不同階段,基于提前暴露問題、事故定位、完善設計、特性研究等原因開展了大量的全機風洞試驗。相比于旋翼、機身、機翼等孤立部件的風洞試驗,全機風洞試驗系統眾多,試驗過程復雜,但是可以在傾轉旋翼機的氣彈穩定性、全機氣動特性、載荷和振動、全機氣動噪聲等方面提供較為全面的試驗數據。因此,傾轉旋翼機的全機風洞試驗在掌握傾轉旋翼機構型特點,建立不同學科的設計手段,提升性能,降低設計風險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