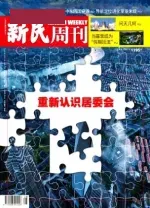古文辭的美
苗煒
這次我想介紹一本書,叫《國文課》,副標題是“中國文脈十五講”。作者徐晉如開篇就說,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正是新文化運動斷了中國的文脈。《國文課》從《詩經》講到李杜,講到宋詞。作者說,“我認為駢文是中國文字運用到了極致的產物,是漢語之美的最終極體現,因此駢文應該有比古文更高的文學價值,更應該被看作是中國文章的正宗”。
徐老師說,從魏晉到唐代,公文如制、勅、詔等等,大多用駢體文寫成,駢文能表現朝廷的威儀,國家的典重,直到清代,判詞都是用駢體文寫的,因為法律是嚴肅的,駢體文才能表現嚴肅性。有一位臺灣學者也說過,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無不特具體裁,別有風骨。然文章之華美,辭藻之旖麗,聲韻之協調,對仗之工整,詞勻色稱,氣靜機圓,則莫若駢四儷六之文。國家的典章用駢文來表達,會增進國家的神圣感和莊嚴感。
古文與駢文之爭,不是什么新鮮事。在新文化運動之前的北大,就有章門學人與桐城派文人之間的論證。桐城派文人是推崇散文的,我們上中學學過姚鼐的《登泰山記》,那就是桐城派的散文,到北大初創之時,桐城派文人吳汝綸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林紓授課時,以姚鼐、曾國藩所選古文為教材,到后來,黃侃等人加入北大,黃侃講《文心雕龍》,推崇以《文選》為代表的魏晉六朝駢文。等胡適、陳獨秀等人發起新文化運動,錢玄同直接開罵,“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前一句罵的就是推崇駢體文的黃侃等人,后一句罵的就是桐城派那些推崇古文的。據說,黃侃后來上課,五十分鐘一堂課,前三十分鐘都用來抨擊白話文運動。
現在我們看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可以簡化為“八不”,其中有兩條說的是不用典,不講對仗。胡適說,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這種說法就是用西方的文學標準來看待中國文學,把小說的地位大大提高,而對駢體文很是不屑。胡適這篇文章發表在1917年的《新青年》雜志上。
徐晉如這本《國文課》再度為駢體文翻案,他說,中國文字的特性,決定了中國必然會產生駢體文,也必然會產生格律詩。中國文字從讀音上就分平仄,從字性上又分虛實動靜,最宜于對仗。從哲學基礎上看,有陰必有陽,陰陽相生相濟,對仗就是這一哲學思想的美學實踐。《文心雕龍》中就說了,駢體文就是基于漢字特點而自然形成的,所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諸子中駢語就不少,比如《老子》中的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再比如《莊子》中的名句,“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
駢文是中國文字運用到了極致的產物,是漢語之美的最終極體現。
我們年少時的背誦,的確是喜歡對仗,比如背《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再比如背杜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從這個角度看,小孩子背誦《聲律啟蒙》,其實就是在沒有現代語法概念的狀態下理解詞性。
徐晉如在《國文課》中說,駢體文的風雅,很大程度上是靠頻繁的用典故。這會讓文章更加深刻婉曲,文辭更加典雅。徐老師強調,這樣美好的文學,本來就需要讀者達到一定層次之后,才能真切理解的。
我得承認,我雖然是中文系畢業的,但我的層次還是達不到欣賞駢體文的高度。我肯定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喜歡白話文和英文更多一些,但我感覺《國文課》這本書也很有意思,作者徐晉如毫不避諱自己的觀點,他對中國古文辭真是熱愛。我們也可以通過這本書,對中國古文辭多一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