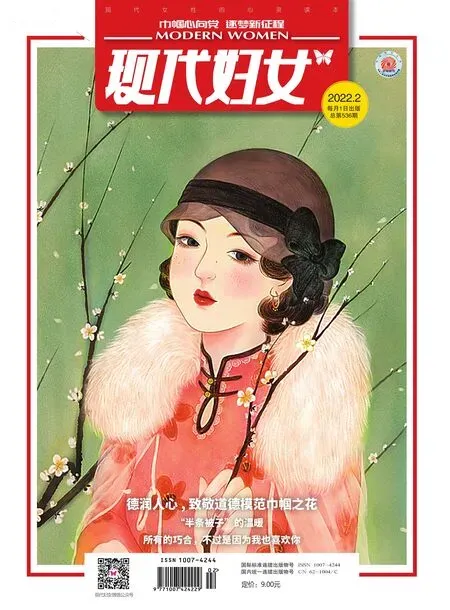追完心愛劇集,你“電子失戀”了嗎
當劇集走到了結局,你是否依舊沉浸其中無法自拔,并伴隨著某些“后遺癥”:每日固定時段追劇的小期待不復存在,內心悵然若失,忍不住反復回溯心愛的劇集片段,早已忘記追劇前的日子如何度過。倘若如此,你正在經歷一場“電子失戀”。
影視劇構筑了一個非常容易令人沉浸的“虛擬世界”,給予人們“情感投射”的實體對象。“失戀感”往往與投入情感成正比,追劇時灌注的情感越多,“電子失戀”后的空虛感越強烈,回到現實便越無所適從。
整個大壩填筑為面板堆石壩,需要填筑石方總量約540萬m3,實際填筑工期約30個月,平均每月需18萬m3,按每車24m3計算,每天需要車數18萬/30d/24m3每車=250車,但實際高峰期每天可能達到450~500車左右,傳統過磅方式根本沒有辦法滿足生產需要,人員過磅記賬強度也沒有辦法滿足要求,所以夾巖水利工程決定應用無人值守自動稱重系統。通過現代射頻技術、計算機軟件技術、遠程數據傳送技術、及地磅鋼梁結構設計的整合來完成這套全自動無人稱重記錄系統工程。
有時候,僅僅是劇集結束這件事本身就讓人心生失落。人們告別的不僅僅是一部部影視劇,更是追劇的時光和曾經的自己。2011年,長大了的哈利、羅恩和赫敏站在九又四分之三站臺,送走了最后一趟霍格沃茨特快列車;《老友記》歷經10年落下帷幕,一同結束的還有與老友們共同經歷的光陰;《請回答1988》的結尾,各戶人家紛紛搬出雙門洞,有網友形容,“仿佛從我心里搬了出去”。在那個“平行時空”里,“擬態人際關系”逐漸形成,劇中人物儼然成為我們身邊相識已久的“老朋友”。看劇的同時,仿佛也參與了他們的成長;揮手告別時,不舍情緒自然而然地傾瀉出來。
大功率參量陣定向揚聲器與傳統創造聲波的方式完全不同。它通過超聲波傳感器發出經超聲波調制的聲音信號,利用波在空氣中的非線性傳播效應,并通過信號自解調形成具有高度指向性的聲波。如同激光裝置可以把光束聚集在一個遠距離的很小截面上一樣,聲頻定向裝置可以把聲束聚集在一個確定的方向上,并把原始聲音無失真地傳給指定方向上的收聽者[1]。
有網友覺得,不追劇就不會因“電子失戀”而失魂落魄。但一次次的“電子失戀”,本質上是在某一個時間節點,偶遇了一段令你心馳神往的絕妙故事。面對“電子失戀”,與其“害怕花落而不播種”,不如承認和接納自身的情緒,擁抱劇集給自己帶來的積極效用。
網友們緩解“失戀感”的方式也五花八門。有人從劇集追到現實,將演員、導演采訪翻出反復研讀;有人堅持“只要我不看大結局,故事就沒有結束”;有人追完正片便轉頭奔向“同人”作品尋求“代餐”,“故事在別人的筆下以另一種方式延續”;有人反復重刷,直到下一部吸引自己的劇集出現。與此同時,影視劇公司還會放出“花絮”“彩蛋”,提供一系列“貼心售后服務”,安慰尚未走出“電子失戀”的網友們。
而包含感情線的故事,帶來的“失戀感”更為明顯,哪怕最終結局是“he”(圓滿結局),總有一幕讓人“意難平”。追劇過程中,人們往往不自覺地把“自我”投放到角色身上,跟隨劇中人物遍嘗世事,實現深度“共情”。可以說,劇集本身越“勾人”,我們就越“入戲”。只有足夠立體鮮活的形象塑造、貼合邏輯的故事書寫、真摯細膩的人物關系和情感,才會讓觀眾“代入感”滿分,并積攢出足夠的情感投射其中,意猶未盡到“放不下”。
時間向來是醫治一切的良藥,“電子失戀”也不例外。失落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歸于平靜,熱烈的著迷逐漸化為淡然的欣賞,收獲的感悟經歷歲月沉淀,也能釀成心底的白月光。與此同時,在劇集結束后抽離自我,以全局的視角去審視作品好壞,或許也是跳脫情緒、回歸個人生活的另一辦法。
通過軟件實現共振解調的主要分以下4個步驟:①對時域信號進行譜分析,找到機械諧振的共振頻率帶,并對此共振頻率帶進行帶通濾波;②對濾波后的信號進行希爾伯特變換;③構造希爾伯特變換后信號的包絡線;④對包絡后的信號進行低通濾波并作譜分析。可用圖1表示。
“電子失戀”是一場浪漫后遺癥,在影視劇搭建的“平行世界”里,人們得以短暫地逃離現實,體驗旁人的情感與經歷。曲終人散后,關閉屏幕摘下耳機,回歸平淡生活。縱使心里有落差,也不要忘記身在何處,畢竟屏幕里的美好世界,終究不如日常生活中的瑣碎來得真實。把注意力投射到學習和生活中,尋找新的關注點——比如一本好書、一個愛好、一部新劇。能趕走失戀陰霾的往往是下一次戀愛,下一部好劇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