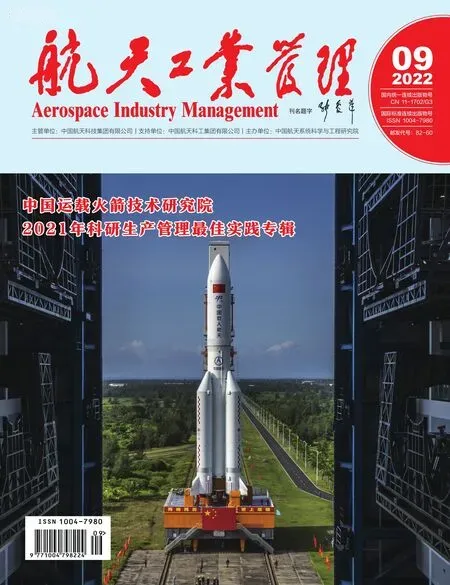基于PRICE軟件的產品價格評估研究
王晶、李春雨、魏東、李寶、劉賽 /北京航天長征飛行器研究所

自“十四五”規劃綱要發布以來,國家首次將“數字經濟”納入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進一步明確了現代企業數字化與成本管控緊密結合的發展要求。產品成本數字化管理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在20 世紀60 年代提出并總結提煉出多種方法與技術,通過對產品全周期成本費用跟蹤與控制,在降本增效的維度上取得了顯著的收益。在此背景下,以PRICE 軟件為代表的通用、商用化模型軟件在現代工業市場上得到了廣泛的實踐應用,通過一系列的優化改進延用至今。
筆者主要運用PRICE 軟件對產品價格的評估方法進行分析研究。PRICE 軟件是一款參數化成本估算模型系統軟件,其研發公司前身為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成本分析部門,估算模型廣泛運用在波音公司、雷神公司、洛馬公司等千余個航天航空項目的產品之中(如F-22 猛禽戰斗機),經過持續回歸驗證,優化其估算模型,進一步提升產品估算成本與進度的精準度。
一、工作與實踐
1.產品分解結構
產品分解結構(PBS)是PRICE 軟件進行產品價格估算的主干框架,其根據產品的軟硬件組成而逐級次分解,形成具有層級關系的產品樹狀結構,并以此為依據延伸出估算分解結構(EBS)、費用分解結構(CBS)、工作分解結構(WBS)、組織分解結構(OBS)等衍生概念。
產品分解結構的特點是根據生產配套任務中確立的分解測算顆粒度,識別出分解結構中的關鍵零部件與高價值的組成部分。PRICE 軟件為各零部組件提供了模塊化的屬性劃分,如自研或外購,不同性質的模塊需輸入的基礎參數數據有較大區分。
2.參數輸入
PRICE 軟件產品模型的建立相當于“骨骼”的搭建,“肌體”的填充則需要基礎技術參數的輸入才能使產品成本估算更貼近真實。產品的基礎技術參數種類繁多且具有級次的特點。基本參數包括結構件的重量、外形尺寸(長寬高)、公差等級要求、平均加工精度、主要加工工藝、去材率、表面粗糙度要求以及電子件的功能、重量百分比、集成復雜度等。綜合參數包括結構件與電子元器件的制造復雜度、工程復雜度、新研產品結構等,需要基礎技術參數進行綜合推導演算才能得到。
3.關鍵因子甄別
以航天某結構產品與電子產品為例,將收集的基礎技術數據代入軟件進行產品價格估算,通過比對估算與校準2 種模型的技術數據發現,影響產品價格的主要因子為運行環境、重量、制造復雜度、新設計百分比、工程復雜度及集成復雜度6 項。
一是運行環境。運行環境為產品實際應用的場景,軟件根據產品不同的運行環境配置不同系數,系數越高代表產品應用場景越復雜,要求的各零部組件可靠性越強,對應的產品價格越高。以某電子產品為例,運行環境參數對產品價格的影響見表1。

表1 某電子產品不同環境系數下價格對比
二是重量。產品重量為影響產品價格的重要因子,且“1 克重量1 份價格”。以某結構產品作為結構件樣例,某電子產品作為電子件樣例,不同重量與產品價格的數據對比見表2。

表2 某電子產品與結構產品不同重量下價格對比
與環境系數類似,重量對產品的價格影響成線性,因原材料成本及加工等因素制約,相同重量電子元器件的單位價格遠高于常用金屬結構件。
三是制造復雜度。制造復雜度需要大量的基礎技術參數進行支撐,并通過軟件特有的算法進行估算,從而獲得最終的系數,其對結構件與電子件價格影響見表3。

表3 某電子產品與結構產品不同制造復雜度下價格對比
制造復雜度相對結構件與電子件的價格關系呈指數相關,電子產品價格對制造復雜度更為敏感,當制造復雜度超過6 時,價格曲線斜率明顯增大,價格顯著升高。影響制造復雜度的因子較多,其中影響結構件的有加工工藝、去材率、平均加工精度、表面粗糙度等;影響電子件的有功能、重量百分比、電子件集成復雜度等。
(1)結構制造復雜度
影響結構制造復雜度的因子有以下5 項。
制造精度,描述制造的零件或組件的尺寸公差。取值范圍為1.3μm~12.7mm,與制造復雜度成指數關系影響較大。以某金屬產品為例,其制造精度為200μm,制造復雜度為4.862,若將制造精度設置小于10μm時,制造復雜度則超過6。
工藝,描述當前組件、零件所用的工藝數值,數值越小加工難度越高,成本越高,取值范圍為0.1 ~10,與制造復雜度呈線性關系,影響適中。某金屬產品的主要加工工藝為熱處理—機加—表面處理,對應工藝系數為3,每減少一單位工藝系數,制造復雜度升高0.29 左右。
加工指數,此參數描述了不同類型材料機械加工的難度,其數值來源于巴特摩爾協會制定的指數標準,標準定義碳合金鋼(C1214)的加工指數為100,大于100 的材料需比其容易加工,低于100 的需比其難加工,取值范圍為1 ~1000,與制造復雜度成指數關系,影響較小。某金屬產品的材料為鋁棒5A06/H112,其對應加工指數為180,制造復雜度為4.862,若將其材料調整為鋁1100/H12,加工指數增加到300,制造復雜度僅下降至4.803。
去材率,從毛坯到成品件過程中,廢棄材料重量的比例,取值范圍為0 ~99,與制造復雜度成指數關系。在0 ~95 區間影響較小,超過95 時影響較大。結構產品的去材率為20%,對應制造復雜度為4.862;若調整其去材率至99,制造復雜度驟增至6.053。
表面處理精度,為了提高表面光潔度而采取的表面處理工藝。取值范圍為0.1μm~254mm,與制造復雜度成指數關系,影響大。以某金屬產品為例,其制造精度為3.2μm,制造復雜度為4.862;若將制造精度設置超過5μm 時,制造復雜度為定值4.687;當縮小精度至0.5 時,制造復雜度突破至6.057,縮至0.1時,制造復雜度達到峰值9.714。
表面處理百分比,是特殊表面處理占總表面積的百分比。取值范圍為0 ~100,與制造復雜度成梯字形關系,影響較小。以結構產品為例,其表面積處理百分比為100,制造復雜度為4.862;通過調整百分比發現制造復雜度峰值發生在表面積百分比為66 ~72 的區間,為4.95;最低值發生在表面積百分比為1 時,為4.711。
(2)電子制造復雜度
相比結構制造復雜度,電子制造復雜度影響因子較少,僅有功能及重量百分比2 項,且根據不同功能其制造復雜度為定值,當電子件具有復合功能時,可按不同元器件的重量百分比進行配比,電子制造復雜度計算公式為:
Z=A*m(A)+B*m(B)+......
其中Z 為電子件制造復雜度;A、B、C...為元器件功能系數(PRICE 軟件進行系數定義);
m(A)、m(B)、m(C) 為 各 元器件占電子件重量百分比。以某電子產品為例,其由處理器、通信模塊及內存模塊組成,對應功能的電子件制造復雜度分別為8.09、7.63 與6.73;3 類元器件的重量百分比分別為25%、60%、15%,則此電子產品的制造復雜度Z=8.09*25%+7.63*60%+6.73*15%=7.61。
四是新設計百分比。新設計百分比是新研產品的一項重要參數指標,其對結構件與電子件價格影響見表4。

表4 電子產品與結構產品不同重量下價格對比
新設計百分比對產品價格的影響成線性關系,對新研產品影響較大,而對批產產品沒有影響。
五是工程復雜度。其是新設計百分比的配套系數,當新設計百分比為0 時,工程復雜度不影響產品價格,代表了產品新設計的工藝實現難度。以電子產品為例,對產品價格影響見表5。

表5 電子產品不同工程復雜度下價格對比
六是集成復雜度。集成復雜度描述當前成本對象向上集成的工作量等級(如總裝、總測工作),不會影響當前項的成本,影響的為上一級產品的成本。其對結構件與電子件的對應關系見表6。

表6 結構件與電子件集成復雜度對應關系
通過對PRICE 軟件各類產品模型的運算仿真,甄別出影響產品價格的關鍵參數是制造復雜度,其需要大量的基礎技術參數進行支撐,并通過軟件特有的算法進行估算來獲得最終的系數,根據對30 余種不同結構件與電子件產品的比對,制造復雜度與價格的關系都成指數關系,當制造復雜度超過某一閾值時,價格曲線斜率明顯增大價格將顯著升高。以下將影響制造復雜度的因子進行分析。通過對產品進行大致分類,可分為結構件與電子件,制造復雜度也因此拆分為結構制造復雜度與電子制造復雜度。
二、實踐效果
1.價格評估,數據為王
通過PRICE 軟件的應用,完成了5 個型號典型產品共計30余種單機與結構件的價格仿真估算,將價格結果與客戶暫定價和審定價進行比對后進行回歸分析,構建典型產品數據庫框架,初步建立了可信度較高的產品價格模型庫,形成了數字資產,對日后與客戶順利開展價格領域的相關工作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2.模式分析,成本管控
在PRICE 軟件進行數據采集時,需要對產品進行全級次分解,并由各外協廠商提供基礎技術參數,以此形成的價格模型掌握了外協產品價格的合理區間,對各類產品的成本價格組成有了一定的判斷,并識別出高成本組成部分,為產品價格模式分析以及降本增效舉措指明了方向。另外,通過與外協在產品價格評估上的互動,探索了新型成本管控的方法,為進一步建立健全產品價格體系打下基礎。
3.流程梳理,固化成果
目前已完成PRICE 軟件應用流程的梳理,初步掌握了產品價格的評估方法。通過對PRICE軟件應用指導手冊的編制以及部分人員的培訓,形成了1 支富有創新管理能力的價格工作團隊,后續將制定切實有效的工作策劃來固化價格評估的相關成果。
三、后續思路
一是根據各型號進展,選取典型類別產品,擴展模型數據庫,增加樣本多樣性,在反復迭代的基礎上完善價格評估數據庫中的相關數據,并針對數據進行分析,尋找差異,深化改進,指導后續的應用工作。
二是結合軟件應用的方法,將其嵌入到科研生產流程中,在競標型號和在研型號中選取試點產品,在技術方案確認后,進行經濟型評估,完成評估報告,控制研制期間產品成本;待用戶完成審價后對產品進行數據校準,完成校準報告,與數據庫積累數據進行對比分析,指導該類產品后續價格管理工作。
三是與客戶開展交流,進行接口對接,對估價與實際成本差異較大的產品引導用戶設置合適的參數或認可產品實際成本,根據其提出的需求與規劃進行實時跟蹤,并及時調整軟件應用研究的工作方向,構建與客戶進行產品議價的對話平臺,實現“同頻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