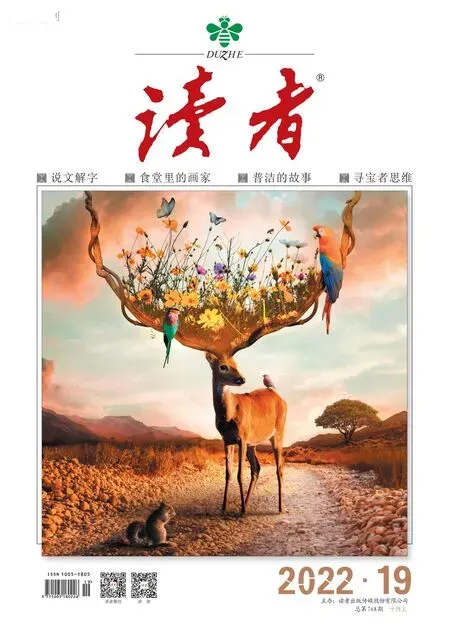雅事俗情
☉桂 濤
世人所好風雅之事,無非焚香品茗、掛畫插花、聽雨賞雪、候月酌酒。
但雅事就像白天鵝戲水,湖面之上優雅從容,湖面之下腳蹼翻飛。雅俗際會,俗到盡頭便是雅,雅到極致不風流。本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但無淤泥焉有荷花?
最近讀了兩本寫雅事的書,都將風雅背后的俗務人情寫得淋漓盡致,講了一人的琴棋書畫得用眾人的柴米油鹽支撐這樣一個殘酷真相。筆墨紙間,“俗”比“雅”似乎更值得玩味。
一本是基于歷史考據的小說《長安的荔枝》,寫的是“一騎紅塵妃子笑”背后,以舉國之力轉運新鮮荔枝的故事。唐明皇要博美人一笑,卑微的長安小吏李善德只能絞盡腦汁地計算,經過反復試驗,最終決定將荔枝連枝埋于土,放入雙層甕,再將其鹽浸、冰鎮,拼了命才將“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的鮮荔枝從嶺南“快遞”到長安。
幾千公里路程,全憑153處水陸驛站快馬接力,各種耗費不計其數。貴妃生辰當日口中的一顆鮮荔枝,要用無數小民的血汗來換。面對龐大的唐代官僚體系,李善德還要只身對抗官場的暗流涌動、云譎波詭。
荔枝無罪,但轉運荔枝過程中的那些勞民傷財、鉤心斗角、爾虞我詐,讓美人啖荔不再風雅。“玉雪肌膚罩絳紗”的珍果丹荔背后,是歷史深處值得細品的冷暖俗情。
另一本是寫明代書畫消費的《風雅之好》,此書從明人王忬花重金購買《清明上河圖》以巴結討好權臣嚴嵩寫起。嚴嵩因聽人說,送來的畫上,有一只麻雀的小爪畫得太大,竟能踏著兩個瓦角,明顯是贗品,于是將王忬治罪下獄,最終要了其性命。王忬到底是故意送假畫還是被賣家坑了并無結論,但他買雅物辦俗事最終賠進去性命卻是定論。
王忬的不幸遭遇,引發史學家對明代古玩書畫多重特質的逐層解構。
一方面,它們是清雅脫俗、饋贈親友的佳品,讓“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成為明代后期有閑階層的日常生活場景之一。
但另一方面,古玩書畫在明代也是攀附權貴的“雅賄”,是“人皆貪墨以奉上司”的媒介。在一個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的社會中,古玩書畫又是自我標榜、清高免俗的捷徑,是公認的品位標尺。在雅集和宴會上展示文物、“以書畫角勝負”十分普遍。因此,古玩字畫還是當時斗侈炫耀的資本,既能夸富,又能免俗,是經濟實力不動聲色的彰顯。
古玩書畫消費的雅俗之辨,背后其實是奢儉之爭、人情世故,審美已讓位于功利。宣德爐、成化瓷、景泰藍、永樂石雕、明式家具——風雅的背后不僅是閑暇與財富,更是精英階層的復雜關系網。
說白了,還是那點俗事。
(山 蟬摘自《環球》2022年第14期,張伯陶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