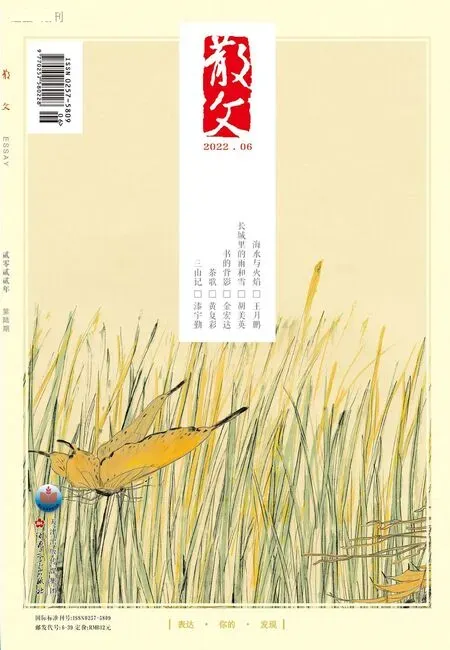書的背影【外一篇】
金宏達
一
書是人的好友,人有行有止,書也有行有止,書的背影,有時讓人看著傷懷。
若干年前,我在某大學圖書館供職,有一位日本數學教授,到了晚年,將他一輩子搜集、珍藏的數理書籍捐贈給我們。他一生清寒,為買這些書,省吃儉用,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在捐贈儀式上,他動情地稱此為“嫁愛女”,聽的人亦無不為之動容。這些書無論就其來歷,就其價值,皆理應優遇,然而接手之后,我們只能委屈它們暫時在書庫的一個旮旯棲身。館方既無人通曉專業日語,能將它們分類、上架,而且書架上也早已壅塞,幾無余地。曾聯系過數學系資料室,想請他們收留,來了幾位學科帶頭人,都搖搖頭,說在自己教學和科研范圍之內還用不上。一年又一年過去了,這位日本友人的“愛女”仍被遺棄在那里,真是“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這確實很無奈,換作那位捐書人,也許會為之很傷懷。我當然能理解,書有生命,有它自身的故事,特別能牽動人的情懷。
很多年以前,我求學時,常常是身無分文,偶爾得到一點零用錢,便積攢下來,鉆進書店,買下一本自己渴求已久的書。那時書價便宜,居然也購置了幾套線裝書——《詩經集傳》《古文辭類纂》之類,也都不是什么珍稀版本,而對一個愛好古典文學的學子而言,卻值得當作一筆財富,上大學時,我把它們珍藏在自己的衣箱里。忽然橫掃“封、資、修”的風暴卷來,我因有罪名在身,生怕禍及這些書,找個機會回到江蘇老家,隨身帶上它們,托付給一位好友。
幾年之后,局勢平定下來,我去找這位友人取書,他告訴我,因為用錢困難,連同他自己的書一起賣了。雖然這些書的歸宿也許還不太壞,仍有未能完璧歸趙的遺憾和些許帶時代色彩的悲情,使我久久難以釋懷。
二
書,生來就是為用的。據說,群居的智人很早就有了記載信息的需要,他們為協調、管理內部關系做出許多規定,為交換、儲存各種物品留下備查記錄,進而,還為向后代傳遞經驗和技巧,表達愿望與情緒,產生出文字符號。最初,也許像蘇美爾人一樣,刻寫在泥板上;繼而,或像華夏祖先一樣,刻寫在龜甲上、竹簡上,把它們分類,打捆在一起,就有了書。書,確是最早承載和傳承人類文明的神器,也有人稱其為“人類進步的階梯”,這一點,它當之無愧。
人類社會在近幾百年里驟然加快了前行的步伐,結下了無數文明的碩果。有一個細節,人們不應忘記:1453年的一天晚上,黑海和地中海交匯處的海面上,隨著奧斯曼大軍攻城炮火一陣緊似一陣,逃難的船只如亂蜂般飛離,其中就有船先于載人而滿載了書——正是這些書,保存了希臘文化的種子,而后播入歐洲大陸的土壤,滋榮出人類近代文明的春天。那些不辭萬險完成這一鴻業的人,無疑是最愛書、最懂書的人,他們完滿詮釋了書對于人類文明的偉大意義。
毫無疑問,書的收藏,最終是為了用,一旦歸于不用,或淪于無用,它的生命即告終結。現實中,人們會糾結于藏與用之間。有的地方,往往重藏,限用。也是因為曾在圖書館供職過,我知道有許多不良于用的情形。在重藏方面,又往往陷入量的迷思,不但以大量的復本充數,還不肯認真地進行甄選,讓許多低質、劣質的出版物占據有限的空間,造成好書的窒息。巡視一下一個個龐大的書庫,你能看到,確有不少書是在“尸位”,它們隨帶的讀者借閱卡表明,從來就沒有被人“嘗鮮”過。還有些書則是被人為地刻意封存,或就是特別保護,不讓人靠近,它們都成了地道的“死囚”。有一次,我憤激地想說點什么,寫下了一個題目:《萬丈書冢平地起》。我在校園里散步,望見夜幕下的圖書館書庫大樓,一個黑乎乎的龐然巨影,想到一些圖書不良于用的痛心的事,就首先想到這兩個字:書冢。
我們當然要創造條件使書利于用,使它活力四溢,而不要讓人看到它被無端地幽禁和湮沒。
三
時光荏苒,我也到了一把年紀,一次次搬家,搬來搬去,凈是書,真苦不堪言。其實,我的書和我的一些朋友比起來不算多,更不能與酷好藏書的人或藏書家去比。“藏書”全盛之時,也或有幾千上萬吧,固然“多乎哉,不多也”,堆在室內,也要占去很大的空間。早自十多年前起,我就到遠郊農村賃屋,以存放一時用不上的書,使人、書各得其所。書們的新居頓時恢廓、堂皇起來,書架環列,氣宇軒昂,頗為可觀。此策千好萬好,唯有一條不好,便是租賃之事不得久長,于是數年之后,又要另覓他處,好讓我的書們安身。
搬家時,一堵堵墻似的書,很令人頭疼,也正是此時,讓我不得不認真端詳起來,它們果是個個都值得端然高踞那里,并值得為之費力搬遷嗎?我先從自己平生疏懶,自己現今的年歲、時間、精力和專業范圍、方向盤算:一些書,我還會與之有緣交接嗎?
有人曾告訴我,對書不可太有功利心,想一想,這也是有道理的。年輕時功利心重,劃定研究方向,學以致用,購書、藏書、讀書,都與一定的目標相關。上了年紀,不免淡泊起來,讀書自少了許多功利性,此時也會讀些所謂“閑書”,或讀書以消閑。而閑消之后,此類“閑書”是否一定要存呢?這就猶如報刊,除非有特殊收藏的目標,許多人都會將看過的報刊交給收廢品者,一些“閑書”,除卻包裝之外,其實亦與報刊無二,報刊可棄,為何就不可與這些書道別呢?
愛書的人總歸不忍心將自己手上有模有樣的書拋棄,吾國的古圣賢早就教導我們要“敬惜字紙”,更何況還是“開卷有益”,那就“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吧。我也曾恭請年輕的朋友來舍下挑選所需要的書,其眼光獨具者,將若干坊間已難以見到的舊書收入囊中,后來者則未必有此幸運。有時這種對象找起來也難。還曾經聯系過幾家圖書館,館方答應了,又敦促數次,終于來人了,老大不情愿的,像是倒欠了他們的債款,此種經歷并不愉快。有一次,中學的母校召集校友開會,號召捐助,乃挑選一批書郵去,冀有所助益,結果泥牛入海,杳無回音,人家或是希望收到鈔票一類,書之類非其所欲,不對路也。邊遠地區學校對書或更有需求吧,然而一來,管道不通,運費、運力,都大費周章;二來,所送之書,亦未必是他們所需。
最省事的途徑,莫過于交給收廢品的人了,我嘗懸揣,書交到他們的手里,無非有兩個出路:一是他們會分類,將有可能賣得出去的,轉到書販那里,換個好價錢,書也得到生路;另一便是按重量賣出,化成紙漿,給這些書一個投胎再生的機會。前一條,我未做過調查,但就所見市面書店、書攤很少而言,恐怕也很難行。我曾將一些較大的畫冊之類拿到中國書店去賣——那里有專司收購舊書的部門,經手收書者皆是對選書很有眼光的人。那天我面對的店員就緊皺著眉頭,好不容易開出了一個極低價格,我倒不介意,只是和他攀談幾句,聽他大念苦經。原來,他們也為收來的許多書堆積如山、沒有出路而苦惱至極,不得不選書從嚴,收價壓低。
我知道,許多書的最后歸宿,只是化漿的場所,這說來似乎有點罪過,而實情就是如此。作為讀書人,曾經的藏書者,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無非是一邊自己用著,一邊也適時地處置,如前面所言,“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讓手中的書得其所哉,盡其所用,此事誠然行來不易,也還是要努力去做。曾有人倡議一種讓書自己漂流的活動,就是將書放在公共區域,任人取閱,閱畢,再“漂”至下一個讀者,想法很是不錯,不妨樂觀其成。
無論如何,書籍總是人類的好友,迄今為止,也仍是我們最親密的伙伴,當電子書橫空出世,曾一度引起過一些人疑慮傳統的書籍會不會消亡,現在看上去,書籍的身影依然活躍,圖書滿架,一卷在手,在理想的生活中,仍是一個非常享受的經典場景。祈愿在未來人類向外太空的遷徙之旅中,馬斯克們一定不忘帶上地球最貴重的珍寶——助成人類文明輝煌歷程的圖書,這是我們最想看到的書的背影。
我從五十多歲起就備下拐杖,不時拄一拄,看上去頗有“望秋先零”之意——人說是一種衰老的象征。
其實,事起于得了“五十肩”,無來由地右肩就痛起來,整個右臂會突地如廢了一般,嚴重時,有一次下車,疼得幾乎跌撲在地。我于是感到,除了治療之外,還需要一根拐杖來支持。不幸的是,痛在右肩,右手也不能著力,即便如此,也多少得到一點被“護衛”的感覺。
接“肩”而至的是“踵”——腳跟痛,這也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疼痛,痛時幾不能落腳,更不能行走。于是,拐杖便出而“代庖”,出出進進,與另一邊腿腳相配合,如同支起了一個豎立的擔架。我由此深知,區區拐杖,實是人在危難時的真正得力伙伴,一個可以托付殘身的朋友。
據說,人之所以偉大,因是唯一能直立行走的動物,從四肢爬行到兩足行走,是人類進化過程中一個偉大的轉捩——今天的人當然無法想象其間會有多少艱難況味。后肢義無反顧地接下了前肢的活,承受上身的全部重量,不僅要行走,而且要奔跑、跳躍——此事一做一輩子,實在不勝勞苦之至。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首先就在年老時體現,各種腿腳疾病頻頻發作。老人往往步履蹣跚,不良于行。民間俗語云“人從哪里老?先從腿上老”,所指即這種現象。上古、上上古的人,也會有老了的時候,行走艱難之際,順手撅一根粗壯的小樹干,助一助足力,定是不二之選。所以,若論歷史,拐杖的產生應是極為久遠,幾乎可以說與人類直立起來同時。《山海經》中說,夸父追日,到精疲力竭之時,就把拐杖扔出去,化為一片樹林,造福后代——拐杖負載他的托付與心愿,是他最重要的遺產,值得我們對之另眼相看。
如今的人大抵不服老,也不愿在人前顯老,對于拐杖倒有點歧視。有一次,我到一位故交家里拜望,他已是近八十歲的老人,給他帶什么做禮品呢,就想到了拐杖。舊時后輩敬老祝壽,每有送拐杖之儀,我與這位朋友雖為平輩,送一根拐杖,更有相互慰勉之意。不料,他竟再三推辭,最后勉強收下,閑閑地把它放在邊柜旁,還再三說他身體很好,不到用此物之時,也絕不會用。我也自覺無趣,許多到嘴邊的話,只好咽了回去。
我也想過,對拐杖的這種排斥,或者不完全與老不老相關。清末有一幫留洋歸來的新派人物,無論老中青,總喜歡手提一根拐杖,英文為“stick”,又稱“文明棍”,在魯迅先生筆下,成為“假洋鬼子”的標配,弄得似乎名聲不佳。其實不然,遠古不去說了,我們的戲曲舞臺上,有多少年高德劭的老太爺、老太君都是拄著拐杖的,而且上面還附著了龍頭、鳳頭之類裝飾,材質也取用紫檀、雞翅木之屬,不僅顯示身份高貴,而且有威權的分量。至于進而又造出什么“權杖”之類,傳授大位,就更非凡人所可企及了。
外國人似乎沒有我們一些人的偏見。有一回,我去游黃山,攜了一個較特殊的拐杖,是三條腿的,可以張開,撐起一個三角形的小小帆布椅,拄杖行走累了,可隨時隨地打開,讓吾臀落座,腿腳即獲歇息。一路行來,竟很有當年陶潛先生“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的瀟灑之態,引得幾個氣喘吁吁的老外蹺起大拇指,連連夸好,不勝歆羨。
斗轉星移,自己年歲一天天老起來,腿腳日漸不靈光。前年我在外地,泡完澡,從浴缸里起身,竟很困難,不得已翻過身,以膝蓋頂住缸底,一使勁才勉強站起來。后來好長一段時間感到膝蓋銳痛,回溯一番,終于找出了致痛之由,正是那次泡澡起身又令吾膝不堪受命之故。那么,以后又如何是好呢?除非不泡澡,若要入浴缸,則須先備好拐杖,借助腕、臂之力站起來。忽然想到,這或者就是最純粹意義上的“手足之情”了吧,不禁為之莞爾。
人在困難時需要幫助,早年我們蹣跚學步,所有能扶的東西,都是我們的“拐杖”;病中無力起床、行動,親人在旁相扶,是我們有力的“拐杖”;擴而言之,學習上遇到“攔路虎”,師友的指教,參考書、字典的釋解,也是我們與有力焉的“拐杖”,皆能助我們逾越障礙,順利前行。垂垂老矣之時,“后肢”已不克支撐沉重的身體,需要原先的前肢“出手”,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手拄一根拐杖,也是手對足的真誠報答:謝謝啦,你們一生勞累,現在,就讓我分擔一下吧。